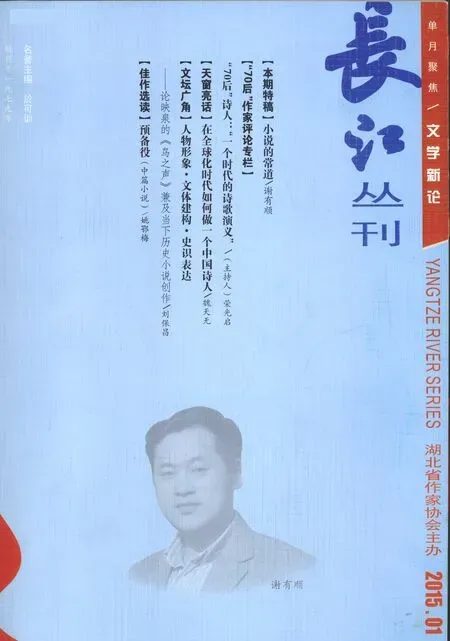好人一個的戲劇人生
劉富道
昨日風景
好人一個的戲劇人生
劉富道
我寫故去的一位同事,他在我們作家協會,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編輯,在職后期就做些雜事。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知識分子。還得再加個但是,據我觀察,他在職的最后幾年,很平常,很平淡,沒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那么,我為什么寫他?我覺得他的人生富有傳奇色彩,可以說是戲劇人生。
說他是戲劇人生,再貼切不過了,他一生的榮辱與戲劇相關。他曾經在中國戲劇家協會武漢分會工作,擔任會刊《武漢戲劇》編輯。上世紀50年代的劇協武漢分會,其實不屬于武漢市,而是屬于中南行政區。后來中南行政區撤銷了,有段時間交武漢市代管過,再后來演變為現在的湖北省戲劇家協會。當時漢口蔡鍔路19號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里面有劇協、音協、美協三個分會。1957年9月24日之后,他再也沒有來到這所房子上班了。他可以再次上班的時間,已經到了1980年6月7日。他注意到這一天的公文上稱他是同志,他回到同志的行列。
他隨后的工作,是參與湖北省文聯大院基建管理。現在的武昌翠柳街1號大院建成后,省作協從省文聯析出,1985年6月成為單獨建制的人民團體,他被分到省作協辦公室工作。我1986年元月來到湖北省作協上班,成了他的同事。他在花名冊上的大名為杜良驥,而他平時自稱杜良一,這就引起我的注意。問其故,答曰:“杜良一,好人一個。”他的身世我以前多少聽說過一些,他為海鷗劇社的冤案坐過12年牢,由于這種事情太多了,也就沒進入我的創作素材庫。
是什么讓我在意他的身世呢?他一次同我說起坐牢的經歷,不僅未作痛苦狀,反倒說得非常輕松。他說他坐牢,沒剃過光頭,可以穿皮鞋,可以經常上街,替管教干部買東西。在監獄業余文工團里,他集編劇、導演、演員于一身,可以表演獨唱,也可以當合唱指揮。每逢過年,他還帶文工團走出監獄,到鄰近鄉村演出。演出完了,村民們會送很多瓜子糖果和香煙,讓他們帶回監獄同獄友分享。他說得有滋有味,好像坐牢的不是他,他還在當他的編劇、導演和演員。他坐牢坐出不一般的情景。
杜良驥有戲劇科班出身的背景。原籍廣東南海縣,在鎮江出生,隨父到南京讀書。上高二就組織過跨校的“藝痕劇社”,劇社成員后來成名的有電影明星王蓓。他就讀于民國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表演系,學長鮑昭壽曾是中南人民藝術劇院的當家導演,正是鮑公1951年把杜良驥從上海招攬到了武漢。1954年杜良驥在武漢劇壇嶄露頭角,幫硚口一家軍工廠導演話劇《姐妹倆》,在全市職工匯演中獲得導演一等獎,演出一等獎。他總忘不了這些光榮歷史。

劉富道,湖北武漢奓山人,漢陽一中高中畢業。湖北省作家協會前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長江》叢刊主編。著有小說集、散文集、文學散論集、長篇傳記文學多種。主要獲獎作品有小說《眼鏡》《南湖月》《直線加方塊的韻律》,報告文學《人生的課題》,長篇傳記文學《天下第一街·武漢漢正街》。近作有長篇傳記文學《1957年中國大冤案——漢陽事件》全紀實文本。
還有更光榮的歷史。南京那個國立劇專,中共地下黨的活動非常活躍,杜良驥說他也是其中一員。只可惜他的光榮歷史沒給他帶來光榮,他正在尋找這段歷史證人的時候,已經被列入另一個名單。一天上班,偶然發現頂頭上司敞開的筆記本上,赫然寫著自己的名字。這是1957年,各地,各機關學校,各人民團體,都在努力完成右派分子的名額指標。他最終沒能證明自己是中共地下黨成員,卻要去充當一個右派指標,這豈不是太有戲劇性了。
1957年的國慶節就要到了,這一年的國慶對他來說,還有特殊的意義——他將在這一天舉辦婚禮,進入洞房花燭夜。幾天前的9月24日,他在深夜睡夢中被叫醒,糊里糊涂上了警車。1958年11月7日,作為海鷗劇社反革命集團案的成員之一的杜良驥,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宣判大會上,曾經朝夕相處的同事們,坐在臺下個個面面相覷:怎么,這些人就是隱藏在我們身邊的反革命分子?我們怎么一點兒也感覺不到呀!
4.選擇合適的教學技術。利用多媒體課件和網絡信息資源,做到“互聯網+課堂教學”,可以讓課堂教學全校同步,做到“班班通”,甚至“校校通”。
這是一個莫須有的冤案。這事我能說清楚,但需要太多篇幅,這里只說個梗概。1957年,中國劇協《戲劇報》編輯戴再民傳來一個信息,說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可以辦民間劇團了。此人原來就在武漢工作,與武漢戲劇界人士私交甚篤。武漢戲劇界有中南大區的背景,人才濟濟,受到這一信息的鼓動,就有人挑頭籌備成立民間的海鷗劇社。定這個社名是杜良驥的主意,他在劇社受聘為導演,參與了劇社章程的定稿。他說當時蘇聯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劇院有海鷗的標志。劇社籌建中,履行了報批手續,并沒有獲得批準,也就中止了籌備工作。就是這么個事兒。
這事怎么鬧大的呢,原來劇社領頭策劃人,聽說自己上了右派黑名單,就約了兩人南下廣州避風。一個星期天,三人相約來到漢口火車站,徘徊了好一陣子之后,各自悄悄回家了。也是因為反右風聲甚緊,領頭人不僅交待了劇社策劃過程,還交待了準備南逃一事。這下子就不是劃個右派的問題了。領頭人主動交代了,公開批判大會就沒讓他站臺,讓人得到了一個錯覺。逮捕好幾個人,卻沒有逮捕領頭人,也讓同仁們產生錯覺。領頭人直到宣判前不久才正式被捕,被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此乃弄巧成拙。受誅連者30多人,獲刑者7人。當時武漢市文化局長巴蘭岡也被撤職,到一家工廠去當車間副主任去了。
幾位武漢戲劇界精英準備放棄公職創辦民間劇社,不過是為了展示自己的一技之長,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何錯之有呢,又何罪之有呢?他們中間,還有幾位是中共黨員,包括領頭人。當今公辦劇團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走這條路,可惜他們走得太早了。
刑滿之后,哪里是他的歸宿呢?杜良驥被送到鄂西南一個山村。村里有個單身婦女,帶著五個孩子,丈夫在水利工地殉職了。大隊書記對這位“刑滿釋放人員”說,你去撐起這個家,有我在這里,保證沒人找你的事了。已經到了這一步,曾經的風流倜儻不再,還有不再被批斗的好事,還有天上掉下的一個家,什么編劇導演演員的角色都不再重要了,該放下身段了,就像在舞臺上一樣,杜良驥很快進入了角色。崎嶇的山路上,經常有他挑著糞桶的身影。他感受到,這里勞動強度,遠遠超過監獄里,但他必須撐起這個家。
武漢海鷗劇社一案,到1980年3月徹底平反了。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再審判決,沒有留下任何尾巴,不僅對全部被告“宣告無罪”,而且認定被告“策劃逃港問題,雖有錯誤,但未構成犯罪,原以逃港叛國定罪不當,應予糾正。”
本來已經沒事了,但1988年卻又有事了。當時出了一本《武漢通覽》,該書有《破獲“海鷗劇社”》一節,原封不動地摘抄了當年報紙上的公開報道,只摘引了“破獲”文字,只字未提已經“宣告無罪”。中國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制造冤案時有大張旗鼓的報道,平反冤案時卻悄無聲息地進行,也難怪《武漢通覽》的失誤了。杜良驥等人提出嚴正交涉。反正好人好說,得到一個公開道歉,也就算了。
杜良驥回來了,杜良一是他的筆名,也成為他的通用名,此舉表明他要告別昨天,重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有段時間舞會風盛行,年近花甲的他經常出現在舞場上。而且英雄不減當年,什么探戈、吉特巴一場不拉,引來女士們爭相邀請。他有時還要唱一嗓子,帶美聲唱法的歌喉,總會引來滿堂喝彩。在大院里只要見到他,他就是騎在摩托車上,英姿颯爽地一副大忙人形象。他還是一個驢友,經常與人結伴騎摩托車旅游,最遠到過重慶成都。退休之后,他受聘在一報一刊又工作了14年,直到進入75歲才閑下來。他還在內蒙古導演過一部電視劇。
當時我是省作協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般而言,在這個職務上,沒有人自己給自己寫總結報告稿。我自己寫也沒圖什么表揚。我如果不是上樓清理資料,直接回家休息,也沒人知道我回機關來了。如果不是一遍又一遍請我,我也不會到場去跳什么舞。這樣想下去,就會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后來我想,杜良驥受那么大委屈,他不是一笑了之嗎。算了。
再說杜公的戲劇人生。他稱他當年的女友為玉,玉在苦等8年之后成家了。當年的小杜帶著同玉的結婚照入獄,這張照片一到監獄里,就被派來搜身的犯人搜走。這對杜良驥精神上是一個沉重的打擊。10多年之后,那個老犯人出獄了,小杜成了老杜也出獄了,那個老犯人居然把這張照片送還他了。老杜跟我說,他不知道老犯人的用意,他為什么要保存這張照片。2003年,這張照片出現在《楚天都市報》的“觸摸老照片”欄目上,有簡要的文字說明,道出了老杜的這段往事。我問杜公,玉看到了嗎?杜公說看到了。我再問,玉會不會反感?杜公答,沒有啊。玉很同情他,很懷念過去,但只有一聲嘆息。
2003年冬季,杜良驥交給我一篇手稿,讓我隨便幫他怎么處理都行。這就是刊登在《武漢文史資料》2004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標題是《1957年“海鷗劇社案”內幕》。原稿涉及當時一些健在的人士,我完全可以找個理由推辭回避,但覺得如果這樣想,那我還是一個襟懷坦白的共產黨人嗎,我還是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作家嗎?我幫他把文章輸入電腦,同時做文字編輯工作,把所有繁體字改成簡體字,加入幾個小標題,忙乎了一個星期,得到他的認可。經與編輯部徐雙明先生聯系,他非常痛快地說,明年第一期已經編好,我撤下一篇稿來,馬止刊載出來。星期天我到郵局發特快專遞,寄出打印稿和軟盤,星期一就到了徐雙明手上,不久雜志就出來了。
有幾百元稿酬,杜公要分我一半,被我拒絕了。當時我說了一句連我自己都大為驚訝的話——
我說:你受了那么多苦。
(我怎么能要這個錢呢!)
他說:那也不是因為你。
(那時候我的頂頭上司并不是你呀!)
我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以我黨一員的名義,向你謝罪。
每當我同人談起杜良驥,談起我們這段對話,我都會眼淚汪汪的。
兩年后的2006年6月20日,杜良驥同志謝世了。我在他的靈柩前想到,好人一個的戲劇人生終結了,如果不是命運對他不公,他的名字會在名編劇或名導演之列。好在有他的文章發表出來,海鷗劇社真相已經大白天下。
縱覽文學現象博采百家新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