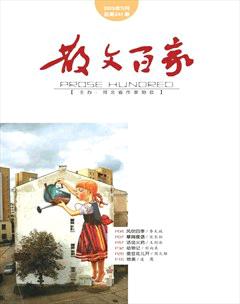淺析魯迅作品《藥》的思想內涵與環境襯托
蒙 利
貴州省獨山縣高級中學
淺析魯迅作品《藥》的思想內涵與環境襯托
蒙 利
貴州省獨山縣高級中學
《藥》是魯迅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在魯迅先生整個的創作活
動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作為一篇成功的小說,《藥》真實地再現了那個特定的時代所特有的風貌,蘊意深刻,回味無窮。
魯迅的小說,總體來看,具有一個特點,也就是“為人生”出發,表現了“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以最平凡的事件來描寫最不平凡的思想,以此成為中國社會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他的小說比較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義的罪惡,反映了處于經濟剝削和精神奴役雙重壓力下的中國民眾特別是農民生活的面貌,描寫在激烈的社會矛盾中苦苦掙扎著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而《藥》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它深刻地展現了中國舊城鎮普通人的生活,來對黑暗的舊世界作了最徹底的揭露。思想深刻,人物形象鮮明,反映了當時的真實的社會現實。《藥》寫的是茶館主人華老栓買人血饅頭為兒子小栓醫病的故事。故事簡單,但蘊涵深刻,以此來揭露封建統治階級長期以來麻痹人民并使得他們陷入愚昧和無知的深淵,最終的結局是:小栓并沒有因為吃了“人血饅頭”而治好自己身上的疾病,而是最終成了這個時代封建迷信的犧牲品。在小說中,作者還把被吃的犯人安排為一個革命者,頗為奇特,這是一位沒有正式出場的革命者,盡管他愿意為民眾獻出自己的生命,愿意用自己的一腔熱血來拯救這個世界,但是人民不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為大家而吃苦,而流血,反而成了封建迷信的犧牲品,被活活吃掉,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悲哀,如果說,小栓之死是一個悲劇,那么夏瑜的死則更應該是一個大悲劇。魯迅既痛心于民眾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覺醒,更感慨于資產階級革命的脫離群眾,脫離現實,這就使小說的主題含有雙重的悲劇性。《藥》帶給人的感覺是沉重的,然而它所描寫的內容卻代表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總特征。盡管如此,在小說最后出現在革命者墳墓上的花環,就顯出了若干的 “亮色”,透露了代表時代特征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藥》給人的感覺是沉重的,但它所表達的這種沉重感并沒有壓倒民眾,總是在呼喚著人們起來拯救這個黑暗世界,找出醫治這個不平世界的良方妙藥,解救這個“吃人”的社會,這也是魯迅創作這篇小說的良苦用心。
如果說《藥》的思想內涵是極為深刻的,那么,它的環境的描寫更不可忽略。
小說的環境描寫襯托主題在小說一開始,魯迅就安排了一個不尋常的時間來渲染、烘托不尋常的環境:“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除了夜游的東西什么都睡著。”沉寂、陰森的環境,可是,華家小茶館里的店主人卻還在不停地忙碌著,顯然預示著有不尋常的事情將要發生:小栓病重,華家正為找藥用盡腦汁,突現了尋常百姓家所發生的不尋常事。接著,寫到了不尋常的殺人刑場丁字街的環境,突出其恐怖、殺氣騰騰。華老栓冒著風寒來到這個令人恐怖的地方,這就巧妙地把華家與夏瑜被害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即為了得到“人血饅頭”,華家買人血饅頭,夏瑜的血被賣、被吃,由此突出了主題,也照應了標題“藥”,再寫一群看客去看殺頭湊趣,最后寫到老栓得到人血饅頭之后的感受。這樣,在一個不平常的夜晚,一個不平常的地點,發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件——殺人。通過一系列的情節,這一典型的環境描寫,魯迅就把整篇小說的內容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以此,深刻地揭示了舊中國下層社會的一個側面,一個縮影,善良的民眾如華老栓這些受壓迫、受欺騙的人們,竟把沾著革命志士的鮮血的饅頭當做藥來醫治自己的身體,就為具體地體現小說的意義作好了準備。
在小說當中,第二個典型的環境描寫,應當是茶館的環境描寫,一個小茶館就是一個大社會。茶館,它可以是下層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聚集的場所,也是人們議論是非、傳播新聞的所在,它所經歷和代表的一切很廣泛。魯迅就是通過茶館這樣一個小小的空間,又把一個家庭和社會結合了起來,閑得無聊的茶客,麻木不仁、趨炎附勢、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百般討好劊子手康大叔,議論夏瑜,甘當封建統治的幫兇;劊子手康大叔趾高氣揚、驕橫傲慢、、仇視革命;華老栓一家渾渾噩噩,對統治者唯唯諾諾。夏瑜被吃,人們無動于衷,甚至加以嘲弄。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茶館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構成了封建統治的下層社會基礎,也揭示出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去做喚醒民眾的工作,不去徹底動搖并摧毀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而僅僅滿足于趕跑了一個皇帝,這就注定了這場革命必然要遭到失敗的結局。革命者的鮮血白流了,可是解放民眾、拯救世界的重任仍然還非常艱巨,愚昧的民眾仍然需要更大的努力從根本上來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一個茶館,一群人,就巧妙地把華、夏兩家結合在一起,說明殺害夏瑜的不僅是劊子手康大叔,而且還有整個社會,找出這個社會的病結,才是“醫”病的關鍵。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墳場周圍環境的描寫。吃人的華小栓與被吃的夏瑜都被這個吃人的社會吃掉了。魯迅以悲劇始又以悲劇終,他寫的墳場一開始就籠罩著一種低沉、凄涼的氣氛:“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在清明,這樣一個帶有獨特意味的日子里,華小栓和夏瑜死后葬在同一墳地,“那墳和小栓的墳一字兒排著,中間隔著一條小路。”這種巧合,是華家和夏家兩家悲劇的匯合點,明線和暗線的結合。可見,兩人走的路雖有不同,卻是同一命運,但兩人死的意義卻不同:前者平庸,默默無聞,除了家里人來上墳外,無人來吊祭他;后者偉大,影響深遠,除了家里人上墳外,畢竟還有覺醒了的人來獻花圈悼念致敬。那花環、那寂靜的墳場,表明夏瑜的血是不會白流的,未盡的事業,后繼有人。既是作者的一種期盼,也是作品主題能產生更強烈的震撼人心的魅力之所在。
總起來說,《藥》這篇小說,它的環境、情節、人物等等,都是緊緊地圍繞著“藥”的主題來表現的,給人留下了很多思考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