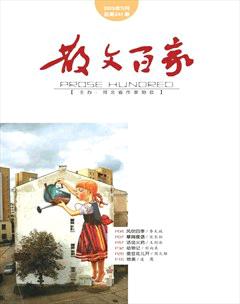讀寫一體化下的審美形式
蘇敏娜
河北省圍場縣四合永中學
讀寫一體化下的審美形式
蘇敏娜
河北省圍場縣四合永中學
社會的飛速發展造成了人們審美意蘊的喪失,審美感受的鈍化。如何使受教育者重獲審美意蘊是語文教學急需解決的問題。讀寫一體化的語文課堂教學是重獲審美意蘊和培養審美感受的重要途徑,是教育中審美創造的獨特審美形式。
讀寫一體化;審美創造;審美形式
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21世紀,高科技被廣泛運用,人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舒服,越來越美好。然而,這繁華的背后,卻是人們審美意蘊的喪失,審美能力的鈍化。最突出的表現則是文化的機械式復制,形象的物質式包裝,感官的刺激式追求。因此,當代教育也面臨著極大地挑戰。培養出具有個性創造力和審美想象力的人才是當代教育的主要任務。語文教學則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何使受教育者重獲審美意蘊是語文教學急需解決的問題。讀寫一體化的語文課堂教學形式是重獲審美意蘊和培養審美感受的重要途徑,是教育中審美創造的獨特審美形式。
如果說藝術中的審美創造,是探討藝術美生成奧秘的關鍵所在,那么它必然離不開形式,因為,沒有形式就沒有藝術品的本體存在。與其說是審美創造,不如說是審美形式的創造。“形式”是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他在貶損再現藝術對生活的拙劣模仿的同時,卻推崇印象派畫家塞尚的成功,認為“塞尚是發現’形式’這塊新大陸的哥倫布”,“他創造了形式,因為只有這樣做他才能獲得他生存的目的——即對形式意味感的表現。”[1]符號學家卡西爾、蘇珊·朗格將藝術形式歸結為符號的創造。法國現象學美學家杜夫海納將“形式”視為“在知覺中完成的審美對象的形式”,并且說,“在藝術中,形式給予意義的存在。當感性全部被形式滲透時,意義就全部呈現于感性之中”。[2]對于形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卻又有同一特點,即賦予形式以本體地位。正如,“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轉動整的地球”,這個支點就是形式。
若藝術中的審美創造,只能從藝術家自身尋找根據,那么,教育中的審美創造則應從教育者、受教育者自身找根據。清人鄭板橋對這一審美創造理解的非常透徹: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霧氣,皆浮動于疏技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在鄭板橋看來,畫竹是一個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的雙重轉化的動態過程。眼中之竹是客觀物象的反映,胸中之竹是藝術家的醞釀與藝術構思的結晶,這是由外而內的轉化過程。而手中之竹又不同于胸中之竹,是因為由內而外的轉化過程中,使胸中之竹增生了新質。語文教學亦是如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想要從既定文本中獲得審美經驗,首先要對既定文本進行審美創造,審美創造的形式則是理解文本,獲得獨特情感體驗的關鍵。在中學語文教學中,讀寫一體化則是重要的審美創造形式。
就教育者而言,對讀寫一體化的美學形式的運用集中體現在備課上。從傳達的角度來看,備課實際是審美形式的一種再創造。備課不是僅僅靠心靈的直覺就能完成,它需要借助感性材料和認知途徑。語文教學則是將語言作為文學材料,具有特殊性。語言藝術中的形象首先是訴諸心靈的想象中的形象。但由于語言自身的性質往往影響文本意義的實現。這就要求教育者在備課的過程中,既要保留文本的感性特征,又不是原材料的照搬,而是傳達教育者獲得的審美經驗。然而教育者審美經驗的獲得,需要借助讀寫這一審美形式。在備課的過程中,對文本進行反復精讀,圈點勾畫,并借助其他文本資料,透徹的了解筆者的創作意圖,進而才能獲得自己的情感體驗和認知。教育者根據自己的情感體驗和認知,借助已有的教學經驗,設計教學方案來表達文本的審美價值。同樣,受教育者想要從文本中獲得情感享受,也需要借助讀寫一體化這一審美形式。受教育者在教育者構建的具有詩意美和歷史厚重感的語文課堂中,不是對教育者情感經驗的照搬,而是在教育者情感經驗的引導下,反復品讀文本,通過對文本藝術性的審美創造,深化對文本的理解,激活自身思維,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感悟,并將這獨特的感悟進行文本在創造,從而獲得主體內在的審美需要。
黑格爾說:“內容非他,即形式之轉化為內容;形式非他,即內容之轉化為形式。”[3]讀寫一體化這種審美形式里積淀著理性內容,滲透著文本背后筆者的生活經驗,人生理想與審美期待,因此是有意蘊的。借助有意蘊的的途徑來學習語文,才可獲得有意蘊的美學享受。也只有這樣,語文課堂才能是生成的,詩意的,具有藝術性的課堂。
[1]克萊夫·貝爾著,周金環等譯:藝術[M],第141、143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84年。
[2]杜夫海納著,孫非譯:美學與哲學[M],第173、13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3]黑格爾著,張世英譯:小邏輯[M],第52頁,北京,商務藝術館,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