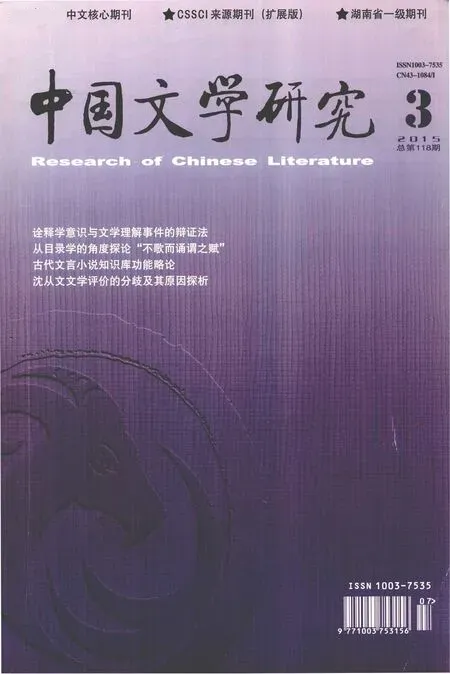探尋民間宗教與小說關系研究的新路徑——評易瑛《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小說》
陳進武
(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13)
從中國文化形態構成來說,巫文化不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而且還對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從巫文化的發展演進來看,巫文化已經從最初的民間宗教信仰轉化成了一種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滲透到了民族的骨髓。對于巫文化的研究,學術界已經作過較為深入的研究,也產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上世紀30 年代,陳夢家的《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等論文就著重探討了商周時期的巫術。新時期以來,有學者討論了上古巫術思維與楚辭的關系,有學者則著重考察了作為神秘文化核心的巫文化。不難看出,研究者對古老的巫文化的興趣始終方興未艾。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有學者從個案視角探尋了作家與巫文化的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關于中國新文學與巫文化的整體互動關系這一論題,卻較少有學者涉及。即便有些論者也涉及過,但大多是簡單事實的羅列,而對于巫(巫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詩性以及這種詩性的文學表現的分析,往往沒有涉及,而或多或少有涉及的也多是語焉不詳。
從上述意義來說,易瑛博士的新著《巫風浸潤下的詩意想象——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小說》(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深入探討了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關系問題,從巫文化這一角度切入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藝術本體之中,運用充分的細讀與分析手段對于民間宗教與20 世紀中國小說的關系進行了獨特的審美與理論研究路徑的建構,尤其是將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巫的詩性力量體現的學理空間上升到了新高度。這既為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提供了新理念與新方法,又為民間宗教與小說的關系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借鑒與啟示。當然,這部著作的可貴之處也正如當代學者譚桂林在該書序《文學離不開巫性的詩意與迷狂》中所言的,這部著作不僅清晰勾勒了“20 世紀中國文學中巫的詩性力量的體現圖景”,而且“對于20 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巫文化現象的梳理,其資料之翔實、分辨之細致、理路之清晰,可謂前所未見,而其對于巫性思維的詩性力量在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各種體現的分析,不乏閃射著作者自己獨到的藝術穎悟與生命體驗。”
在詞源上,“巫”即“祝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原本指稱能以舞降神的人。鑒于中西方學者對“巫術”界定的不一致,著者經過仔細辨析后認為,巫術既是行為狀態,又是信仰系統,“是指人類試圖通過某種儀式、利用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對客體加以影響或控制的行為方式”,包括完成巫術行為的人、巫術儀式和巫術意識等三個基本要素。而“巫文化”是指“以巫師、巫術及鬼神信仰為總體特征的文化,又被稱為巫鬼文化、神巫文化、巫儺文化或薩滿文化。”由此可見,著者從一開始用分析方式對“巫”及其相關概念的自身譜系進行了追根溯源,并辨析與界定了“巫”、“巫術”與“巫文化”等核心概念。盡管這些理論界定在某種意義上屬于“一家之言”,但透過分析正顯示了著者的扎實與穩健。
該著以20 世紀的中國小說為研究對象,將小說置于巫文化的視野中進行考察。著者自始至終站在分析的視角,運用分析的手段,并且在對于具體小說文本的解讀與分析中來呈現問題、解決問題。比如,探討現代小說家理性上的啟蒙主義和藝術上的近巫傳統之間的主體悖論及其呈現出的藝術張力問題。著者既從魯迅《祝福》、巴金《家》、陳煒謨《夜》、魯彥《菊英的出嫁》、閻連科《耙耬天歌》等小說中發現啟蒙者對巫術信仰的理性批判,又洞察到受到心靈創傷的啟蒙者在這些創作中潛藏在最深處的巫鬼信仰的情感慰藉。可以說,著者對啟蒙敘事與巫文化呈現出的這種“啟蒙”與“審美”糾纏狀況的探索,無疑是建立在有效的分析基礎之上的獨到發現。著者對少數民族文學與巫文化的“詩性”與“神性”的追尋、政治敘事與巫文化的革命訴求下的“對立”“合謀”和“流離”、尋根文學與巫文化的“尋根”與“尋巫”的交融,以及先鋒小說與巫文化的“現代”與“傳統”的對接等現象的揭示,都是得益于這種精細的分析。
著者在提出自己的相關觀點時,并不僅僅是從橫向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分析,而且還從縱向上對小說與巫文化的關系變遷作出解釋,以此保證了自身論述體系的細致、獨到與嚴密,顯示出了該著較強的邏輯性。為合理呈現出巫文化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歷時性變化,著者引證了大量第一手相關理論與小說文本材料,用豐贍的材料說話。她收集了大量的理論著述和20 世紀中國小說中有關巫文化的材料,尤為細致地將原本顯得零散的材料累積起來,并且進行了有機的融合,由此來系統、翔實地論證所提出的觀點。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有關巫文化的材料,還是相關的小說文本,無不是資料浩繁,復雜紛亂,但著者巧妙地化繁為簡,將這種復雜關系分為啟蒙敘事、少數民族文學、政治敘事、尋根文學與先鋒小說等專題,分別論述與論證,從而顯示出清晰的線索與思路。
著者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所建構的體系并不僅僅是純粹的文本分析。在她看來,這種關系的研究就是要“將以往對某一作家或某一地域作家的小說創作與巫文化的關系的個別性研究,提升到對‘巫文化影響下20 世紀中國小說’的整體性研究,全面梳理20 世紀由傳統向現代嬗變的文化轉型期,中國現當代作家對巫文化重新選擇的同與異,追溯與辨析巫文化在20 世紀小說中存在方式的歷時性變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能以種種隱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試圖對巫文化影響下中國現當代作家參與20 世紀中國民族文化建構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審美經驗的創造進行歸類分析和系統考察。”從選擇的幾個切入點來看,著者有效地揭示了巫文化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緊密關系。她以20 世紀中國小說文本為中心,采取點面結合,仔細梳理了思想特征(審美探尋)與巫文化的關系,尤其是對于中國現當代小說和巫之詩性的聯系進行了深層的探究。
從方法論上看,著者的這種整合還體現在她對諸多學科理論方法的借鑒和綜合之上。雖然著者對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考察是以小說文本為中心,但她突破了以往局限于小說的思想、主題、人物、情節等的研究模式,而是從巫文化的視野出發,緊扣巫文化本身與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具體內容,充分運用了宗教學、人類學、神話學、民俗學、心理學和文藝美學等學科研究成果及理論來分析與整合小說作品和文學現象。簡要梳理,我們會發現,該著涉及的西方理論主要有弗雷澤的巫術理論、榮格的人格分析心理學、列維·施特勞斯的人類學理論、卡西爾的人學理論、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學理論、巴赫金的詩學理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諾依曼的原型分析理論等。而著者參考的國內相關研究著作也是相當豐富的。從表面上,該著的理論涉及相當龐雜,但從深層來看,一方面,著者并非機械地以某種理論分析某個小說文本或文學現象,而是特別注重在相關理論融合的前提下以研究主題為核心對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詩性進行科學歸納與分析。另一方面,盡管著者在立論和方法上多借鑒西方資源,但她又并非一味沉溺于“西學”難以自拔,而是將中西相關理論加以整合并結合小說文本和文學現象言說。
這種融合眾家之長的研究方法無疑使得這部著作有效避免了研究思維的局限,既對小說作品進行了有新意的解讀,開辟了小說文本研究的新路徑,又顯示出了該著邏輯結構的嚴謹性,增強了理論觀點的可靠性。更為重要的是,著者這種將多種理論和研究方法的交錯使用,也促使她借此提出了諸多創造性的觀念或見解。比如,關于啟蒙敘事與巫文化的問題,著者敏銳發現啟蒙者在質疑與批判被認為是反理性與反現代的巫文化的同時在情感上卻又存在著難以割舍的寄托與慰藉。又如,對于政治與巫文化的關系,著者又察覺到了兩者的微妙關系,亦即巫文化與政治“有時是敵對、有時是同謀,在夾縫中得以延續下來。”再如,對于上世紀80 年代的“文化尋根”現象,著者又發現了當時及其后一批作者的文學創作,并不僅僅是“尋根”,同時也是一種“尋巫”的探索。由此可見,著者將相關的理論思考與具體的小說文本分析有機融合,透過她的理性分析與整合,涉及的許多小說得到了某種全新解釋,而不少觀點更是發他人所未發。可以說,透過這部厚實的著作,我們找尋到的并不僅僅是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精神聯系,而且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不同階段的復雜性與深刻性,也會獲得更為深入的體認。從這一意義上來講,易瑛博士的這部著作其實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文學與文化的關系研究,而是達到了更為深層的研究目的,這種探尋也為當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拓展了新的研究視野。
不可否認,巫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共同話題,而巫文化和中國現當代小說的關系研究同樣是有著極強的延展性的課題。對于這樣的高難度的重大命題,易瑛博士的這部著作也并非完美無缺的,盡管她把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小說的關系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正是在這種提升中能夠察覺到對于這一問題還有進一步開掘的余地,還有不少亟需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實際上,著者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她在“后記”中這樣說到,“在研究的過程中,我不斷產生新的困惑,如巫術儀式與文學的關系、巫文化對中國戲劇的影響、中國巫文化與西方巫文化比較等問題,還有待今后進一步探討。”〔1〕然而,略有遺憾的是,雖然該書是以中國現當代小說為考察中心,又試圖對其作出歷時性分析與闡述,但在具體作品的選取與分析中并未能完全達成這一研究目標。不過,在我看來,面對龐雜的材料與有限的著述篇幅,該著的這一不足也正是目前研究者難以避免的。
總的來說,該著為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民間宗教與文學的關系研究開辟了新的思維空間與新的研究路徑。盡管這種研究體系的構建和原創性觀點的提出,尚未成為一種學術共識,但是對于這一重大命題的完善與突破,以及著者的質疑、辨析、探索與發現其本身無疑就是一種獨特的貢獻。
〔1〕易瑛.巫風浸潤下的詩意想象——巫文化與中國現當代小說〔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