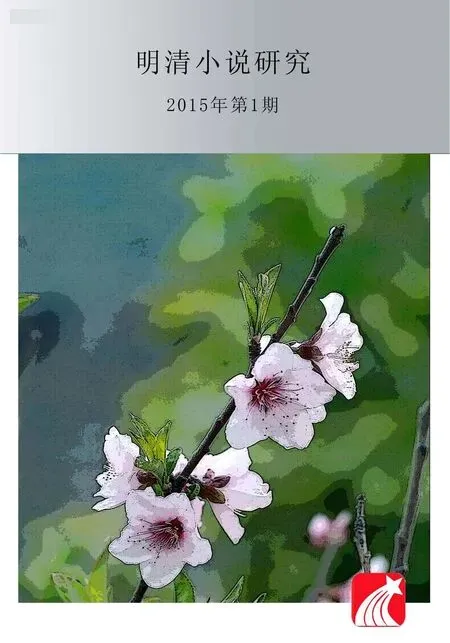論古代小說中的離別場景
論古代小說中的離別場景

·李萌昀·
摘要
離別是中國詩歌的重要主題。隨著詩歌傳統的日益深厚,離別詩歌逐漸形成了一些模式化的情感套路和寫作方式,而詩歌本身的第一人稱抒情傳統和高雅化的文體性質也限制了文人對離別題材之可能性的探索。古代小說同樣有著離別書寫的悠久傳統。由于文體差別,小說中的離別場景有著自身的特色,或詩化、或戲劇化、或寫實化,與離別詩歌相映成趣。同時,離別也在小說的情節建構中發揮著重要的鋪墊作用。比較詩歌與小說對離別的不同書寫,不是為了給出一個孰優孰劣的評判,而是希望在比較中探討每一種文體的獨特性與可能性,并對其書寫傳統加以總結和分析。關鍵詞
古代小說離別場景文體離別是中國詩歌的重要主題。從《詩·邶風·燕燕》中的“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到《古詩十九首》和“蘇李詩”,再到近體詩時代浩如煙海的離別歌詠,中國詩歌形成了離別書寫的悠久傳統。然而,隨著詩歌傳統的日益深厚,離別詩歌逐漸形成了一些模式化的情感套路和寫作方式,而詩歌本身的第一人稱抒情傳統和高雅化的文體性質也限制了文人對離別題材之可能性的探索。與詩歌相比,古代小說中的離別場景同樣淵源有自,特色鮮明。從形式上說,古代小說“文備眾體”,以散文為主,兼有韻文,對離別的表現較為靈活,且可以吸收詩歌的意境為己用。從內容上說,古代小說雅俗兼備,以俗為主,題材相對豐富。從表達方式上說,古代小說以第三人稱敘事為主,與詩歌的第一人稱抒情相比,形成了另外一種離別場景的描寫范式。
古代小說中的離別場景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為詩化的離別。此類場景一般出現在文言及才子佳人小說中。小說家在散文描寫中引入詩歌,營造出濃重的詩意色彩,在情感表達上偏于高雅化和文人化,與離別詩歌的意境較為接近。古代小說中最早的離別場景當數《穆天子傳》中的瑤池之別和《燕丹子》中的易水之別。在這兩個場景中,詩歌都起到關鍵作用。《穆天子傳》卷三云: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群,于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周穆王將要告別西王母,繼續自己的旅行。離別的宴席上,西王母賦詩表達內心的惜別。“白云”兩句既是起興,又可以看作是對穆王西行的比擬。“道里”兩句寫出兩人相距之遠,路途之艱,相見之難。“將子”兩句則坦率大膽地表示出對再見的期待。面對西王母的邀請,周穆王同樣選擇用詩歌來加以回答。相對西王母詩中明顯的個人化情緒,周穆王詩充滿著對帝王責任的強調。雖然許下了三年之約,但卻是以“萬民平均”為前提的。小說家通過離別詩歌的對比刻畫出中土與西域、男性與女性面對離別的不同反應,體現出文化與性別的深刻差異。
但是,《穆天子傳》的離別場景是完全建立在詩歌之上的,缺乏對人物動作、神態等細節的具體描寫,近似于一幅靜止的畫面。相比之下,《燕丹子》中的易水之別則生動許多。《燕丹子》卷下云:
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為壯聲則發怒沖冠,為哀聲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
此場景的核心是著名的《荊軻歌》,慷慨悲壯,氣勢磅礴,將整段文字都籠罩于其營造的悲劇氣氛之中。然而,小說家卻沒有完全依賴于詩歌的意境,而是在散文部分設置了一連串動作性詞語,如“擊筑”、“和”、“發怒沖冠”、“流涕”、“升車”、“不顧”等。這些動作性詞語與詩歌意境相輔相成,使整個場景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燕丹子》的作者靈活運用散文和韻文的各自特點,超越了《穆天子傳》,大大提升了離別描寫的藝術水平。
在通俗小說中,詩化的離別場景大多集中于才子佳人小說之中。這些場景雖然同樣韻散兼備,但是格調纖弱,筆力綿軟,因而場景中的動作性較為模糊,往往淪為詩歌的附庸。如《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嬌鸞百年長恨》寫才子與佳人的離別:
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畢集,為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傷欲泣,潛歸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伺便投之。章于馬上展看云……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鸞也。
這段文字雖然亦多動作性詞語,但實際上都是離別詩歌的鋪墊,散文與韻文之間并未起到互相輔助的作用。因此,此一場景中的感情顯得豐沛而造作,影響了人物性格的塑造。
第二類為戲劇化的離別。此類場景以一個戲劇性的細節為核心展開情節,節奏緊湊,富于懸念,人物形象和離情別緒在對此細節的層層凸顯中得到生動呈現。魏曹丕《列異傳》載望夫石的傳說: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這段文字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戲劇化離別場景,作為場景核心的是“形化為石”的細節。貞婦在送別丈夫時形化為石,有著雙重的含義,既是望著丈夫遠去,同時也是望著丈夫歸來。換句話說,望夫石是一個凝固的情感符號,既象征著對丈夫離去的不舍,同時也象征著無窮無盡的思念。妻子的生命永遠定格在離別的剎那,直到丈夫的歸來。“遠赴國難”為妻子的這一凝望提供了一個悲壯的背景,為國從役的丈夫很可能戰死沙場。“形化為石”這一戲劇性細節雖然具有神異色彩,但卻是人民樸素感情的凝結,因而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再如唐孟棨《本事詩》“徐德言”條中的破鏡之別: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
這一場景以“破鏡”的細節作為核心。銅鏡與人事之間構成一種映射關系,鏡的破碎象征著人的離別。殘缺的銅鏡構成一種思念的憑據,也隱藏了一種重逢的希望,這正體現在徐德言夫婦賣鏡之約所包含的那種堅持和信仰當中。
通俗小說中也常見戲劇化的離別場景。例如《西游記》第十二回《玄奘秉誠建大會觀音顯象化金蟬》中玄奘與太宗的離別。離別之時,太宗突兀地遞給玄奘一杯酒。戒酒是包含在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之中的,作為篤信佛教的皇帝卻賜酒給僧人,的確有些匪夷所思。因此,玄奘回答道:“陛下,酒乃僧家頭一戒,貧僧自為人,不會飲酒。”太宗回答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餞之意。”玄奘只得受了。這一來一去,構成了第一層戲劇性沖突,但這只是開始:
只見太宗低頭,將御指拾一撮塵土,彈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這一去,到西天,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進此酒:寧戀本鄉一捻土,莫愛他鄉萬兩金。”
小說家層層設伏,抽絲剝繭,直到最后才把謎底揭開,引出“寧戀本鄉一捻土,莫愛他鄉萬兩金”的道理。整個過程節奏明快,富于戲劇性,且與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相呼應,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第三類離別場景的界定較為模糊,不像上兩類那樣特征鮮明,姑且稱之為寫實化的離別。這一類場景既不以詩歌營造氣氛,又不以戲劇性的細節吸引讀者,而是純以敘述的筆調摹寫離別情境,再現日常生活中的離別現場。在詩化和戲劇化的離別場景中,主人公大多為帝王、英雄、才子佳人,而在寫實化的離別場景中,題材較為開闊,更能觸及市井細民的生活狀態。寫實化的離別場景還可根據主題的差異細分為兩種:一種可以被稱為人情式離別,如《古今小說》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照世杯》卷三《走安南玉馬換猩絨》等;一種可以被稱為倫理式離別,如《古今小說》卷十八《楊八老越國奇逢》、卷四十《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等。前者將“情”的因素擺在突出的位置,后者則更加強調“理”的意義。
人情式離別的典型作品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故事的開頭寫王三巧兒與丈夫蔣興哥的離別場景。為了突出夫妻離別的不舍和傷感,小說提前做足了鋪墊。首先是對二人感情的渲染。二人成婚后“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夫妻情深是離別艱難的基本前提。之后,小說家又描寫了幾次“失敗的離別”:
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后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舍不得,兩下凄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
夫妻恩愛竟然使商人數次放棄了出行的打算,在家中消磨了一年又一年。經過兩重鋪墊,最終的離別變得格外刻骨銘心:“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瞞過妻子而定下長行的日期,并非薄情的表現,因為蔣興哥心里清楚,如果與妻子商議,定會重復“凄慘一場,又丟開了”的循環。于是,他硬起心腸,在臨行前才告知妻子,并講述了一番“成家立業”的大道理。然而,他內心的柔情在和妻子議定歸期時便暴露無遺:
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著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著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里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
小說家在此處精確地刻畫出丈夫和妻子不同的情感表達方式。相對于妻子的坦率來說,丈夫的情感表達顯得極為含蓄,“甚不得已”四字隱含了無限的眷戀。“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的細節可謂神來之筆,離愁別緒盡在這無言的動作當中。天亮以后,蔣興哥出門在即,開始最后的布置:
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后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個丫頭,一個叫晴云,一個叫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
這段文字既沒有苦心營造的詩意氛圍,亦沒有精心設計的戲劇性細節,甚至沒有刻意對人物感情多加渲染。然而,這一項項看似平凡的打點安排,卻真切地體現出丈夫對妻子的信任(“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體貼(“留一個老成的在家”)和關愛(“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也使之前的“分外恩情”落到了實處。
和人情式離別場景對“情”的凸顯相比,倫理式離別場景更重視“理”的實踐。在傳統中國,“居”與“游”并非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復雜的社會行為:人們需要根據自己的社會角色做出相應的選擇。離別是“居”與“游”之間的轉換,因而可以最為典型地體現出人們在“居”與“游”面前的倫理選擇。以《楊八老越國奇逢》為例。故事開頭寫楊八老欲出門經商,與妻子告別:
一日,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事日漸消乏。祖上原在閩、廣為商,我欲湊些貲本,買辦貨物,往漳州商販,圖幾分利息,以為贍家之資,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李氏道:“妾聞治家以勤儉為本,守株待兔,豈是良圖?乘此壯年,正堪跋踄,速整行李,不必遲疑也。”八老道:“雖然如此,只是子幼妻嬌,放心不下。”李氏道:“孩兒幸喜長成,妾自能教訓,但愿你早去早回。”
此場景與蔣興哥夫婦之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相對后者的依依不舍、怨離惜別,此場景著重表現的是“居”與“游”面前丈夫與妻子的不同責任。中國古代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外出經商、養家活口是丈夫的本分,而留守家園、教育后代是妻子的責任。因此,在丈夫提出往南方經商時,妻子沒有像王三巧兒那般“兩淚交流”,而是引用了“治家以勤儉為本”的古訓,勸丈夫“速整行李,不必遲疑”。“自能教訓”既是妻子對自身能力的表白,也是對自身責任的確認。
再看《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秀才沈小霞的父親和二弟被奸人害死,自己也將被解往京城。小說家描寫了沈小霞與妻子孟氏和小妾聞氏的離別場景:
沈小霞帶著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為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著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著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卻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了沈氏香煙。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幾時,等待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
在離別之時,沈小霞雖然悲傷,但他真正關心的卻是自己離開之后的家庭倫理問題。首先是貞節問題。自己如遭不幸,妻子必須守貞,妾則可以再嫁。沈小霞稱妻子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是對妻子的撫慰,更是對妻子的提醒。其次是后嗣問題。古語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因此,雖然妾沒有守貞的義務,但是由于她已有身孕,沈小霞仍然請求妻子照顧她直到孩子出生。小妾聞氏卻不滿丈夫的安排。古代倫理雖然對妾的貞節沒有嚴格的要求,但是對自愿守貞的妾仍然是相當鼓勵的。聞氏不但拒絕改嫁,而且提出“情愿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她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可見,小妾具有對丈夫、對正妻的雙重責任。在這種場合,正妻由于身份的尊貴,自不能蓬首垢面、一路陪伴,小妾則沒有那么多禁忌。由此可見,“理”構成了這一離別場景的核心。相對人情式離別場景來說,倫理式離別場景通常具有較為濃厚的說教色彩,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趣味性和藝術性的缺乏。相反,倫理式離別為不同的思想觀念、不同的倫理選擇提供了一個對比乃至論辯的舞臺,成為剖析整篇故事之觀念系統的樞紐之處。這一點在下文將展開說明。
離別場景在旅行故事的整體情節建構中起著重要作用,往往包含著情節發展的諸種暗示。換句話說,鋪墊是離別場景最基本的情節功能。離別場景的鋪墊方式可以分四種:伏筆式鋪墊,對比式鋪墊,關鍵物式鋪墊,論辯式鋪墊。
伏筆是離別場景之中最常見的一種鋪墊方式,小說家通過人物在離別時的某些話語和行為為下文的情節發展做好準備。這些話語和行為在離別場景中顯得平淡無奇,但卻會隨著情節的逐步發展顯示出其真正的含義。《石點頭》卷一《郭挺之榜前認子》寫郭喬與青姐的離別。郭喬在外游歷時納青姐為妾,返家之前,青姐告知郭喬自己“已懷五月之孕了”,因此,“賤妾可棄,此子乃相公骨血,萬不可棄”。郭喬于是“預定一名于此,以為后日之征”:“世稱父子為喬梓,我既名喬,你若生子,就叫做郭梓罷了。”二十年后,郭喬赴試京師,高中第三十三名進士,在會試錄上看到第三十四名進士名為郭梓,籍貫亦與青姐相同,立刻懷疑其是青姐之子。后在房師的幫助下,父子終于團聚。在這一故事中,離別時給孩子的定名是后來父子團聚的伏筆,也是將前后兩段故事情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鍵紐帶。若沒有這一細節上的準備,在敘述團聚環節時必然要另尋頭緒,很容易影響故事情節的連貫性。《郭挺之榜前認子》中的伏筆是較為明顯的,“后日之征”的說法很容易使讀者聯想到父子將來的相認。
在另一些故事中,離別場景中的伏筆較為隱蔽,只有當下文情節對其形成呼應時,其鋪墊作用才顯露出來。如上文提到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蔣興哥在離別時“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至此,讀者只能從這個細節中體會出蔣興哥對妻子的絕對信任,從而感到溫暖和贊嘆。但是,當王三巧兒將珍珠衫贈與奸夫陳大郎時,這一細節才表現出其真正的作用。正是由于蔣興哥的信任,才使王三巧兒有機會將傳家之寶贈與奸夫。王三巧兒的背叛使蔣興哥的信任成為笑柄,讀者在閱讀離別場景時產生的溫暖和贊嘆之情由此迅速落空。這一鋪墊的隱蔽性使其在之前、之后的情節中起到了截然相反又互相關聯的作用,不但成為貫穿故事發展的脈絡,而且通過前后對比有效地深化了故事的悲劇性。

對比是離別場景的第二種鋪墊方式,通常出現在婚戀類型的旅行故事中。空間上的距離往往會對婚姻和戀愛帶來不可預測的影響,導致奸情、負心一類情節的發生。在此類故事中,小說家竭力渲染某一方在離別時的賢德或深情。當奸情、負心發生時,其最初的表現在對比之下便具有了一種反諷意味。如《百家公案》第八回《判奸夫誤殺其婦》中,書生梅敬為棄儒經商征求妻子的意見,其妻回答說:






上文提到,倫理式離別是整篇故事之觀念系統的樞紐之處。不同的人物出于不同的社會身份經常在離別時就“居”與“游”展開一系列的論辯,離別場景因而成為各種思想觀念交鋒的舞臺。離別時的論辯揭示出人物“居”與“游”之選擇背后的復雜動機,預示著未來情節發展的走向,這就是所謂的論辯式鋪墊。與另外三種鋪墊方式相比,論辯式鋪墊不針對某一具體的故事環節,而是從宏觀上對情節發展、人物塑造、主題表達加以影響。因此,離別時的論辯常常是分析一篇旅行故事之觀念背景的切入點。
以《警寤鐘》第四卷《海烈婦米槨流芳》。論辯發生于陳有量被惡人騙往蘇州、與海氏離別之時。離別時二人的激烈爭論清楚地預示了高潮和尾聲的來臨:


在海氏方式激烈(“悲哭不勝”)卻措辭模糊的哀求面前,陳有量并沒有體現出應有的體貼和洞察,恰恰相反,他的回答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充滿了男性的剛愎與自負。“男兒”、“大丈夫”、“男子漢”是他的關鍵詞,代表了他的自我想象與期許。然而,這些詞語超出正常頻率的出現,恰恰又揭示出其內心的自卑和懦弱。作為一個落魄羈旅的無能書生,陳有量需要靠這些詞語來重建男性的自尊和自信。但是,男性氣概不僅意味著陽剛之氣,更意味著對責任的承擔,而他卻將男性氣概作為逃避責任的借口,沉迷于“懸弧四方”、“周流天下”一類空虛的詞藻。當妻子向他求助時,只以“操持自守”四字作答。妻子被迫代替丈夫履行守護自己貞操的使命。至此,我們在論辯中看到一個羞恥感過強的妻子,一個因自卑而自尊的丈夫。過剩的羞恥感使女性在面對強暴時勇于選擇死亡,卻怯于設法求生。源自自卑感的自尊心使丈夫逃避保護妻子的責任,將希望寄托于妻子的貞烈。這才是海氏殉難的真正根源。小說家通過離別時的論辯揭示出二人隱秘的內心世界,從觀念層面為故事的悲劇結局做好了鋪墊。
提到文學中的“離別”,人們通常想到的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詩·小雅·采薇》),或是“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實際上,相對于離別詩歌的典雅與含蓄,古代小說中的離別場景自有其獨特的感人之處。古代小說家根據題材的差異,對離別場景加以或詩化、或戲劇化、或寫實化的處理,在詩歌之外探索著離別書寫的新的可能。同時,離別場景通常出現在一個情節單元的開端,對整個情節單元的建構起著重要的鋪墊作用。從伏筆式鋪墊、對比式鋪墊,到關鍵物式鋪墊,體現出古代小說之情節藝術的精致化趨向。相比之下,論辯式鋪墊雖然文學效果較弱,但是卻提供了一種從思想史角度切入古代小說研究的視角,展示著底層思想世界與倫理世界的豐富景觀。本文是一種嘗試,也是一種思考:那些傳統上被認為專屬于某一文體的主題,在另一文體中是如何表現的?我們不需要給出一個孰優孰劣的評判,而是要在比較中探討每一種文體的獨特性與可能性,并對其書寫傳統加以總結和分析。
注:
①王貽梁、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2頁。
②《燕丹子》,《燕丹子·西京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4頁。
③馮夢龍《警世通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46-547頁。
④魯迅輯《古小說鉤沉》,《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頁。
⑤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頁。

⑦⑧⑨馮夢龍《喻世明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5、25、664-665頁。
⑩天然癡叟《石點頭》,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責任編輯:胡蓮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