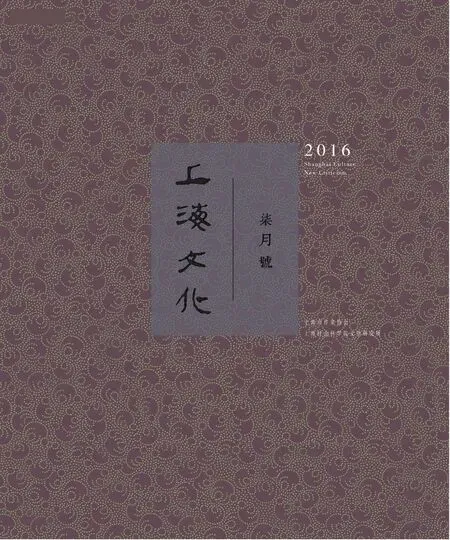凱恩斯談藝術
朱生堅
?
凱恩斯談藝術
朱生堅
1947年3月,劍橋大學《經濟季刊》刊登了執行總編輯奧斯汀·羅賓遜撰寫的《凱恩斯傳》,紀念一年之前去世的這位經濟學家。傳記開頭說到:“他具有超群的天賦,在眾多的學科領域里都具有高深的造詣,使內行人都引以為知音而對他十分推崇。他能夠在相等的知識和理解水平上,同哲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藏書家、現代油畫評論家、芭蕾舞評論家等談論問題。”可惜作者和傳主畢竟都是經濟學家,這篇傳記(中譯本不到六萬字,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主要講述凱恩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實踐活動和理論貢獻,幾乎完全忽略了他在藝術領域的活動和見解。
1982年,英國皇家經濟協會出版《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全集》第28卷,收錄凱恩斯在社會、政治、文學和藝術領域的著述,此書的中譯本《凱恩斯社會、政治和文學論集》由商務印書館于2014年出版,讓我們得以領略凱恩斯在多個領域的卓越才能,并且深信羅賓遜所言果然真實不虛。
凱恩斯對現代主義繪畫的眼光相當精準。1920年代初,畢加索、馬蒂斯的作品還能夠以相對較低的價格買到。凱恩斯認為,收藏他們的一流作品是天大的好事,“其原因在于,無論現在人們對其作品的價值評價如何不同,這批具有原創性的天才在歐洲繪畫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已給我們提供了充足理由,證明他們應在英國國家博物館中占據一席之地”。然而,正如通常出現的情形,官方的反應非常遲緩,這讓凱恩斯“不禁扼腕嘆息”。
如果說,看好畢加索、馬蒂斯這些現代繪畫大師,這還不算獨具只眼,那么,凱恩斯1936年在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次關于閱讀的談話節目,足以令人對他的文學修養刮目相看。他明確表示,不太看得上同時代的小說,但是也肯定“有一批作家具有天賦”,譬如埃德加·華萊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這些作家的作品具有一種偉大的純潔性,沒有任何虛假和捏造的東西。它們充滿活力,從容,淡定,就像奧林匹斯山的神靈,沒有以故弄玄虛的方式與現實生活接觸”。凱恩斯的文筆向來受人贊賞,由此亦可見一斑。這樣的評論本身就是極其出色的寫作,而他談論詩歌的口吻就像是文學評論權威:“當代詩歌沒有多少值得推薦的東西。但是,有一位詩人值得推薦,他就是英籍美國人T.S.艾略特。我相信,隨著讀者逐步適應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將會廣為人知……我可以確定,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之中最杰出的詩歌,是秉承了兼顧音樂和意義兩個方面的偉大傳統的詩歌。”如果必須要加一點限定的話,可以說,艾略特是那個時代用英語寫作的最杰出的詩人之一。而這并不足以動搖凱恩斯的判斷。
同樣,當他談到芭蕾舞,也完全是行家的口吻——這大概不會讓感到奇怪,如果考慮到他的妻子莉迪亞·洛波科娃就是一位著名芭蕾舞演員。而且,萊布雷希特說,那時候,芭蕾是知識分子關心的焦點,不懂舞蹈在社交圈和知識圈是不可接受的。順便說一句,凱恩斯從小到大都在劍橋大學圈子里生活、學習、任教,他也是劍橋知識分子高級俱樂部成員,該俱樂部后來演變為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其中包括一些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
作為經濟學家,凱恩斯談論藝術的時候,也會非常坦然地談到金錢。他經常為一些畫展目錄撰寫前言,其中就曾經從投資、收藏以及贊助藝術的角度,鼓勵觀眾“應該快速下手購買”;在經濟蕭條年代,繪畫作品價格下浮大約一半,他也會放低身段說,“我希望喜歡藝術的公眾現在將其購買力量加倍,以便回應我們的舉措。實際上,我懇求他們這樣做”(1931年)。凱恩斯在諸如此類的文字中表現出來的對待藝術和金錢的態度很耐人尋味。除了他的經濟學素養之外,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什么原因,使得他總是保持著一以貫之的冷靜、理性,即便是為展品做廣告,也能夠用一種近乎超然物外的態度來談論展品的價格。我們知道,很多藝術家終其一生都處理不好與金錢的關系,有人高調標榜自己不為金錢所累,實際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也有人故作通達,公然貪斂錢財,還要裝出一副名士的樣子。金錢讓他們扭曲變形,甚至于扭曲了藝術本身。要是他們能跟凱恩斯學一點對待金錢的態度和方法就好了。
當然,凱恩斯完全了解藝術是怎么回事。他非常清楚,藝術這門行當不應該以賺錢為目的,藝術創作的結果即作品本身就是藝術創作的目標,雖然“大多數進行創作的藝術家自然都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賣個好價錢”,因為“他們創作的時候不考慮金錢,面對生活卻需要金錢”。他明確強調,“繪畫不可能作為快速致富的職業來加以追求”。事實也正是如此:眾所周知,梵高的作品的價格現在都是天文數字,可是梵高本人一輩子窮困潦倒;即便是某些足夠幸運,在世時已經在市場上得到認可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的價格也完全不能跟他們去世之后的價格相比。總之,藝術是藝術,金錢是金錢,兩者終究是兩碼事。不過,一旦進入市場,凱恩斯就完全以高超的經濟頭腦來處理藝術作品。這對他來說是“原則問題”。有意思的是,1936年,凱恩斯接受某刊物約稿,與編輯通信商談稿酬,討價還價,其中的一封信里說:“我可以誠實地告訴您,我已經不再將撰稿作為獲得收入的方式,所以從財務角度上考慮一點也不在乎。但是,可以這么說,我身為作家工會的一員,按照一般的思維習慣,無法讓自己完全忽略原則問題。”
從凱恩斯關于藝術的著述來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英國似乎尚未形成一個較為成熟的藝術作品市場及其運行規則。1930年,凱恩斯為他參與創立的倫敦藝術家協會撰寫系列文章,回顧該協會成立五年來的情況,其中也提出了關于價格政策的構想:“應該考慮兩個原則:其一,在公眾愿意掏錢購買的前提下,我們希望盡量讓藝術家的作品賣一個好價錢;其二,預先定下一個價格總比沒有標價強一些。與此同時,顯然必須維持某種統一的價格標準;否則,買家就會感到困惑,產生懷疑,擔心自己購買的作品是否價格公道,得到的待遇是否與別人一致。”而他之所以積極支持視覺藝術的發展,是因為他把它與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聯系在一起。他在上述同一系列文章里,表達了自己的愿望:“當代藝術家創造的許多令人愉悅的美麗作品應該像其他任何藝術一樣,被人欣賞。要是公眾學會如何欣賞他們,那將是多么巨大的進步!”
除了撰寫文章、序言、評論,凱恩斯對英國藝術的巨大貢獻還在于,他一生之中為多個藝術團體、協會投入時間和金錢,以他的個人魅力和才能,直接參與管理和運作。如前面提到的,凱恩斯作為四個發起人(出資人)之一,成立倫敦藝術家協會。他還曾經擔任當代藝術協會的作品購買人,卡馬戈芭蕾舞協會的財務總監,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受托人,英國音樂與藝術促進會主席,皇家藝術劇院主席。他還參與了劍橋藝術劇院的創立、修繕和管理,參與劍橋大學和劍橋民眾的表演項目。事實上,凱恩斯在政治、經濟領域擔任的職務之數量和重要性都遠遠在這些職務之上,而所有這一切都絕不是單單憑借其家庭背景等外在條件所能達到的。
凱恩斯創立倫敦藝術家協會的緣由是當時一批藝術家缺乏有效的組織來宣傳、推廣,收入很不穩定,一些具有發展前途的畫家面臨生活困難。因此,該協會的宗旨是“使其成為一批藝術家的代理機構,通過給他們提供一筆得到保證的收入,并且為其承擔整個商務管理事務,從而讓他們享有更大自由,以免除他們所受的財務困擾”。協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財務管理制度,每年給會員提供保底補助,同時從銷售收入中提成、再分配,這套制度使得協會能夠正常運轉并有盈余——這對凱恩斯來說,簡直就是小菜一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協會成員的遴選制度。連同凱恩斯在內的四位出資人負責為協會進行商務管理,包括聘請工作人員、安排銷售,幫助會員簽署銷售合同,但是,決定接收新成員的事宜則主要由協會會員,而不是出資人來負責。這樣的分工當然是合理的,因為“毫無疑問,與畫商或者本協會的擔保人相比,協會中的藝術家能夠更好地評估新人的發展潛質,判斷新人的藝術成果”。再者,凱恩斯非常清楚,“這類協會性質特殊,不同成員之間應該存在表達共同同情心的基礎,但是要找到這樣的基礎并非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讓會員來決定接收新會員,可以有效保護、維持這一基礎。
當然,協會在遴選、接收新會員這件事情上還是非常審慎。因為這個協會成員眾多,從商業角度考慮規模已經足夠大了。盡管成員之間還能保持親密關系和espirit de corps(團隊精神),對任何這類合作機構而言,這樣的狀態都是可取的,但是,凱恩斯仍然警醒地認識到,把協會成員整合起來并且維持團結的難度非常巨大。他以經濟學家的本色,毫不含糊地說:“我們每接收一名會員,往往否決十名或者更多的申請人提出的要求。本協會不是慈善機構,無法完全不考慮畫作的商業價值。本協會并不致力于支持剛剛涉足藝術的新手,無論新手具有多大的潛質都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列。除非申請人顯示了足夠的品質,顯示其畫作遲早將會贏得市場,本協會是不急于進行選擇的。”
從該協會的新會員遴選制度,可以總結出一些基本原則,那就是:維護團隊精神,注重專業素質,不求過度擴張,注重商業價值。而這也差不多可以視為整個協會的基本原則,對于此類合作機構都不無借鑒意義。
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英美各國開始由政府大規模贊助公共藝術,以此作為經濟救助計劃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蘇聯在推動“戶外大型綜合藝術”實踐,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宣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而德國和意大利也在積極利用各種藝術形式、藝術手段進行社會動員和意識形態宣傳。由此,政府與藝術的關系問題引起關注。1936年,凱恩斯應邀撰寫了《藝術與政府》,探討這一問題。
凱恩斯首先指出,政府推動、發展公共藝術,其來有自。“古代的統治者們為了彰顯自己的榮耀,滿足自己的意愿,把相當大一部分國家財富用于舉行儀式,制作藝術品,修建規模宏大的建筑。這樣的政策、習慣和傳統并非僅僅限于古希臘和羅馬。”然而,在18、19世紀,出現了一種功利主義的經濟觀念和財政觀念,“它被視為整個社會唯一值得尊重的目的”。這種觀念認為,“人們追求的是面包,只有面包”。它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已經接受這樣的情形:“政府在非經濟目的上花費半個便士也是邪惡之舉,甚至教育和公共衛生也只能以假借經濟之名,悄悄混進來,理由是它們‘是有回報的’。”凱恩斯毫不留情地指出:“利用公共娛樂提供者具有的才華,讓其為經濟目的服務(按:這就是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從而進行剝削和伴隨而來的破壞,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犯下的最糟糕的罪行之一。”
事實上,在任何時代,公共藝術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義。“每一代人都會樹立永久性紀念碑,以便崇尚尊嚴,彰顯美麗,表達時代精神。比這類紀念碑更重要的是各種持續時間短暫的儀式、表演和娛樂活動,一般人工作之余可以借此獲得愉悅。這樣的活動具有獨特作用,讓一般人覺得,自己是社會一分子,與獨自生活相比,自己在這類活動中情趣更雅致,才能更凸顯,感覺更美好,心情更放松。”
“有時候,處在一個地方的所有人聚在一起,共同慶祝,表達共同的感受,甚至僅僅是共享簡單的愉悅之感……一般說來,提供適當機會,滿足這類幾乎堪稱人類的普遍需要,這在政府事務中應被置于很高的地位。在歷史上,如果哪種社會制度以不適當方式忽視這類活動,可能被證明給其自身帶來危險。”
多少有些令人驚異的是,凱恩斯已經知道,“大量民眾聚集起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這可能非常危險,超過了其他任何場合;然而,正是由于這種原因,這樣的情感應該受到正確的引導,并且加以滿足,而不是被人忽視”。他看到的實際情況是,從傳統中繼承下來并且加以維持的公共表演和公共儀式為數不多,有的人只是把這些東西當作古代遺跡進行學術研究,而且,人們從這些表演和儀式中所獲得的滿足感被認為是“野蠻的,或者至多的幼稚的”,不值得加以嚴肅對待。這使得當時的人們幾乎已經不知道應該如何著手,讓這些東西“在當代精神的環境中復活,讓它在這代人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令人滿意的作用”。那些曾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公共表演和公共儀式,一旦被破壞、被遺棄,也就很難再回到原先的有機狀態。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