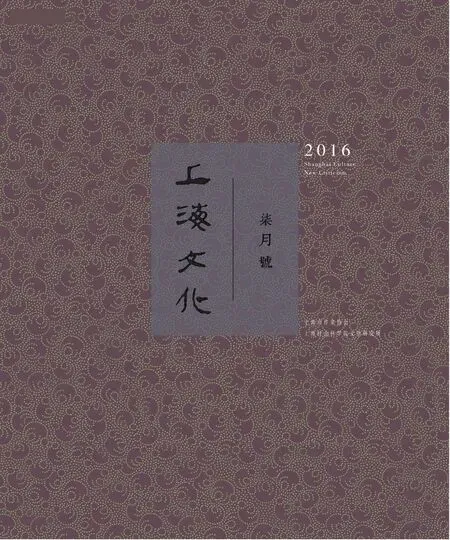良史傳統滋養創作,多副筆墨出入無禁
李潔非 項 靜
?
良史傳統滋養創作,多副筆墨出入無禁
李潔非 項 靜
項 靜:您是復旦大學78級的學生,由于家學和個人愛好,側重于古代文學、歷史的閱讀,畢業之后特別希望從事元明清的研究,這跟復旦大學是古代文學研究重鎮也有關系吧?當時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肯定也在時代激蕩之中發生了一些改變。在一篇訪談中您談到77級出了許多寫作者,比如陳思和、李輝、盧新華等,那個階段當代文學的氛圍比較濃厚,文學思潮萌動,文學新人涌現,各種爭論浮出地表。這種氛圍應該延及整個文學界,包括古代文學研究。您能談談當時的情形以及對您個人的影響嗎?
李潔非:很巧的是,我上學讀書的經過,跟當時歷史變遷幾乎完全咬合。中小學與“文革”共始終,1966年上小學,高中快畢業時“文革”結束,躲過了上山下鄉,很快,鄧公決定恢復高考,于是作為第一批應屆高中生參加1978年高考,幸運考到復旦大學。中小學沒學什么東西,倒是很自由,隨便玩。不過我因父親在大學教書,家中有些書,不甚多,但當時跟
別的家庭比,也算是得天獨厚了,所以養成了愛讀的喜好。上學雖學不到什么,但我自己的讀書尚不至于貧乏的地步,凡家里有的書,不分種類,一一讀之,亂讀,從古希臘羅馬傳說、《紅樓夢》、《水滸》、《三國》、王力《古代漢語》、《中國歷代文論選》、中華活頁文選到梅蘭芳文集、全套京劇傳統戲劇本,以及魯迅的書、《子夜》、《林海雪原》、《艷陽天》、劉白羽《紅瑪瑙集》、《馬克思與燕妮》之類。林彪事件后,文禁稍松,父親系里資料室有些書可以外借,我求父親或自己跑去以父親名義借一些書,記得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尚鉞《中國歷史綱要》、《倪煥之》、《西游記》、《少年維特之煩惱》、許地山和王統照文集等,還有“文革”時出的《大刀記》、《征途》、《朝霞叢刊》之類。最喜歡讀《西游記》,反復多遍,幾能通篇復誦,夏天晚上乘涼,逐日給小伙伴講《西游記》,歷歷道來,最小的細節亦不落下,一時如“明星”般為小伙伴追趨。至稍知人事,輒受《紅樓夢》吸引更多,亦讀多遍,之前讀《西游》,常常樂得床上打滾,讀《紅樓》卻暗自淚下,平生初嘗錐心滋味。又比較好地理,平時讀報,特注意國內外方域情形。總之,因愛讀和雜讀,高考時并不憷,入復旦后,同窗年齡懸殊,不少人拖家帶口,作為應屆生小弟弟,倒也不覺得矮了三分。不知怎么,我從小就有鄙薄當下的習氣,很習慣地為古代東西吸引,對現當代提不起興致,尤其是當代。加上當時當代文學學科初立,沒有多少成就成果,而復旦師資又是古典超強,更助長了我是古非今的心理。其實我就讀期間,當代文學風起云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等,火得不行,寫《傷痕》的盧新華又出在我們77級,所以關心當代文學的風氣非常盛,《當代》、《收獲》、《十月》等雜志極為搶手,另外像美學、心理學等新興領域,也都時髦。我卻跟這些不沾邊,不理會,還隱隱地排斥,目為“時學”,自己閱讀都在舊書上,特別是先秦和元明清這一頭一尾,還打定主意將來搞古典文學研究(高考報志愿所填之一是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可見那時的趣味)。結果分配不由人,分到新華社,搞古典就此無望(我不能忍受考試,肯定不考研究生),又趕上在新華社結識了幾個同年分配來的朋友,大家談論的多是當代文學和時代思想一類,不知不覺就轉到當代,開始寫文學評論。說起在校時系里環境,77級創作很活躍,盧新華聲名鵲起,張勝友以散文著稱,還有陳可雄因發表《杜鵑啼歸》、顏海平因發表《秦王李世民》也名噪一時,另如張銳、胡平當時在中篇小說等創作上都頗有斬獲,文學批評自然是陳思和為翹楚,那時就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他的文章,敬羨不已。78級也有搞創作的,愧77級頗多,李輝在校期間好像還不太顯,但他畢業到北京后進益驚人,多年來他所做的工作,從《搖蕩的秋千》《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直到眼下,我認為對當代文學史料學是奠基性的,切實清俊,能夠體現復旦學風。
項 靜:您寫過“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壇》、《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您本人其實也是當代知識分子中一個典型個案,尤其是放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這個學科之內來看,幾乎很少見到像您這樣不斷自我更新知識系統、轉移陣地的寫作者。您曾經是直接參與文學現場的批評家,直接回應當年的文學思潮、寫作現象,又是小說文體專家(《小說學引論》、《中國當代小說文體史論》),后來轉入城市文學研究(《城市像框》)、延安和當代文史研究(《解讀延安》、“典型三部曲”),還有當代生產方式比如文學制度的研究(《共和國文學生產方式》),又是一個明史系列的作家。您的研究方向的轉變或者說并存,都是一個典型的寫作現象,評論家、文學研究者、小說家、隨筆作家、史料專家集于一體。關于為什么轉型您肯定被問過很多次,還愿意再談談嗎?
李潔非:這個問題講起來頭緒比較多,梳理一下,可能要分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條件,一是個人原因。從環境講,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學科化,跟學術評價體系是分不開的,因為晉職和各種資格競爭,僧多粥少,為了可操作,二三十年來逐漸生出很多條條框框,我稱之為打格式,而學者因此就被導入格式化的套路,近十來年,日益奇葩。比如論文按發表出處分其高下、給予分值,核心期刊幾分、非核心幾分,抑或核心期刊計分、非核心不計分,又國際期刊得分高于國內……等等;對于論文、著述的規格、樣式乃至文體風格,也都給予硬性的排他性規定,什么提要啦、關鍵詞啦、注釋體例啦,都得照著格式來,好像不采取那些形式符號,就不配稱論文、專著;還統計學者拿過什么項目、是否主持人、作者排位順序、所獲獎項是何級別,都換算成分值計入,十分繁瑣。這股風從幾個著名大學搞起來,沒想到大家不覺得無聊乏味,反而紛起效尤,現在已完全成為統治性制度。這種導向作用是決定性的,學人不從不行,不從就不能晉身、拿到各種利益,所以現在知識分子普遍被關在這種學術囚籠里了,按格式做學問,從擇題、文風直到思想,循規蹈矩,捆得死死的。明清八股取士,現在學術體例實有其神,內容上代圣賢立言、形式上起承轉合,實質一模一樣。我因為不在大學環境,僥幸置身其外。社科院這地方諸多不如人,過去卻有一點好,就是學術上一些表面的條條框框很少。如果在大學,像我這樣的,早就混不下去了,像您提到的那些拙著,其中有不少算不算“學術成果”,大概很成問題。近幾年,社科院也越來越與大學那套同質化,條條框框基本都移植過來了,好在我距退休不遠了,無須焦慮。至于個人原因,有性情、興趣、經歷等。
項 靜: 您作為一個打破壁壘的“典型”研究者,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出現的學院派、媒體派等等不同寫作方式之間的壁壘分明。我發現研究者的身份已經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學科化,每個人都劃定了越來越較小的領域和風格。
李潔非:我從小性情,比較自由散漫,不耐拘束,受不了壓在模子里刻板做事情。做事須認真、須審慎,但與戴上籠套嚼口是兩碼事,那樣搞出來的東西一了無生趣,二面目可憎。試想,這種“成果”連自己都不能讀而悅之,又怎好意思邀別人盼睞?學術應不掩性情,泯滅性情的學術斫失靈氣,這顯而易見的道理,似乎已被現實壓榨一空。自古,中國的學術何曾這樣干癟過?八股文害人不假,但那只是敲門磚,博取功名而已,功名之外,古人真正做學問仍然具見性情。直到民國,無論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胡適作《白話文學史》、顧頡剛作《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梁啟超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郭沫若作《十批判書》、蔣廷黻作《中國近代史》、許地山作《扶箕迷信底研究》、孟森作《明清史講義》、錢穆作《國史大綱》、陳寅恪作《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包括馮承鈞獨特的翻譯式研究《馬可波羅行紀》、《多桑蒙古史》……等等,都揮灑性情、通脫不拘。以它們為準繩,我無法視學術為機械式操作,凡落筆,我都無意以取悅學術判官為目的,總想著在立足自己尺度的基礎上,博讀者好感,縱使多爭取一位讀者也好。至于興趣,這里非泛泛所指,是單講文趣。
我走在今天的路徑,歸根結底源于“文章”的那個“文”字,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言之不文,不若去言,既然提筆去寫,在我不拘寫什么,都不忍不從“文”上去追求和打磨,斷不可因為寫的是論文、專著,就有理由語言無味、催人入睡,那我寧肯去做點別的。我之抵觸所謂“學院味”,與此有很大關系。語言能力與感覺,因人而異,差別很大。坦白講,我們這一行筆墨好的人并不多,我做過幾年編輯,頗有感受。不少人的筆頭,只適合論文類,一旦寫點別的,“文”的不足就顯露無遺。這也是當代人文以及漢語質地蛻變的一個結果,文章之道,不復為讀書人所講求,似乎有思想有見地,即可以為文。這與古人大不相同。《過秦論》就是漢代的論文,而今,誰會像賈誼那樣寫論文,注重辭章與文氣?
今天的論文,可以全無文采,只要內容提要、關鍵詞、引文注釋合乎規范,配上幾條新理論和一堆術語,設法發表到列于名錄之中的核心期刊,就是第一等的成果。我們看現代(民國)時期,當時的學者,幾乎無人像今天的專家、教授,一輩子只搞一種東西,例如魯迅,小說、散文、隨筆、舊體詩,多副筆墨拈起放下、出入無禁、彼此滋養,他的雜文、小品,學問含量不遜學術文章,專著專論《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卻又如同小說一般引人入勝,而這是當時很普遍的情況。在這一點上,我比較頑固,既然明知孰優孰劣,我就沒有辦法不效仿好的,反而追隨不好的。我寫作方式的多次轉換,以及在不同文體之間跨越,原因之一就是難拒各種筆墨的誘惑,想都嘗嘗。1980年代起先寫散文,然后是文學批評,1990年代大量寫隨筆,同時以“荒水”筆名寫了五六十萬字的中短篇小說,世紀末又轉向專題研究,寫專著,之后則對非虛構史傳入迷。我獲魯迅文學獎,不是文學理論批評,居然是報告文學獎,連自己都覺得怪怪的。還有一個是“經歷”,我曾在新聞單位工作,后到學術期刊做編輯,再后來搞研究,經歷幾種身份,多少會有影響。前兩份工作,不甚合我意,但畢竟構成了一些人生體驗和視角,這些東西會不知不覺帶入你的眼光和方法。我覺得這方面李輝師兄或許更典型,他畢業后到《人民日報》當記者,但好像不很務“正業”,實際上還是在做研究,頑強追求學者使命,但他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法,跟“學院派”路數完全不同,調研色彩非常濃,不做書齋式的高頭講章,重材料、重現場、重敘述,這恐怕有新聞職業帶給他的影響,他也主動結合和利用工作上的因素,成就了自己的風格,假如他不到《人民日報》那樣的單位,而是留校當老師,也許未必能做出《搖蕩的秋千》、《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等成果。
項 靜:您從文學批評轉入專題研究,這個是一個寫作轉向,不同專題的寫作之間可能僅僅是研究對象的不同,但不同的寫作對象您居然是同時進行的,這一點挺讓人驚訝。 聽說《天崩地解:黃宗羲傳》和《文學史微觀察》這兩本書的寫作是穿插進行的,內容也出現交互,兩種寫作同時進行,您是如何分配時間和轉換思維的?
李潔非:其實,人本來不是單向性的,之所以普遍比較單向性,是被束縛的結果,而想要不被束縛,或束縛少一點,取決于看淡得失。把得失看淡,不禁抑自己,做想做或喜歡做的事情,就可以有多向的表現,這并不難。舉個例子,《北京日報》李靜,她是出色的文學批評家,文章有溫度,曾經得過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的年度文學評論家,但是近來她投入精力最多的是話劇創作,搞得風生水起,用話劇形式表達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我覺得她就是按照“想”和“喜歡”原則做事的人,話劇與文學批評只是方式不同,在她也可以說是換了一種方式的文學批評,也許是更有趣、更見效力的文學批評。但如果你的思維都在所謂學術評價框框里面,恐怕你不肯去做這樣的探索嘗試,因為“不務正業”,試想李靜如果身處高校或研究單位,話劇創作肯定不被納入“考核”范圍。凡能打破壁壘的,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務正業”。前面講李輝在《人民日報》幾十年,做的都是當代文學史和知識分子個案,只怕也無助于他在所謂業務范圍之內的競爭。我這十年來,一手做當代文學史,一手做明史。兩條線索,一條“務正業”,一條“不務正業”。所幸社科院比較包容,沒有拒不承認我的明史著述為成果。縱然不承認,我也仍然會做,因為“想”做、“喜歡”做。表面看這兩件事用上海話說“勿搭界”,其實在我心里是相關的。我曾講,明史可稱“古代史里的當代史”,當代則有“現代明史”的意味,有很強的深層聯系。不光是整個中國歷史走向上,當下與明代同處一個問題系當中,連思想特征也一直延續著相通的東西。讀一讀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和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兩本書,會悟出很多。《黃傳》和《微觀察》確實是穿插進行,同時截稿,出版相隔也僅一個月。這種穿插,彼此輝映,我出入三四百年一頭一尾,好像更完整地摸到了歷史的脈絡。旁觀者或覺得跳躍很大,在我反而思維是連續的、非割裂的。
項 靜:無論是明史研究還是當代文學史研究,對您來說都是在進行同一個主題即社會轉型,與社會轉型相關聯的是文化、文學的轉型。從共和國的文化轉型到1980年代,1990年代,還有互聯網時代,每一次都在文學表達方式上打下了印記。有人認為今天我們的純文學出現了保守主義的傾向,與當代重大的社會轉型失去了聯系,文學實際上是萎縮的,失去了曾經的活力。但是在龐雜、混沌、難以命名的網絡文學和新媒體中可能出現了革新的力量。您能簡略談談當代的文化轉型與明代的文化轉型共同的問題嗎?
李潔非:我在《解讀延安》里講過“文化重心下移”問題,這是從明代至今一以貫之的趨勢,它最根本的表現,就是文化權力、文化中心、文化等級的耗散和瓦解,先前主導性的價值逐漸衰弱,分散為無序的、多元的局面。明代文學里的誨淫誨盜內容,在中國過去很少見甚至沒有,明代卻全冒出來了,像《水滸》公然表現江湖社會、盜寇天地,唐宋漢魏何曾有過?《金瓶梅》肉欲橫流、聲色犬馬,更是駭人聽聞,過去從“關關雎鳩”到“春蠶到死絲方盡”,涉愛涉性,都用曲筆,意會而不言傳,明代卻是一覽無余。這些只從文學上講,是講不透的,實際上是社會解放帶來的文化秩序的崩解。以前由貴族、士大夫搭構的文化體系,被新興的社會力量拆毀了。這種拆毀,三四百年來一直在進行,尤其是到了目下,網絡這怪力亂神,接過印刷術的火炬,到處點火,燔朽焚舊,大鬧天下,終致文化主導權徹底易手。立足于這文化現實,掉頭回看文學,實在不宜說是文學自己發生了保守主義傾向,而是它不得不退避三舍、獨善其身,想要文學重返1990年代以前引領社會的局面,其可得乎?實際上也并不能說文學萎縮,單論文學自身,它不但沒有萎縮,相反實則比以前更加精進了,近幾年,中國作家莫言、劉慈欣、曹文軒屢斬世界性大獎,是有力的證據,即便不看這些大獎,平心以論,中國頂尖作家如賈平凹、劉震云、王安憶近年的創作,品質都不僅是當代以來最優,甚至逾乎現代之上。完全不能說文學失去了活力,問題是,原有概念的文學,被廣眾的自在、自娛性質的網絡文學海洋,變成了孤島,不再是文化的高岸和大陸。結合明代以來的文化趨勢看,這是無可逆轉的。我們看到并承認歷史的一種大勢所趨,但同時,從評價而言,無關好壞;不能說文學沒落了是因為它不好或變差,相反,沒落的往往可以是優質的東西,這也一再被歷史證明。“病樹前頭萬木春”,自然界規律如此,人類文化不盡然,人類文化可能優勝劣汰,也可能劣勝優汰,否則人類世界也不至于每每出現后人對前人文化心慕手追的情形。
項 靜:城市文學在90年代里是一個熱點,城市正成為最為重要的人文景觀。您是較早專門研究城市文學的學者。“這個新城市社會是當下中國社會的軸心,城市文化是當下文化的軸心。”二十年后,您對城市和城市文學的理解和判斷有沒有改變?
李潔非:沒有改變。《城市像框》可能是最早的一本從城市文學角度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著作。之前我就對一個奇特現象感到好奇,就是中國當代作家幾乎全都居住于城市空間,但他們敘述的故事和表現對象卻又幾乎全都是農村和農民生活。老輩作家如此,猶可理解,因為自幼生長鄉間,后來移諸城市,但是連知青一代作家,包括后起的先鋒作家,根在城市、生長于斯,卻也只作鄉村敘事,從不寫城市,這就太過奇怪。仔細一想,原因是中國的城市形同虛設,城市生活無論從內容到情感,不構成獨立的文學資源,使作家覺得有表現它的欲望。透過這個,我覺得抉到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和秘密,以及中國和西方在文化上的一個重大差異,1980年代困擾我的中國當代“現代派”文學或先鋒文學內容、形式兩張皮的問題,也迎刃而解。所以1990年代城市化進程展開,我即覺得對于文學將是一個質變性影響。彼時至今,二十年過去,文學果然完全被放置在城市背景和城市語境下,不一定是指所有作品都成為城市題材,而是城市視角成為文學的內在視角,當年《陳奐生上城》,城市是異物和隔膜的它在,如今文學敘事基本上都是從城市立場出發,包括現在作家的鄉村敘事都是以城市為幕布為起點,對鄉村作逆旅式返回,鄉村成了“鄉愁”、成了憑吊和挽回對象。對文學批評者來說,提前察覺一種動向而預言之,是可以滿足的。
項 靜:我看到一個訪談中您說對1980年代的文學有一個反思,“優點是進取、有闖勁,不過水平不高,技術幼稚,內容和題材單調,視野也窄,文學主要還處在復蘇過程,但風氣好”。“作家方面,留意較多是知青文學和尋根派,之后有莫言、劉索拉和先鋒派。”三十年以后,去年當代文壇又重新思考先鋒派,尋根文學,您覺得今天我們應該如何來重新看待先鋒派和尋根文學?
李潔非:去年有討論活動,我從報上得知,沒有仔細了解。1980年代文學一個要點,在于它是“文革”時代的回聲,這一點不知人們是否抓住。回聲的意思,除了“撥亂反正”,還涉及技術層面。從那樣一個將一切泯滅殆盡的時代走出來,文學在精神上之貧乏、藝術上之孱弱,非經歷其間者很難想象。可以說,1980年代文學一方面是“文革”時代義無反顧的唾棄者、批判者,一方面同時又是那個可憐時代各種桎梏、戕害的產兒。它的思維并不從容,認識力、判斷力、表達力也都處在比較低的水準。現在有些懷舊者,說1980年代是文學黃金時代,從文學在社會上所享榮耀,特別是文學風氣上,我能理解,但單論文學質地,我覺得這樣說是以情感代替現實。當時文學界對問題的思考,片面、輕率、表淺,甚至無知。這幾個字眼,我回看自己八十年代的文章,就常常難堪地面對。這沒有什么奇怪,經過“文革”那么徹底的反智歲月,精神如果立刻達到豐厚健全,反倒不合邏輯。“尋根文學”最大功績在于它將文化意識這面旗幟重新插在文學園地,但另一方面,“尋根文學”對文化的理解、表達本身,很多是想象的、臆造的、牽強的,它沒有能力真正碰觸文化問題本身,只是張揚了文化“意識”而已。至于先鋒文學,是1980年代文學最重要的反叛性力量,對于粉碎極左文藝枷鎖有著除根的作用,但作為一場文學運動的先鋒文學,有很多可笑亦復可悲,像極了民初社會生活中的“咸與維新”。加入到先鋒文學運動中的人,并非個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為何做,也并非個個想要這么做、適合這么做,只是一窩蜂、爭先恐后、猶如上山落草一般趕了去,以免落于人后。只有在中國,先鋒文學才成為主流的、非少數派的、席卷一切的勢力。為什么?因為當時中國作家內心并不真有自主性,中國的文壇也并不真正給個性留有空間,文學競爭的方式仍然主要不是個人的,是拉隊伍、扯旗、隨大流,這就造成“咸與先鋒”時,許多人心中實無先鋒精神,僅以先鋒姿態作為搏生存的“策略”。修辭立其誠,離開一個“誠”字,先鋒文學魚龍混雜就可想而知。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是“文革”時代的回聲或“文革”后遺癥,是逃出“文革”荒谷時的難以避免的階段。
項 靜:看到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以良史傳統滋養創作》,您說:“在許多國家,宗教是文藝創作的主要誘因和題材,但在中國居此位置的是歷史。”今天的創作中,歷史想象和重新敘述是一個重要資源,比如共和國歷史、民國、文革,1980年代等已經成為當代寫作的重要歷史資源。您對今天的文學中對當代歷史的呈現滿意嗎?比如對共和國歷史。
李潔非:怎么能夠滿意呢?雖然一直在長進,每過一段時間,都發現文學創作對當代史的描寫又深入了一點,像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王朔《動物兇猛》、賈平凹《古爐》,在表現“文革”深層肌理上,比之于80年代,高出太多。除了小說,也有不少非虛構文學作品,陸陸續續在開掘。但文學的當代史敘事,受限太多。其次,文學自身的歷史書寫素養,也妨礙此類創作出現頂尖佳構。古人由于特重史,所以常有文學一流而又深研史學的,現代時期猶然如此,但當代文、史兩途,對歷史研究下過功夫、有所訓練、認識端正的作家少見。基礎情形擺在那里,文學對歷史的表現若想達到情理兩通,非短期可致。這里,要好好溫習中國的“良史”概念。寫史而至于“良”的狀態,相當不易,除了才、學、德,還得用心平和、存意公正,去除各種私心雜念,絕不意氣用事,能夠瞻前顧后,又需要不單站在當下角度,還跳出于一時一地,從寬廣幅度看歷史中的人和事……總之,用大胸懷包容歷史。對文學創作的歷史書寫來說,獲得與歷史相匹配的復雜性,非得有“良史”精神的培煉不可。
項 靜:《天崩地解——黃宗羲傳》這本書,您把黃宗羲放在17世紀世界歷史的視野里,提出對近代歷史重新解讀的可能,中國文化有無自我更新的能力,可否自發孕育現代性,您選擇黃宗羲是因為這個歷史人物有可能告訴我們不同的答案。“一方面他的平生所歷很精彩,值得一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對我們重新確認中國精神資源頗具啟發”。 您能否把您由黃宗羲的思想所引發的“中國精神資源”略作闡述。
李潔非:“五四”以來,更早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光社會、政治完全被西方擊潰了,進而是文化自信心的摧毀。處處不如人,事事不如人,中國歷史文化被一古腦兒否定,以至于覺得它找不到一點善因。像今天稱為“普世價值”的觀念,反對者把它們斥作西方價值觀,擁護者卻也一樣,在擁護的同時,激烈咒罵、批判中國文化,仿佛非得把中國批倒批臭,才能去實現那些價值。這種自我撕裂太可怕,也是中國一二個世紀以來沒法平和理性地追求“好社會”建設的一大障礙。世界上凡公序良俗藹然的國家,沒有哪個是在自我詛咒中達致。中國真像左右兩種眼光看的那么不堪嗎?根本不是。全世界自紀元前后,直至15、16世紀,總體看下來,唯一祥和、理智的國度,就是中國。在此小二千年當中,中國的賢明之士、博洽智者,比任何國家都多。其他地方,文明墜地、思想黯昧、學術蕩然,到了驚人地步。你能想象中世紀歐洲曾經數百年間沒有幾個作者、文化近乎凋零一空嗎?你能想象印度一度沒有自己的歷史書寫、許多情形唯賴玄奘法師的記述方始可知嗎?當時馬可波羅東游回去后所講故事,確有奇貨可居、賣弄吹噓的成分,但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巨大差距是毋庸置疑的。了解這些真不是為了“老子也曾闊過”,而是平心靜氣去想其中的道理、由來,中國何以獨能如此?中國歷史有許多地方需要重新認識。像漢光武帝,他開展了世界上最早的“廢奴”運動,幾次頒詔責令豪門釋其奴婢,給其平民身份,成千上萬人得到自由,同時還從法律上廢止了對奴婢種種的非人、野蠻的規定,非常了不起。像宋仁宗,薄賦輕徭、讓利于民,寧肯“國”弱也不奪民之食。這種行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定是中國的賢哲、中國的文化種下深厚的善因,才在現實政治中結出這種果實。直到16世紀,中國社會和文明進步的腳步,一點不落人后,事實上,最早的近代化跡象即出在中國宋代時期,只是這一次中國比較不幸,草原蠻族入侵嚴重干擾了中國步伐。紀元四五世紀是歐洲倒楣,北方蠻族入侵吞沒了地中海沿岸希臘-羅馬燦爛文明,讓歐洲沉淪了一千年;蒙元滅宋,對中國性質相近(當然元代加大了東西方交流,也有好處,這不必說),雖然中國文明更頑強,蒙元統治也為時不太長,但終究使中國從古代社會向近代嬗變的腳步緩落下來,而且留下很多后遺癥,加重了后起漢族政權的專制程度(這一點,俄國亦然,俄國的亞洲意味,除了地理關系,還得之于蒙古統治的文化、心理殘留)。
項 靜:中國從古代社會向近代嬗變的腳步緩落,明朝是一個分水嶺,明朝經濟上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期,文化上也誕生了許多重要思想家,形成了后世文化上追溯晚明的重要傳統,但在政治上,明朝卻是一個落后于先前宋朝的時期。
李潔非:但宋代在經濟上、思想上、文化上開啟的向近代轉型的指向,明人心里并不糊涂,從皇帝到知識分子,都主動自認是宋的祧繼者。明在政治上比宋黑暗許多,文化卻是沿著宋的軌道前進的,宋明之學連為一體,知識分子的人格意識、主體意識繼續覺醒,思想或心靈的解放蔚然成風,思想探索和思想交鋒的空氣很濃,這都顯示了明代人文的活力。而在物質文明方面,中國二千年來雖有起伏但從未中斷的生產力發展,和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總量擺在那里,客觀上必然要求空間的突破和方式的轉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想壓抑都壓抑不住。因此,到中晚明,社會經濟與政治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凸顯,賦稅、金融、田畝、礦業、海禁問題百出,對專制政體的反抗已明確提出和表現出來。其表現獲證于兩個方面,一是民間和地方,東南經濟發達地區鄉紳勢力崛起明顯,以至于分權于官府,在諸多事務上實際影響力超過政府,而隱然有自治意味;二是朝堂之上,所謂“宮府相抗”,宮是皇帝、皇族及其親倖(宦官、特務之類),府是士大夫官僚階層,二者分別是專制政體的擁有者,和對它持異議者,各有利益要伸張,遂終訖于明亡,相持不下,而我們從后來主要來自東南經濟發達地區的眼光,可以透視這種權力之爭背后實際上是新舊社會力量的較量。黃宗羲正是東林的直接后裔,他的思想感情無疑緣著明代社會發展的核心沖突而來,他身處明亡清興之后,說出了過去父輩內心深處想說而未曾直言的話,那就是從“天下”的倫理正義而言,專制君主不合法,“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產,而是所有社會成員(“萬民”)所共享,以一己之私剝奪、殘害他人的制度必須滅亡。他這個意思是表達得很清楚的,你能說這不包含民主的自覺嗎?黃宗羲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自己追溯得很明白,二千年前孟子就為中國立了“君輕民貴”的思想。當然,二千年后,黃宗羲為現實所激發,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君”不單是“輕”,或許還未必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君”的存在,是那種以“一家一姓”凌駕于萬民萬姓之上的存在。《明夷待訪錄》對于平權(至少是分權)的訴求,對于國家政治從“專制意識”轉向“合作意識”的表述,是相當明確的。其實,他的看法在當時絕非個例,后來呂留良案,揭出曾靜說過這樣的話:皇帝不該由無賴來當,該由“儒者”來當。這話什么意思?翻譯成今天話語,不就是“專家政府”嗎?專家治國的觀念,一定排斥世襲制,一定排斥權力私有,所以背后顯然隱藏著通往近代政治(民主選舉、議會、權力分解及相互制約)的無限可能。這些都是中國思想者地道的原創,都發生在西風東漸以前,怎么可以說中國沒有自發走向近代化的可能?又怎么能說民主、平等、自由意識都是西方價值觀?中國想要變得更好,必須正本清源,將形形色色、或左或右,對中國歷史、傳統的妖魔化驅除掉。
項 靜:您對延安文學歷史的研究和明史研究都有一個特點,小敘事大歷史,越沉潛越復雜,文章也就越豐厚。我看您的作品過程中會不自覺聯想到黃仁宇、孔飛力、史景遷等外國歷史學家的寫作方式,既有宏闊的視野,又有問題意識,敘述方式有小說筆法,非常吸引人的一種歷史寫作。您心目中理想的歷史研究方式是什么樣的?
李潔非:歷史研究有兩類,一類基礎型,一類應用型。前者搜蒐史料、訂訛辨誤、精梳源流、考詳制度,這一類是基礎,非常重要,在中國有著深厚積累,足以傲世,像馬端臨《文獻通考》那樣的巨著,像宋代以來形成的方志,像清代學者做的大量史學辨偽,就是如此。但這類研究,接受面很窄,普通人不會接觸,難以對社會、國家的歷史認知發生作用。應用型的研究,就是史傳,這是從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以來開辟的偉大傳統,中國史學這一脈,理念獨特而先進,重敘述輕論說,西方歷史科學正好相反,重理論、重抽象、重主觀,我個人趣味完全在中國一邊,且目為更“先進”。以歷史之浩瀚曲晦,個人的論說、抽象實在難以避免一葉障目,所以抑制主觀是保全、接近歷史的明智之選。中國史傳傳統并非棄絕主觀,它只是比較懂得節制,借語言的處理將主觀融于敘事,不讓它跳到事實的前頭、上頭,去干擾讀者對歷史的自行解讀。當代以降,由于服膺于“主義”,義理先行,這個傳統慘遭丟失。我自己著述時,努力回到史遷,視他為表率。
項 靜:現在還能看到您寫的零星的評論文章,比如寫褚福金老師的,您現在比較關注的當代作家有誰呀?為什么?
李潔非:我疏離文學批評業已多年,對當下創作讀得甚少,所以也只能“零星”有一點這樣的文字。它們或者是機緣湊巧,或者是有什么引起我的感想,或者是我剛好能說上話的。像褚福金先生的《黑白》,以圍棋為題材,那是我耽迷的對象,于是有興趣略表觀感。但這樣的寫作,現在于我越來越“業余”了,難得您還能注意到,非常感謝。
項 靜:每一次轉換無論是主題還是寫作方式,背后肯定都有非常具體的原因,但從外人來看,是比較順暢的,從一個主題到另一個,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對您來講,寫作過程中遭遇過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李潔非:最大困難是學識不足,因為我的寫作跨界明顯,而每個問題都涉及一大堆事實、材料、說法和前人成果,這還不光是作為當代文學研究者去搞舊史國學,即便在當代文學史范圍之內,像延安文學這一塊,我也不是素有積累,所以學識之欠隨時隨地能夠感受到,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埋頭讀書。我從文學批評抽身以來十多年,很少出門,一般活動和應酬敬謝不敏,主要就是時間少余閑,要讀的東西太多。
項 靜:我們這個行當的人無非就是讀書寫字,李老師現在在讀什么書?您方便介紹一下現在正在寫作的專題嗎?還會不會開啟新的領域?
李潔非:誠如您所預見,我又跳到了一個新的領域,眼下正在做太平天國的研究。本來明史書系后,我想沿著明上溯到宋,往前再探一探中國近世史的頭緒,為此讀了不少書,宋史、宋儒,包括蒙古、遼、金、西夏以及西人關于中亞草原文明的著述,又因儒學問題而延及秦漢、因夷夏沖突而延于漢末、魏晉南北朝。不料,其間偶然拿起梁啟超寫的一本李鴻章傳,里面講到太平天國中間發生的事,一下子抓住了我,欲罷不能,找來所有能見到的太平天國資料,逐日去讀。讀著讀著我才發現,雖然太平天國這一段,中學、大學課堂上早就學過,卻是相當扁平化的。太平天國出了許多有意思的事,且在有趣的同時極重要。它是中國農民起義史的終點,但已逾越了農民起義的一貫特征,跟黃巢、李自成明顯不是一路,結合了近代的各種因素,確有理想、革命的維度。它的意識形態特別值得研究,從中可以找到中國近代以來許多問題的根須和死結。太平天國的史料工作開展得相當好,從民國至當代,許多學者付出了大量辛勞,只是一般不為人所知。但是解讀做得不夠好,諸多分析在我看來不在節骨眼兒上,外國作者是由于對中國歷史上下文缺少整體了解,中國學者則囿于時代觀念太深。我目前打算做做這件事,把宋代那段先放一放。
項 靜:我們看一個文人的時間基本上可以從他發表的作品從勾勒出來,您多年來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創作力,您平時的寫作時間是怎樣安排的?
李潔非:幾乎談不上“安排”,除開日常生活行為,每天都是讀寫穿插,寫乏了,就看書,通過看書又找到新的發現與興趣,引出下一個寫作行為,就這么周而復始。以前熬夜,這幾年身體出問題后不熬了,改成早起先寫作約三小時,然后看書,下午或者續寫一點,或者不再寫。大致如此。因為不坐班,也極少外出應酬,時間倒還有保證。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