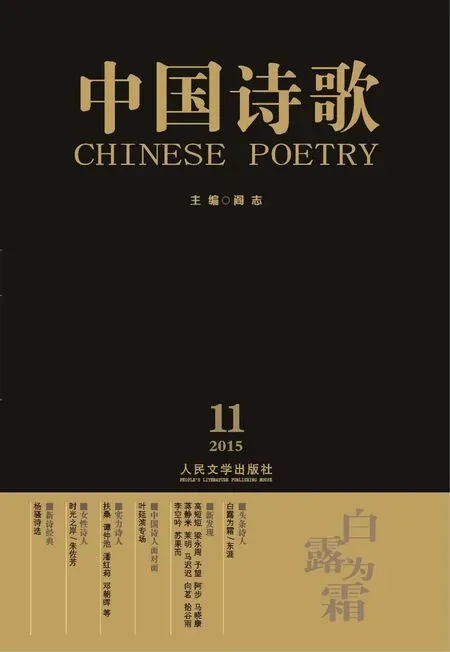轉變、介入與自我認同
——論1930年代楊騷的詩歌創作
□張立群
轉變、介入與自我認同——論1930年代楊騷的詩歌創作
□張立群
相比較而言,詩人楊騷雖然不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詩壇最為響亮的名字,但無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位。自1927年秋末從日本歸國,在上海開始寫作生涯,之后,又受到魯迅的扶植,出版《受難者的短曲》等多部詩集,楊騷便登上文學史意義上的1930年代文壇。隨著1930年加入左聯,1932年在上海成立中國詩歌會等一系列活動的展開,楊騷已經與“1930年代文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由于種種歷史原因,楊騷頗為豐富的文學創作活動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并未引起文學史研究者的關注。但是歷史又是公平的,楊騷的創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重新獲得了研究者的重視。隨著一大批關于楊騷創作道路、生平傳記、研究論文的出版,楊騷研究已成為文學史研究視域不斷拓寬趨勢中的重要現象,而本文在結合大量資料的前提下,以“轉變”為主線對楊騷1930年代的詩歌創作進行研討,只是期待豐富其中的一個側面。
“歷史”的轉變
楊騷1921年嘗試習作新詩歌,從二十年代詩歌創作的情況來看,楊騷的作品多“追夢”、“行者”、“旅人”一類抒情主人公,這充分反映了他在這一階段受西洋文學影響的創作傾向。但在另一方面,楊騷的創作又從不乏反抗意識,《把夢拂開》、《夜的上海》、《黎明之前》等作品,遍布著詩人對新生的期待。事實上,楊騷在《我與文學》一文中提及的“文學是武器。所不同者,是誰用這武器,怎樣用法,為誰用,用于誰罷了”,已預示了其日后創作發生轉變的原因。
1930年代的詩壇,由于社會形勢的變化,詩歌的現實性追求逐漸成為當時創作的重要趨向。歸國后的楊騷目睹中國社會的現實,在創作上自然產生相應的變化。早在歸國的途中,楊騷便以“日記”的方式寫道:“我還是向文藝戰線這方向走罷。既不會太過白白地送死,又較近自己的性質。”懷著對祖國和自己未來的憧憬,楊騷離開“熱國”新加坡,并開始在上海過著寫作生活。1928年,楊騷與魯迅相識,得到魯迅的教誨、培養與資助。正如李丹、趙鵬所指出的:“魯迅對楊騷創作上的影響還表現在日常交往中對他實實在在的幫助和支持上。楊騷在和魯迅結識后不久便成為魯迅所主編的《語絲》和《奔流》雜志的主要撰稿人,并在上面發表了大量的詩歌、劇本、譯作。正是在魯迅的提攜下楊騷迅速地步入了上海文壇,并日漸為人們矚目。不僅如此,魯迅在具體創作上對楊騷的幫助也使他獲益匪淺”。應當說,楊騷在人生旅途的關鍵時刻認識了魯迅,在魯迅的關懷和影響下,迅速走出了思想上的低谷,而與其思想轉變相一致的是其在創作上逐步由感傷主義、悲觀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此后,他致力于揭露黑暗現實,反映革命斗爭,歌頌光明的未來,一種“歷史的轉變”正在他身上“誕生”。
如果說他1928年12月14日“舊稿改作”的《粉蝶與紅薔》還更多流露過去的創作風格,那么,從寫于兩年后的《臨終》一詩結尾中,我們則看到:“我昨夜偷了你那秘藏的不屈的光銳的刀劍,/今天借了你那決絕的圣潔的剛強的心肝,/把我吸著失望的空氣的口鼻割掉,/把我流著灰黑的毒血的血管切斷。”“現在,我的血將流盡,我將死去,/悔恨凝成的這個暗淡的天地,/將散開換來一個光輝綺麗的。”“現在,我將死去,我沒有話安慰你;/愿地下的黑泥埋沒我的死尸,從此絕滅,/愿天上的陽光的輝煌照臨你,新生一切!”“啊,現在,現在,現在我將死去,/如有來生,我愿生做一株堅固的大樹,/做成你和大家的手中執著的血染的旗!”
毫無疑問,這是屬于一個悲傷主義者的死亡,但在字里行間,又有悲傷之余的反抗。上述的“結合”使《臨終》在表達死亡狀態的同時,又呈現出較為明確的新生渴望。這種狀態應當是屬于1930年代詩歌的寫作狀態,而事實上,歷史的車輪也已經駛入了這個年代。
文學的“武器”
楊騷1930年的主要社會實踐活動是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并與穆木天、森堡(任鈞)、蒲風、白曙、杜淡等組成“左聯”詩歌組,成為詩歌組負責人之一。在“詩人如果是預言者,藝術家如果是人類的導師,他們不能不站在歷史的前線,為人類社會的進化,清除愚昧頑固的保守勢力,負起解放斗爭的使命”的旗幟指引下,楊騷積極參加貼標語、發傳單、演講、示威等活動,翻譯蘇聯作家雅科列夫的《十月》。他在是年5 月2日的一封信中曾寫道:“我要在群眾之中找點熱氣,取點暖味。”1931年,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左聯五位年輕作家之后,楊騷仍堅持在左聯活動。是年,在杭州治病和翻譯期間,楊騷又在信中寫道:“時代已經不是浪漫好玩的時代,人心當然要受著影響,我相信這不是我的衰老,而是我更進一步地知解人生和創造人生的開始。”1932年1月,楊騷作為發起人之一參加中國著作者協會。“一二八”事變發生時,楊騷參加上海各界慰問團,親自到寶山路一帶慰問十九路軍。即使在返回故鄉漳州,窮困逼迫的時候,楊騷仍自白地說:“一無膽量做土匪搶錢,二無婢顏奴膝的本能做官,三無狡猾的本能做商人,當然是要窮的,再無祖宗遺下什么大財產。最后留給我們的一條路,便是實際革命去。”這種認識再加上1932年9月在上海他與穆木天、任鈞、蒲風等發起成立中國詩歌會的過程,足以表明楊騷已逐步轉變為一位詩歌戰士。
在1932年11月發表于《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上的《小兄弟的歌》中,楊騷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寫出革命推翻舊社會時的巨大力量。詩人借助小兄弟之口,滿懷激情地寫道:“我今晚怎樣也睡不著/我想見明早的天陷地落。/我喜歡那毀壞這個天地的狂暴,/因為這個天地是慘酷的,我憎惡。/來罷,哥哥,這碗紅茶給你喝,/準備我們明天在暴風雨中唱歌。”顯然,作為左聯詩歌陣營的一員,此時的楊騷已經認識到:惟有投身于革命實際工作,惟有通過詩歌反映現實,其詩作才會在讀者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同年發表的《關于文藝創作不振的感想》一文中,楊騷指出——
新興文藝的作用,要把新興階級的思想、意志、感情傳達給大眾;換句話說,是新興階級為著要完成它本身的歷史底任務的一種攻擊敵人的武器。
那么,當然的,這種武器,須得新興階級的人來運用它最為適當。須得新興階級的人自己出來,用自己的話,來表現他們自己的感情、欲求、理想,才能夠建設真正的新興文藝,和正確地完成新興文藝的任務。
…………
因此,對于中國新興文藝負著過渡期的領導任務的前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藝理論家,尤其是創作家,為著要救新興文藝的不振,使它走上正常的軌道而發展下去,首先必須克服他們的所屬的階級特有的個性(感情意識)。
楊騷的這段話,與其說是寫給特定時代的詩歌與詩人的,還不如說是結合自己的“蛻變認識”而進行的創作經驗總結更為確切。在革命的年代,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都是“武器”,但“武器”的內容和“使用者”的身份,無疑同樣是需要甄別和過濾的。詩人一般出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成為楊騷筆下的“新興階級”,必須將自己的個性、感情、思想、意識轉變并且具體指向人民大眾,這就必然決定了詩歌的大眾性。因此,如何克服詩歌創作主體自身的情感意識,儼然成為這一轉變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楊騷認同“一位優秀的作家,最少須具有第一,他們所生存的時代的代表底時代精神;第二,進步的世界觀;第三,敏感性;第四,描寫的能力”。他對作家“敏感性”的要求,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賦予了革命時代詩人的全部意義。
從楊騷1930年代著名詩作《福建三唱》第一部分可知,“朋友,你問嗎,我的故鄉?”與“哦,我愛我的故鄉!”的反復出現,是為了將視角首先“局限”在一個基調之上。通過故鄉福建與東北(吉林、奉天、熱河、黑龍江等地)的比較,“我的愛”首先來自“此刻”美麗、寧靜的故鄉。但在另一個世界,在歷史形勢的陡然嚴峻之下,“哦,你泉漳的子弟,/你福建的鹽,你,/你向哪兒逃避?!”這里,詩人的責任感、現實精神已經通過自己的詩意經營獲得了升華,因而,在最后他以反問的方式唱道:“哦,你泉漳的子弟,/你福建的鹽,你,/鼓起廈門灣中的怒潮罷,/淹沒遠東的帝國主義!”
看來,文學的“武器”不僅在于題材的選擇,也在于某種風格的呈現,而此時,楊騷的詩歌又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展示與時代的契合關系。
“我們”的介入
有關現代詩歌人稱的使用,一直存在著某種歷史認同的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是一種言說。言說使詩歌主體身份認同得到了提高,隨之而來的又包括如何言說與言說對象等系列問題。現代詩產生于“五四”文學革命時期,“我”在這一階段的應運而生在很大程度上與“五四”啟蒙意識、個性張揚密切相關。在充分顯示“五四”時代詩歌創作實績的郭沫若《女神》中,其名篇《天狗》、《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每一句都是以第一人稱“我”字開頭;“我”的不斷出現與重復,不但強化了“我”的主觀情懷,而且也在昂揚激越的吞沒一切、崇拜一切的情感宣泄中,實現了“我”才是“我”的人格價值。這種“自我”在詩歌中的極度膨脹甚至狂妄恣意,正是“五四”個性精神最狂熱、最浪漫的彰顯與噴發。然而,在外來文化刺激和本土文化現實發展的共同訴求下,“五四”時期的個性思想啟蒙只是以相互對峙的方式完成了現代意義的文化轉型。在破除傳統“群體意識”的盲目依賴和喚醒人格獨立之后,現代社會意義上的“個體意識”與傳統文化意義上的“群體意識”,正以新的形式走進了二十世紀的歷史。殷夫在1929年完成的六首《我們的詩》及其《我們》中,以“我們”的語詞方式替代以往抒情詩中“我”的抒情主語,并不斷進行激情洋溢式的群體性呼召,都說明了這一時期詩歌的抒情主人公與詩人的主體意識已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無產階級的戰斗集體。
通過歷史的回顧,我們不難想象:1930年代詩歌中的創作主體在革命斗爭形勢日趨嚴峻、不斷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在楊騷的《小兄弟的歌》的結尾“但還有我,有無數和你們一樣的,/勇敢耐勞的活著的兄弟!”的詩句,其實已經體現了所謂“融入集體”的傾向。而在一首名為《第三人稱的悲劇》的詩中,楊騷更是寫出了“他”這個獨行者所遭遇的人生困惑:“他躍起,踢開睡慣的被窩,/但望那通紅的火光,他遲疑。/看那海嘯般的大眾,戰栗,/捏住自己的心,不敢用力,/啊,他終于不行,終于!”可以確認的是:楊騷的這首詩其實突出了“自我”在社會斗爭和大眾群體面前孤立無援的精神狀態。這一“反向書寫”在某種程度上預示楊騷詩作中可能呈現的正面刻繪。
抗戰全面爆發后,楊騷在《保衛大上海》、《搖籃曲》、《我們》、《這是一首活的諷刺詩》、《二月四日》等作品中體現了以抒情主人公“我們”替代“我”的現象。《我們》一詩以直白的方式充分體現了抗戰時代詩歌的主題風格:“我們有熱的血,/鐵的心!/我們有粗的臂膀,/大的拳頭!/我們要替受難的同胞復仇!/我們要替兒孫找出一條路!/我們有決心——/要抗戰到底!/我們肯犧牲——/為光明自由!/我們筑起堅固的堡壘/不能失掉一寸土地!/我們愿流盡最后的血/不讓強盜有所進展!/我們不怕死!怕死的是狗!/我們不妥協!妥協的是賊!/我們用熱的血——/消滅侵略者的狂焰!/我們用大的拳頭——/粉碎侵略者的幻夢!”然而,我們更關注的是其人稱的使用:“我們”的頻繁出現,生動地體現了當時斗爭形勢的變化,以及同仇敵愾的團結氣勢。相對于1920年代那位孤獨的行吟詩人,楊騷1930年代詩歌抒情主人公由“我”向“我們”的遷移,與1930年代詩歌大眾化趨勢緊密相關。作為中國詩歌會的重要詩人,楊騷的作品與《新詩歌》旬刊創刊號《發刊詩》中的“呼吁”“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大眾歌調,/我們自己也成為大眾中的一個”具有實踐證明的關系。然而,如果一旦著眼于中國詩歌會提倡的“大眾化”問題,楊騷的詩歌又獲得了新的闡釋內容。
形式的嬗變
楊騷在《略談詩歌音韻與大眾化問題》一文中,結合“新詩歌并不是沒有韻律調子的。新詩歌自有新詩歌的韻律調子,那是配合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的要求,跟著刻刻在變化的客觀現實走,因詩人的修養生活之不同而有異,取著極自由的形態的”的現實背景,展望未來:“新詩歌的前途是無限的!新詩歌將來一定能夠大眾化!新詩歌在目前所以未能深入大眾的原因,并不是單純的音韻問題,而是更根本的大眾教育的問題。不錯,新詩歌本身的缺點是有的,有若干詩歌工作人員在拆爛污是真的,這都是新詩歌大眾化的阻力。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應該怎樣團結熱心真摯的詩人,更加努力,來克服新詩歌本身的缺點及客觀底阻礙,而不是懷戀過去的尸骸!”楊騷的看法生動地體現了詩歌大眾化主潮對其創作的影響及其他所特有的詩人身份。中國詩歌會雖在1935年被迫停止活動,“左聯”也在1936年初為了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而自行解散,但作為一種形勢的適應,楊騷等詩人并未放棄“詩歌大眾化”的實踐,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詩歌會”時期確立的理論主張在這里得到了延伸與強化。
歷史地看,中國詩歌會同人的詩歌創作整體上具有“捉住現實”,努力“歌唱新世紀的意識”,“用俗言俚語”使詩歌成為“大眾歌調”,“重視以敘事詩來反映農村動亂的現實”,“詩風剛健、樸實、明快”的風格、氣質。這種傾向對于楊騷而言,其題材、風格已在上面的論述中得到證明。然而,對于具體的詩歌形式呢?或許,我們重新審視當時由同人撰寫的《關于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一文,可以更為明確、具體地了解當時對“形式”方面應有的共識:“關于新詩歌的形式,我們有如下的意見:(一)創造新格式;(二)采用大眾化的形式;(三)采用歌謠的形式;(四)要創造新的形式,如大眾合唱詩等。”
由以上內容看待楊騷1930年代的詩歌創作,在《小歌金陵》中便具有極為明顯的歌謠體傾向:“明孝陵,/中山陵,/一樣的偉大,/一樣的驚人,/一樣的成功,/一樣的革命!”“古百姓,/今百姓,/一樣的渺小,/一樣的可憐,/一樣的挖肉,/一樣的抽筋!”除了簡單、通俗的詞句之外,上下兩節的對比手法,和長短句結合、形式相同,都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也足以成為其符合時代風格的重要特征。由此聯想到1920年代楊騷的傷感、內斂的詩風,其形式的嬗變無疑是讓人感到“驚訝”的!
這樣的傾向還在《雞不啼》、《福建三唱》、《搖籃曲》、《莫說筆桿不如槍桿》等作品中有所體現。當然,對于1930年代楊騷創作整體實績而言,長篇敘事詩《鄉曲》無疑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峰。鑒于1930年代一部分唯美派詩人,因追求形式完美而走上雕琢之路,“中國詩歌會詩人的詩,不僅從內容到形式與他們有根本的不同,就連詩體也相反了。唯美派詩人多寫短小的抒情詩,中國詩歌會的詩人們,則重視長篇敘事詩。因此,從抒情到敘事,從短到長,是新詩領域的開拓”,所以楊騷在1936年6月《文學界》創刊號上發表長詩《鄉曲》絕非偶然。《鄉曲》長達五百余行,共分五個主要部分,在內容上真實地再現了1930年代農民的悲慘生活和農村的破敗景象,從而揭示了舊中國農村的黑暗現實以及農民逐步覺醒的必然歷程。在藝術上,長詩主要以兩行一節的詩形為主,并輔之以書信體。除此之外,為了表現農民斗爭雄偉壯闊的生活內容,詩人常常運用現實主義手法直接描摹,從而使時代活生生的畫面呈現于讀者面前。
上述創作傾向的出現,對于1930年代的楊騷而言,既表明其完成了歷史的轉變,同時,也表明其作為愛國詩人、大眾詩人的革命立場。楊騷1937年2月9日在日記中寫道:“前進的作家,是革命的一種特殊群眾,他們的力量在乎借文字影響一般群眾;因此,他們要始終忠于革命的信仰,不能因革命政策的改變而稍有和向來的信仰違背的表現。”這大致可以印證其創作實踐的本質及力量之源。
藝術的綜合
一般來說,1930年代左翼詩歌及其“詩歌大眾化”容易給人帶來如下的印象:由于追求詩歌的功用意識和受眾程度,所以詩質是透明的甚至口號式的,自然其藝術成就也就不高。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反復閱讀楊騷的文論時,才會發現其可貴之處。按照潘頌德的劃分方法,1930年代屬于楊騷建國前詩歌創作的第三階段,而此前日本留學(1921-1927年)與歸國至1930年春加入“左聯”(1927-1930年)分屬第一、二個階段。從這個階段劃分不難看出:楊騷是在“五四”新詩運動影響下走上詩歌道路的。1921年,楊騷在日本留學時開始嘗試新詩創作,并寄回國內發表,這一異域氛圍內的創作使其很容易產生中西合璧式的詩歌傾向。而事實上,無論從現代文學上很多作家接受西方現代派是通過“取道日本”的經歷,還是弱國子民地位極易和某種現代派風格發生契合,這兩方面都決定了楊騷早年的詩風。而一旦最初的詩歌風格形成并得到發表的確認,其內在的延續性也必然在日后的創作中呈現無意識的傾向流露。
從發表于1936年的《感情的泛濫——〈在故鄉〉讀后感及其他》一文中“若是想到什么就寫什么,感到什么就唱什么,表現的手段又毫不加以選擇,結果便難免顯出形態雜湊,感情泛濫的毛病,而不能抒寫出來那應該讓讀者感到的鮮明的特征和形象,易流于一般化,概念化了。一般化概念化,這不但是詩歌的大敵,也是詩歌以外的其他的文學樣式的死對頭,已經成為我們的常識”的論述可知:楊騷在詩歌大眾化的年代,一直保持著較為清醒的詩歌認識,因此“詩是比較直接地反映生活感情的一種形式內容最被壓縮的文學樣式”就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詩歌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應有的品格,這一品格可以隨著時代主題的變化凸顯審美意識形態的功用意識,但這并不是以降低審美意識為代價的。楊騷1930年代的詩歌創作在總體上呈現的時而歌謠化、時而藝術上的多樣性,以及難以排遣的自我意識,正是其詩歌創作道路影響其理論主張從而再次投射于創作的必然結果。
很多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楊騷的文學觀、文藝思想、文學思想等內容及其詩歌表現時代生活的獨特性問題。楊騷在寫于1936年5月的《從詩的特殊性談起》中指出:“因為詩的特殊性,根本就要因時代的不同而起變化。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社會底要求(必要)。這個社會底要求(必要)正是決定詩的特殊機能的因素,而詩的特殊樣式便是決定于詩的特殊機能的。”但如何為“時代的要求”表現目前詩歌的特殊性呢?楊騷指出:“詩人不但被要求破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殘殼去創造新的完美的容器,而且被要求采取新的酒來裝滿它(容器)。換一句話說,(一)把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和反應,在情緒的本質底波浪中表現出來的,(二)比小說及其他的文學樣式適合于朗讀或可能譜成歌的,(三)在諸文學樣式中是內容和形式最被壓縮的,(四)用新的完美的容器來裝新的酒——客觀現實及詩人生活感情的精華——的,這便是當為‘時代的要求’的目前的詩的特殊性了”。楊騷強調詩的表現情緒以及詩人對現實的認識及反應,并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指出:“一、因為詩在表現情緒上比小說直接很多,也可以說詩人對于現實的認識及反應,在情緒的本質底波動中表現出的,便是詩,所以詩比小說更忌說理說教或大談其政治常識與主張”;“二、不要把事實的細部描寫得太煩”;“三、要強調音樂性”。
結合其時代語境可以將其作為一種“藝術的綜合”,這種“藝術的綜合”在其他文章中可以表現為“反對口號標語的詩并不是反對口號標語。各時代要求各種的口號標語,詩人應該跟著時代所要求的口號標語前進”,“但一個時代的口號標語能夠有幾個,你若直直地把它們喊出來,問你能夠寫出幾首詩?”這恰恰可以凸顯楊騷詩歌認識及其實踐的意義和價值。
綜合以上五方面所述,我們大致可以了解楊騷1930年代詩歌創作的意義和價值。楊騷1921年、1941年兩次離開祖國,離開時代歷史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注其創作的重要原因。然而,歷史并未遺忘這位卓有成就與見識的詩人:“除非你不談起三十年代革命文藝運動,不然的話正如你不能不想到許許多多曾經為它的發生和發展貢獻過自己一份力量的尚存或已故的作者們一樣,你也不能不記起他,談到他”,“這自然是由于詩人生前曾經對我國現代文學領域有所建樹,其作品在人民群眾中起過較大的影響,因而對革命事業有過一定貢獻之故”。身兼楊騷的詩友與同事身份的詩人任鈞,在不同時期回憶楊騷及其創作實績時所做的評價,正是我們重新審視楊騷創作的重要原因與邏輯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