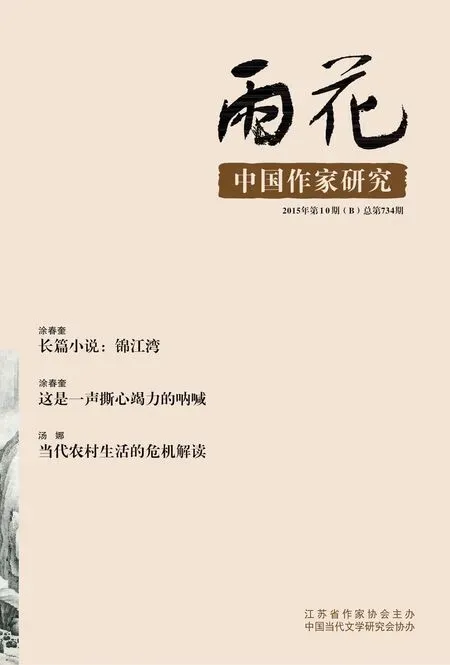這是一聲撕心竭力的吶喊
——《錦江灣》創作談
■涂春奎
這是一聲撕心竭力的吶喊
——《錦江灣》創作談
■涂春奎
我一直想寫一部小說。
這些年里,我一直奔波在一條艱辛的路上,一頭是故鄉,一頭是異鄉,淚水是我彷徨的腳步。
已是,掙扎多年后,我決定寫了。我怕自己會在遺憾中死去,真的。
當我在夜深人靜,在有些灰暗的燈光下敲打鍵盤的時候,我就會讓自己的靈魂變得謹小慎微。我的文字告訴我,這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情。
我寫的時候,我的親人們會突然站到我身后說,切,就你,一個小學生,還寫小說。
但我真的在寫。我就是這樣一個在別人看來是多么古怪,可笑,迂腐的一個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但我習慣了。
我就是這樣一個走在一條艱辛,一條奇怪的路上的人!
貧窮迫使我低下了文學少年那顆清高的頭顱,像一滴卑微的雨點一樣融入了浩瀚的生活洪流,從此心無旁騖,呼吸緊迫,文字的那縷清香被我撂得足有十萬八千里之遙,不敢回望。
娶妻,生子,養家糊口,我成了一臺沒有時間來緊發條的機器。我和村里的兄弟姐妹們一起,撇下親人,撇下故鄉,撇下讓我們成長的空氣,不得不像候鳥一樣飛向遠方,然后熬過一段漫長的日子又焦急地飛回來。周而復始。那種日子的長度是我們身上看不見的血管,它足以繞上地球好幾圈。
我們一起罵過這個時代洪流的洶涌,一起埋怨過命運之路的狹窄。但實際上的我們無能為力,依舊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城市的馬路上,工地上,消耗在太陽照射不到的農村的溝溝壟壟里。苦了,累了,我們只能空洞地對自己說一句:要堅強!
人活著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吃上一口有肉的飯,為了妻子能穿上一件有花格子的衣裳,為了父母在死亡的路上走得有尊嚴些……!
這些年,我就這樣奔波在一條艱辛的路上,一頭是希望,一頭還是希望,淚水是我彷徨的腳步!
好在我是幸運的。我結束了那噩夢般的日子,我努力讓自己靠了岸,把孩子,妻子,把年邁的父母攬在了自己并不寬大的港灣里!
我慶幸自己不再漂泊,親人們不再牽掛!
不漂泊是幸福的。不漂泊是一種安靜的幸福,是一種可以休養生息的幸福,是一種能夠靜下心來思考的幸福。我在這種幸福里度過了三年的美好的時光。
但就在2013年9月的某一天,一件與我無關但曾經與我有關的事刺痛了我的心臟,一股滾燙的血液瞬間就噴涌而出……
我才發現,我的過去是無法遺忘的,它已鐫刻在了我的脊椎骨上!
我一直想寫一部小說。現在是時候了,但我馬上就發現我無法把它當作一部小說來寫。
2013年的冬天,深夜伏案的我根本感覺不到季節的溫度,身體好像死的,唯有手指敲在鍵盤上是那樣的矯健。窗外是一個冰冷的,黑洞洞的,寂寞的世界,唯有頭頂上的那盞燈無怨無悔地陪伴著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深夜,從冬到春,從春到夏,到秋,再到冬,那盞燈仿佛眨眼間就老了兩歲,我的生命也離死亡又近了兩年。
我把小說中所發生的故事當作自己的故事來寫,我把小說里的人當作自己來寫的。我又在文字里重復了那段日子,依然有艱辛,有彷徨,有淚水。
當然,對于一個門外漢來說,寫作的過程是極其不易的。好在我還算頑強,既頂住了來自家庭的阻力,也克服了自身遇到的困難,始終沒有動搖過。說實話,我只讀了小學,只是在少年時憑著興趣讀了幾部小說,根本沒有過真正的寫作經歷,即使短文也沒寫過幾篇像樣的,更不要說洋洋萬言。記得寫初稿的速度倒是很快的,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兩個月就寫了17萬字。但真正的艱辛卻是此后的打磨,逐字逐句的斟酌,增增減減,直到最后一個字完結時,已是七易其稿。
有位尊敬的作家說過,一部好的作品不是寫出來的,而是修改出來的。雖然我寫出來的不會是好作品,但就沖著這句真理,我想給他深深地鞠上一躬。
兩年的時間跟十年磨一劍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每一日都真實地融入在《錦江灣》的世界里,睡前琢磨,醒后構思,雙腳時刻邁在錦江灣的村道上。
這兩年不是生命的損耗,而是增加。我活在兩個世界里。當別人鼾聲四起,對世界毫無知覺時,我還在燈光下活著。不是嗎?
期間也有過幾次興沖沖的投稿,但結果都是失望的,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作品自身的問題。好在我得到了眾多文友老師們的無私幫助,他們在百忙之中閱讀了我的文字,并提出了許多中肯切實的寶貴意見,《錦江灣》才得于初步完善。我要感謝他們。是他們催生了我的另一個生命!
《錦江灣》寫的是一群當下農村人的生活。我寫他們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善惡有報,寫他們不屈不饒地追求著美好的生活……
最后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錦江灣》里的那條錦江就安靜地流淌在我的村前,只要跨過流湖大堤,走過瓜子洲就到了。我童年時老去江里洗澡,那水清澈得就如同小說里主人公菊萍那潔凈的生命,無瑕的靈魂,不滅的信念!
現在,我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我撕心竭力地吶喊了一次,為我的兄弟姐妹們,更是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