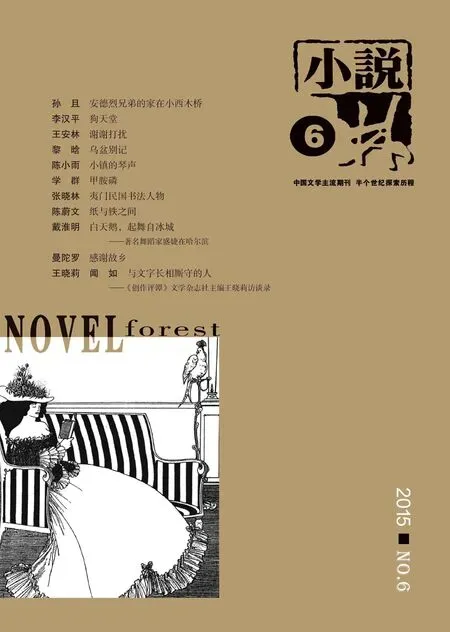謝謝打擾
◎王安林
一個很典型的周末。
劉小白醒得很早,他想,那就是從昨晚開始的吧,或者是從昨天下午開始。他一直在想著這個周末應該干些什么。比如讀一本書,看幾個片子,或者寫點東西。對于劉小白來說,周末沒有特別的意義,也許是特別的沒有意義。但時間就在那兒。時間總是在的。不像一些人和一些事,會走開,會過去。
客廳里的電話響了,劉小白雖然醒了,但他不會去接。他知道,不會有人在這個時候來打擾他。她的周末安排得很滿,有另外的男人和女人。他不怪她。就算不是周末她也不會往家中打電話。電話被人接走了,是妻子周藍。在這個家中,周藍永遠會比劉小白起得早。當然,如果有一天她生病了臥床不起,那是另外一回事。她醒來時,經常看到劉小白打著輕輕的呼嚕,有時臉上還帶著幸福的笑容。她不知道他是夢見了什么。她覺得他真幸福,因為她總是早早的就醒來。她認為自己有強迫癥,總覺得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人在等著自己。想到這些時,她心里面會慌亂一下。慌亂的時候她就會更拼命地去做各種事情。這已經成了她的習慣。電話響的時候,她已經做了許多活兒。每天掃的地又掃了一遍,每天拖的地板又拖了一遍,每天擦的那些柜子桌子還有墻面又都擦了一遍。她正打算去清理衛生間,電話就響了。她也感到奇怪,這么早有誰會打電話。但心里面還是有一種期待。她知道,現在的周末正在變得越來越漫長,就像那些睡不著的早晨,讓人著急。
“猜猜我是誰?”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聲音渾厚,但卻充滿了一種老朋友的熱情。周藍有點懷疑是電視上介紹的那種詐騙電話。對方想引你上鉤,故意不說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在你的焦急中布下陷阱。
“您是——”周藍還真的是急于想知道是誰打來的電話,也許可以改變點什么。一瞬間,她的腦子里面閃過許多熟悉男人的影子。不過,好像都不大可能,她是這么想的,但真的聽不出對方的聲音。哪怕是一個騙子的聲音。
“我是謝芳,”電話里面換成了一個女聲,“剛才是小明,他想裝得有文化一點。”周藍聽出來了,原來是劉遠明夫妻,在他妻子口中,劉遠明永遠是小明,
“我剛剛還說他了,你裝什么裝,再裝人家就將你當成騙子了。”
“是你們呀,”周藍的心里還是有些失望的,但她的聲音里面充滿久別重逢的喜悅,“多少時間沒見了,真的很想念你們。”
兩個女人的話就多起來。看來,真的是有很長時間沒見面了。互相問了對方的近況,說到了孩子,兩個都是差不多大的男孩,都在外面讀大學,說到了孩子的身高體重還說到了有沒有異性朋友。周藍還發自內心地嘆了口氣,如果有一個是女孩,那咱們就結成親家。謝芳那邊就客氣地笑,怎么敢找你們這樣的家庭。電話里面兩個女人好像是要一直說下去的樣子。后來還是謝芳將熱烈的談話中斷了:“今天是周末,”她似乎是要提醒周藍應該做些周末應該做的事,“你們有什么安排嗎,比如逛街、爬山,或者是看一場電影?”
“今天天氣不錯,也許可以做些戶外活動,但我們沒有任何打算。”周藍一邊說一邊朝臥室的門看了一眼。她在想那個睡覺的男人是不是想到過今天是周末。
“你看,我們能不能過來?”
“當然,我告訴他,他會比中了彩票還高興的。”周藍心里面一點把握也沒有。他從來不買彩票。但劉遠明是劉小白的朋友。如果沒有丈夫的這層關系,她根本就不可能認識謝芳。所以,她覺得她是可以替丈夫答應下來的。
劉小白開始刮胡子了。而周藍開始給自己挑選衣服。
劉小白做事情動作麻利,洗臉刷牙還上完了衛生間總共也沒超過十分鐘。他看了看鏡子里面的自己,胡子好像并不明顯。本來今天他不打算刮胡子的,因為是周末。劉小白這么想的時候又看了一眼鏡子里面的自己,沒有精神,空洞,飄忽。如果打個比喻,他想,像一支沒有子彈的槍。
劉小白刮胡子有點怪,他從來不用電動的,也不在臉上涂抹那些刮胡泡和刮胡露之類的東西。他經常看到電視廣告里面那個絡腮胡男人,臉上涂滿雪白的泡沫,然后那把刮胡刀出現,胡子是連同那些泡沫一起被清除的。劉小白覺得自己的胡子并沒有那個男人的頑固和瘋狂,他一點兒也不擔憂。他記不起自己從什么時候開始有胡子的,但記得第一次的擔心,鏡子前面他看到自己嘴唇周圍有了黑色的一圈,也許只是茸毛,他使用了各種各樣的工具和手法,以至于用剪刀在自己的唇邊拉開一道口子。那時他邊上的同齡人中已經有人在使用電動剃須刀,但他第一次使用的最正式的刮胡刀就是手動的。他覺得電動剃須刀有點像割草機,他無法想象一臺割草機在自己的臉上橫沖直撞的感覺。
刮過胡子的劉小白與沒刮胡子前的沒有太大差別。他是這么想的。他想應該吃早點了,否則等會兒劉遠明夫妻就該來了。實際上,他知道他們在另外一個城市,雖說不上有多遠,但也有幾個小時的車程。想起那個城市,劉小白有一些迷戀。他在那個城市有過很多的生活,只是那個城市對于她來說是陌生的。他看到周藍換了一條黑色的長裙在落地鏡子前左右的打量。這讓他覺得房間里面似乎一下子多出了一個女人。鏡子外面的女人向鏡子里面的女人嫵媚了一眼。里面的女人做出相同的反應時,外面的女人已經走開。
當劉小白坐到餐桌前時,周藍已經在黑色長裙外面攔了一條白色圍裙。周藍燒了泡飯,飯是昨天晚上剩下來的。兩個人一起吃了那么長時間的飯,應該可以很好地控制。飯是故意剩下來的。桌上有南方人喜歡的豆腐乳、醬黃瓜,本來還應該有炸油條,但那得跑出去買,路雖然不遠,但對于這個周末來說還是有些麻煩。
“要不要剝個松花蛋?”周藍實際上已經走向儲物柜。她拉開灰色的門,那里面存放了各種食物。她拿出兩個,想了想,又放回去一個。劉小白看到周藍手中拿的那個松花蛋,光光的,顏色與一般的鴨蛋沒有太大的區別,不像傳統的松花蛋,外面有厚厚的一層攪拌了谷糠的黃泥。名不副實的松花蛋在周藍的手上很快就被剝去了外衣,那個光溜溜的蛋被放在了一個小碟子里。在將小碟子拿上來之前,周藍猶豫了一下,她是在想要不要將這蛋切成幾份。后來只是在光溜溜的蛋上面澆了海鮮醬油。劉小白知道周藍一直不喜歡松花蛋的味道,這樣,有著海鮮味醬油的味道就占領了一切。
周藍并沒有坐到餐桌前面。
“他們來了會待一整天吧,”周藍在不斷地將儲物柜里面的各種食物往外拿,“中午我們吃涼水面吧,天氣有些熱了,再開車走路。遠明是北方人,他應該會喜歡,只是不知道謝芳是不是習慣。”劉小白愣了一下,他已經忘了劉遠明是什么地方人,盡管他們曾經同事多年,而且是在一家工廠的一個宿舍里面住過上下鋪。但他知道謝芳是當地農村的。他想起劉遠明第一次帶謝芳到他們的宿舍,謝芳坐在他的床沿,沒辦法,遠明睡在他的上鋪,總不能讓一個姑娘爬到上鋪去垂下雙腿。但他還是看到了謝芳的一雙大腳。謝芳走后,劉小白竟然對著遠明抱怨:“這雙腳也太大了吧,而且根本看不出腳踝的形狀。”遠明有些生氣,他說:“又不是你找對象,我看上的是她的臉蛋。”
“路上得花好幾個小時呢。”劉小白的意思是他們到了,估計也已經過了中飯的時間。劉小白已經將早點用好了。他看了一眼周藍的腳,她穿了絲襪,而且黑裙一直拖下去,幾乎看不到腳踝。他想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她從來不穿絲襪。但今天是周末,他想告訴周藍穿上絲襪也不一定性感,但終于沒說。劉小白想收拾碗筷,周藍說:“我還沒吃呢,你去將冰箱里面的魚肉拿出來,要不,怕解不了凍。”
劉小白打開冰箱的門,一股白氣沖出來,黃色的照明燈下,他看到了一些有顏色的蔬菜,并沒有什么魚肉之類的。他看到下面有一排白色的抽屜,他想,應該是在這些抽屜里面吧。他拉開其中的一格抽屜,抽屜的周圍結著厚薄不一的冰霜,一些紅色的肉整齊地排列在那些冰霜之間。他還看到一些白色的魚睜著黑黑的眼珠瞪著他。這些魚好像是春節時朋友送的,他沒有將魚往更早更遠的時間去想。竟然就在這冰箱里面躺了大半年,如果沒有什么,它們是會一直躺下去的。動一下吧,他伸出手拿出了一塊肉和兩條魚。在拿的時候,他讓自己的手在抽屜里面躺了一會兒。他想,沒事在里面待著還挺好的。
周藍一直在廚房忙碌著。劉小白坐在餐廳里面看報紙,平時的周末他往往一個人待在書房。外面的陽光越來越白,劉小白偶爾會將報紙上看到的他認為有趣的事與周藍說一下。他覺得自己有點像個陪讀者。廚房里面的周藍往往只是一個背影,她的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那些食材上面。當劉小白一個人坐在書房時,她在客廳的電視上面已經學習了許多烹調本領。這些本領足夠她對付任何突然出現的客人。只是這種機會很少。她已經記不起上一次和朋友一起在家聚餐是什么時候。
周藍將晚餐的菜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她本來可以歇一會兒,坐到餐廳和丈夫一起說說話。但她開始找各種杯子:酒杯和茶杯。他們家本來有各種各樣的玻璃杯,是當地一家很有名的企業生產的。她看到過那些晶瑩剔透形態各異的玻璃杯是怎樣制造出來的。那個站在熊熊爐火前面吹玻璃杯的年輕人總是會在一些時候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她的面前。那長長的吹管前面桔紅色的一點,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最后成型為一個玻璃杯。她想,真的很奇妙。她說的是事物。什么事物都是會變幻無窮。只是那家企業早已經倒閉。但她終于還是找出了一個玻璃杯子。她又找出了一個。雖然都是玻璃杯,但都不是一個樣式的。她有些失望。
周藍找出一套茶具,一個茶壺配著六個茶杯,是紫砂的。周藍說:“他們來了,總不能就看著你一個人喝茶吧!”家中只有劉小白一個人喝茶,他只有一個杯子。杯子是白底藍花,但又不是中國傳統的那種,下面還有一個小托盤,也是白底藍花,看起來很相配。只有劉小白知道這不是一套的。她告訴他,托盤是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的小鎮上買的,她在買這個不配套的茶杯的時候,一列火車正經過商店的窗口。
劉小白此刻并沒有在喝茶。他將那個茶杯放在書房。那個茶杯從來就沒有出過書房,即使是給茶杯里面續水,劉小白也是會將水瓶往書房里面拿。這個茶杯好像是擁有貴族身份。此刻周藍在洗那套紫砂茶具。洗好后她將茶具整齊地擺放在客廳的茶幾上。她先是將茶壺放在中間,六個小茶杯圍著茶壺。但放好后又覺得不好看。她覺得這個樣子讓中間的茶壺太自以為是。她又將小茶杯放成一排,她覺得這樣更好一些,六個茶杯既互相關照又各自獨立,都在等待著自己的主人。
門終于被人敲響了。夫妻倆是愉快地也是緊張地去開門。這時候已經是下午的時間。敲門聲讓他們聽起來有點不舒服。門上本來是有電門鈴的。只是這電門鈴在更多的時間里面總是被那些推銷各種商品的人所摁響,劉小白就自作主張地將里面的電池取下來。他想也許應該將電池重新安裝上去的。
劉遠明夫妻帶來了一些禮物,謝芳手上拎著包裝很精美的紅酒和巧克力,而劉遠明的腳下躺著一只碩大的纖維袋,看來從樓下上來,劉遠明和纖維袋都累了。劉遠明一邊將纖維袋往廚房拎一邊說:“這可是好東西,全是綠色無污染食物。”他在周藍的指領下放好了纖維袋,但他沒有馬上出來,而是在廚房檢查周藍準備的那些菜肴。
謝芳和劉小白在說纖維袋里面的東西:“全是我們自己種的紅薯土豆,有周藍最喜歡的茄子,還有出門才摘下來的黃瓜西紅柿。”劉小白聽到周藍在廚房里面發出一種夸張的驚叫:“啊,真的有茄子!”劉小白皺了下眉頭。
劉小白看到謝芳穿了一身白色的套裙,看起來她的皮膚比以前更黑了。也許是因為裙子的顏色,劉小白想。裙子過了膝蓋,但露出了小腿和腳踝,這是大部分中年婦女喜歡的樣式。劉小白并沒有特意去看謝芳的腳踝。謝芳還沒有坐下,她站在客廳與廚房相連接的過道上,這樣就可以銜接兩邊的人:“我們在城郊買了一幢別墅,樓前樓后全是空地,好大的一片,小明說,我們種點什么吧,我想對,種點什么,既可以消磨時間,又可以保證我們的食品安全。”
劉遠明從廚房里面出來,一邊走一邊說:“是你說要種點什么。我說,買別墅,種紅薯,這成本也太高了,是你非得要種。”劉遠明個子矮小,但說話的嗓門一點也不小。劉遠明經常會埋怨這是因為工廠工作太久的緣故。他說,機器那么響,沒有這么大的嗓門誰聽得到。每當這時候,謝芳就會拿劉小白來對比。劉遠明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嗓門有點大,但他會說,人家是讀過書的。劉小白知道劉遠明沒怎么讀書。劉小白進廠時,劉遠明已經工作許多年了,他小學都沒讀幾年。劉小白還是喜歡聽到劉遠明的大嗓門的,他會一下子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劉小白知道現在劉遠明在四川投資了好幾個企業,經常會與那邊的小市長什么的一起開會喝酒。但嗓門還是這么大。
現在四個人都在客廳坐下了。紫砂茶壺里面的茶是早就泡好了的,周藍給每個人倒上茶水。劉小白看到自己的前面也放了一個紫砂小茶杯。這讓他對周圍有了一種陌生感。可這是自己的家。杯真的很小,只能用兩個手指來輕輕地沾起。他有點不習慣。他想回書房去拿自己的茶杯,但只是心里面這么想了一下。劉遠明的手不大但手指關節很粗,拿那小茶杯時,幾乎可以聽到他關節彎曲時的聲音。劉遠明還在說新買的別墅:“邊上有個湖,以前我們經常去游泳的,從這邊游過去就出城了,成片的柳樹,會有很多的知了,然后就是看不到邊的西瓜地。”謝芳說:“那個晚上你提了個西瓜來看我,后來告訴我,是和小白一起在那邊偷的。”劉小白淺淺地笑了,心里面還是有著感覺的。那次他們偷回來的西瓜有好幾個,只是他已經和她分手了。
“你們先聊著,我去做飯吧。”周藍插不上話,所有的一切對于她來說都是陌生的。她似乎看到了那個湖,湖水碧藍如洗,你永遠不知道這水有多深。謝芳也許是感覺到了,也起身說:“我來幫你。”兩個女人就去了廚房。
“她問你現在過得好嗎?”劉遠明的聲音突然變得很輕,劉小白看到劉遠明的臉上浮起一種關懷備至的表情。三十年前的劉遠明也是這么一副表情。“她還是很在意你,她的房子也買在那個湖邊。”劉小白想象著那個冰冷的夜晚,他在湖這邊來來回回地走著。是一個有月亮的夜晚,他曾經懷疑這是一種錯覺。月光也是冰冷的,但他想借月光來取暖。月光涂抹在湖面似乎有了一種誘惑,他想沿著月光走去,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來。
“她說,她想告訴你,那個晚上,她一直在湖邊走著,走著。”
劉小白想,這是同一個湖嗎?
劉遠明將頭靠在沙發背上,他的手指在不斷地擊打著沙發扶手,顯得很有想法的樣子,“那個湖現在成了風景區,造了一些涼亭樓閣,你不會認識了。記得你讓我背《黃鶴樓》那首詩,我怎么也記不住‘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這兩句,你就帶我去了這個湖邊,你讓我看湖邊的柳樹,讓我想象自己是在漢陽,讓我看湖中的小島以及小島邊上的水草。現在這些全沒有了。”
劉小白看到一對十六七歲的小青年,一個初中畢業,一個才讀過兩年小學,那個初中畢業的裝出滿腹詩書的模樣,那個小學沒讀幾年的希望自己腹中也能有幾首詩。那個初中畢業的將《黃鶴樓》倒背如流。輪到那個小學沒讀幾年的了。“有人已乘黃鶴去”,“是昔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后面真的太難了。”小學沒讀幾年的似乎決定放棄了。劉小白搖搖頭,他當時以為劉遠明真的是放棄了的。但幾天以后,她對他說,劉遠明不僅能夠將詩背出來,而且會將詩完整地默寫出來。她說:“你真的了不起!”沒錯,她是夸劉小白。
那個夸劉小白的人是誰?劉小白已經模糊,不,已經沒有了那個人。他想象現在的湖,湖會被那些高樓大廈包圍,當然,還有劉遠明說的那些別墅。即使是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也會被高樓上的那些燈光所淹沒、剝奪,熱鬧總是會戰勝清冷。
兩個女人擠在一個廚房里面。抽油煙機的聲音有點響,看來有些年頭了。廚房有點小,幸好周藍會打理,所有的東西都在它們應該待的位置。臺面上的盤子整齊而有條理,誰和誰搭檔職責分明。
“他們在聊什么?”周藍在為蘋果削皮,她想做個水果沙拉。
“還會說什么,不就是他們年輕時那些偷雞摸狗的糗事,”謝芳在稱贊周藍削蘋果嫻熟的手法,“換成我,一個蘋果削好,怕只剩三分之一的肉。”
“那是因為你們有錢,”周藍笑笑,“有錢的人還在乎這點蘋果的肉。”
“在乎不在乎,真的與錢有關系嗎?”謝芳在她邊上轉來轉去地想做點什么,但總是插不上手。她索性就不做了,站在邊上與周藍說話:“你看你們的生活多好,缺什么吧,什么也不缺,多什么吧,什么也不多,而我們……”謝芳開始埋怨起自己的生活,而剛剛她還是快樂的甚至是幸福的。周藍本來以為謝芳會與她說說劉小白他們以前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可能會讓自己吃驚、意外甚至崩潰,但沒想到會勾出她的不快。
“那時候我們有什么?我在一個很偏僻的小鎮供銷社工作,周末,他們騎著自行車趕過來,那中間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大山。”謝芳的眼睛盯著周藍手里面的蘋果,但她已經看到兩個年輕人,他們穿著白襯衣,皮帶扎在襯衣外面從山上下來,車速很快,那是一種迫切的心情。那兩件白襯衣在小鎮的陽光下分外耀眼。她的臉上有了羞澀。當然,她忽略了其中一輛自行車后面坐著的她。就像現在一樣,他和她在小鎮的那些小攤前轉來轉去,后來他們買了一小籃的櫻桃。太貴了,她說。是太貴了,她也說。兩個人重新坐上自行車,他們過來是接她回城的。她永遠記得兩輛自行車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盤旋的畫面,春天,滿山的映山紅,還會有不知名的鳥兒突然從前面飛過。她的雙眼迷惘了。
“不過,我覺得小明對你挺好的,”周藍將幾樣切好的水果都放在一個龐大的玻璃器皿里面,她往里面倒那種乳白色的色拉,“你看,你們剛才在電話里面的情調。”周藍一邊用力攪拌著,她想,不滿意的應該是自己,但她沒有在任何場合向人傾訴的習慣。
“可是你不知道小明以前有多么在乎我,”周藍可以感受到謝芳站在邊上的分量,她覺得她們的距離太近了,剛才劉遠明進來的時候應該更近,但她沒有這樣的感覺,而現在她似乎可以感受到她的呼吸,她身上多余出來的一些東西,“他再懶得看我一眼,回家只是吃飯睡覺。吃飯時,他會嫌這個菜咸了,這個湯淡了。只要一躺下,他就會呼呼大睡,也不知道是真睡著了,還是裝的。我們剛認識時,他告訴我,小白說你的腳太大。當時我還在心里面嘀咕,小白怎么會注意我的腳。你不知道,當時他就用雙手捧著我的腳說,這么漂亮的腳,怎么會是大了,他拼命地親我的腳,親得我全身癢癢的。”
周藍說:“我先將水果色拉放冰箱里面冰一會兒。”她是覺得自己的身體不自在了。渾身的不自在。謝芳并沒有觸碰到她,但她感覺到她的手在自己的身體上肆無忌憚地游走,甚至到達了那些敏感的地方。怎么可以這樣。
謝芳一步不拉地跟著她,嘴巴像打開了的閘門滔滔不絕。謝芳說到劉遠明不知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地愛上了打球,是打那種羽毛球。他買了成套的球衣球褲還有很貴的羽毛球拍,每天早上晚上都會去練球。“但他的球藝從來就沒有長進,他是喜歡上了一個女人,”她竟然是那么直接地就說出來了,“他裝模作樣地穿上球衣球褲,拿著球拍,嘴上還哼著小曲,而實際上他的心里面想著的是和那個女人見面。”
周藍將水果色拉很快地放進冰箱,她的樣子有點害怕。她看到劉小白穿戴整齊地出門,他平靜地告訴周藍,是去與朋友喝茶,晚上可能會晚點回家。
這頓飯吃得輕松而愉快。
如果是晚餐,時間還是有點早,所以大家都是不慌不忙。盡管其中有一對夫妻是要趕回到他們自己的城市。劉遠明說他喜歡晚上開車,特別是現在這樣的天氣,打開所有的車窗,然后,讓風進來。他說得好像是一首詩,大家都習慣了他的附庸風雅,所以并不認真。周藍的烹飪技術征服了所有人,盤子的干凈程度可以證明。這讓周藍很是有些得意,但她沒有顯露,而是不失時機地恭維一下謝芳,從發型說到服裝。這時候,最適合的話題是說說孩子,孩子的過去和現在,還有將來。盡管兩個女人已經在電話里面有過交流,但那是遠遠不夠的。
“長得越來越像他爸了,”謝芳覺得應該對剛才周藍對她的贊揚有所回贈,“我敢肯定,周圍應該有許多女生追求。這孩子,從小就知書達理,文質彬彬。”周藍覺得謝芳好像不是在贊美孩子,而是說孩子的父親。不過,不得不承認謝芳說得很正確。孩子很英俊,他應該會有許多女生追求。她經常想象兒子和女生擁抱接吻的場面。她擔心的是孩子會不會把握好那最后的一關。有時候,就在那一瞬間。
男人們本來是應該喝點酒的。周藍已經問過劉小白。那些酒也已經擺上了桌面。劉遠明的酒量大得出奇,如果時間允許,他看似矮小的身材可以裝下整箱的啤酒。“只是今天不適合,”他給自己倒了一杯橘子汁,他已經喝了五杯了,“作為一個合格的公民,我們應該嚴格地遵守法律,”他是一臉的嚴肅,“我們得對自己的身體負責。”他說的當然是指不能醉駕,但以前他不是這樣的,他是可以在大街上與任何人打上一架的。劉小白想,不知道的人會以為他現在是喝醉了酒。就算不喝醉酒,一個人可能對自己的身體負責嗎?劉遠明的話讓四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周藍將水果色拉拿上來了。謝芳幫著給每個人前面擺上叉子。兩個男人并沒有打算使用那種亮閃閃的金屬叉子。劉遠明已經在拿牙簽在剔牙齒,他拿一只手捂著另外一只手,顯得很有教養的樣子。周藍希望他能用點水果。劉遠明還是沒有運用那把叉子,他直接拿手上的牙簽去叉了一塊水果。劉小白笑了笑。他知道劉遠明從來就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但周藍不這么認為,她在心里面想,他去見那個女人時難道也是這樣?。謝芳依然是快樂的,她在稱贊水果色拉的味道,至于剛才說了什么,她已經忘記,但誰又知道呢?
謝芳和劉遠明要回去了。劉小白與周藍將他們一直送到他們的車前面。天還沒黑,那輛車停在一棵叫不上名的樹下面,樹的葉子有點像含羞草,但花是粉色的,如果有風,那些花瓣會灑落到車上。周藍去樓下的車庫里拿了一塊毛巾出來。謝芳接過去擦去車上的那些花瓣。“這些花瓣怎么這么熟悉,”她一邊擦一邊說。劉遠明已經坐進駕駛室,他說:“擦什么擦,快走吧,我們已經打擾他們一天了。”他將車發動起來了。謝芳也坐進了車里面,她搖下車門,真誠地對劉小白和周藍說:“不好意思,打擾了!”
“謝謝打擾!”劉小白與周藍互相之間看了一眼,竟然不知道這句話是誰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