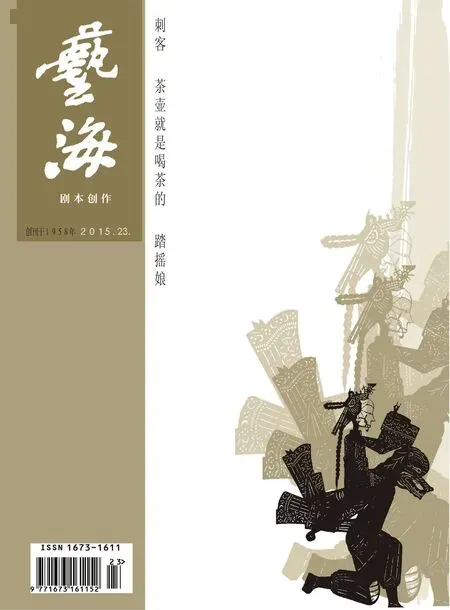《踏搖娘》創作漫談
吳 戈 子 方 云南藝術學院
《踏搖娘》創作漫談
吳 戈 子 方 云南藝術學院
很大程度上,歷史和文化,是依賴于文獻的事物。
這是從秦漢開始就定下的。從那個時期開始,一切歷史的記錄和文化的沉淀,都要依賴文字和圖像的記錄——可以說,沒有了文獻,很可能就丟失了歷史,同時也就湮滅了文化,也正是因為如此,幾乎在每一次考古的大發現中,都包含著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因為,這些文獻資料可以更加清晰地解釋清楚跟我們之間存在著重巒疊嶂、并遠隔千年的歷史。
因此,我們景仰、崇拜著文獻。
而戲劇史中的文獻資料,更是我們不能忘情的瑰寶。這些瑰寶,展示了中國戲劇從無到有的漫長的過程,記錄了中國戲劇從分散到聚合的完整形態的變遷——其中的任何一段記載,任何一個形象,都使得我們為之迷戀不已、難以忘懷:優孟衣冠、黃公搏虎、參軍參鶻、踏搖歌舞……這些款款的形象在古老的文字篇章中浮現著,只存在于只言片語之間,卻讓人們琢磨了百年千年。
選擇踏搖娘,正是出于這樣的迷戀和忘情。
一
吳戈是我的老師。
十年前,吳戈老師還在為云南藝術學院的本科生講授“戲劇概論”。在課程講授中,他反復提到踏搖娘的歌舞風姿,街頭歌舞、阻斷街市、顧盼之間、眾人癡迷,這是何等的狂熱,然而,即便是這樣精彩的、得以舞動全城的演出,卻只在戲劇史上留下這樣的文字記錄:
北齊有人,姓蘇,鼻包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怨,訴于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斗之狀,以為笑樂。
這并非文學語言的簡要記錄,看不到表情,聽不到語氣,一方面,文獻記錄著歷史,但另一方面,文字也壓縮了歷史。留存的是印象,丟失的卻是骨肉。作為一代一代的戲劇人,當然可以想見,戲劇史上的踏搖娘是怎樣的精彩,然而,曾經的萬人空巷不應該僅僅埋沒在經籍的記載中,過去的“人簇看場圓”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灰色的地帶;這些過去只言片語的記載,應該再度活躍在活色生香的舞臺上——
所以,當十年后,老師跟我談起踏搖娘的創作思路時,我同感興奮。這就是我們創作《踏搖娘》的第一層愿望,希望將文字變成血肉,為歷史注入生機。
二
第二層愿望,是希望完成一次有趣的猜想。
作為戲劇研究者,我們從戲劇史中得到這樣的認知,踏搖娘的歌舞,在文字記錄的表現中是:且步且歌,謂之踏搖;并且,演唱者一邊唱,觀眾還在“和”,這可以理解為幫腔——
于是,身處云南的我們,很容易就想到了云南花燈。
崴花燈,也是一邊唱,一邊舞蹈(且步且歌);而這種舞蹈的姿態,也很像“踏搖”,擊地為節,阻街斷市,這在今天的云南花燈歌舞中,依然存在著。
于是,將云南花燈的形態和踏搖娘的記載合起來,居然可以達成一種非常默契的統一,這很有意思。目前,在中國話劇界,越界和混搭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現象,既然話劇可以,為什么云南花燈不行呢?因此,不妨就以花燈來演繹踏搖娘的故事,從踏搖娘的歌舞開始,將這種舞步和歌聲從長安一路帶到云南,并且,就在云南進行著這樣的歌舞,最后讓踏搖娘留在云南——也將這種踏搖歌舞的形式留在了云南。
值得一說的是,以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猜想是有趣的,但未必能夠合理地論證,但是,作為創作者來說,這樣的猜想又充滿了讓人創作的動力。說起來,我們當然是研究者,然而,對于《踏搖娘》來說,我們更是創作者,因此,在創作作品的時候,創作者的身份取代了研究者,我們期待共同完成這次創作——而非純粹學理的猜想。
三
愿望之三,出于我們對云南的認知。以劇情所示:踏搖娘和崔十郎長安相見即分別,陰錯陽差,崔十郎被發配充軍,攻打南詔——這就將云南和長安聯系在一起了,將南詔與大唐聯系在一起了,將邊疆和中土聯系在一起了。
這種聯系,就是我們的創作愿望。
長久以來,云南人總會以這樣一種開場白來表示出一種近乎自卑的謙遜之心:“我們云南地處邊疆……”
久而久之,面對著與邊疆相對的中部和東部,這種謙遜則漸漸演化成了一種價值的自棄,落后、蠻荒、貧窮、不開化之類的形容詞就變成了一種極端的標簽,無論我們是否愿意,這種標簽都時時顯現著。并且,還異化為一種奇特的想象:男女情愛的隨意、奇風異俗的順遂、艷遇之都的迎合……這都來自于云南的自卑。
實際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自信。
何以自信,可以隨意列舉兩個現象。
現象之一,2013年,西南聯大大講壇邀請余秋雨先生來到昆明舉行講座,在講座中,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話讓在座諸多師生感動落淚,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云南在抗戰時期,作為中國的大后方,接納了很多來此避難的文化人,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網兜,在中華民族面臨巨大危機的時候,兜住了這個民族的文化種子,而在危難過去的時候,將這些保存住的文化種子,又完好無缺地還給了中華民族——在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當中,云南是發揮過作用的,而且發揮的是重要作用——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講述當中,完整地表達出了對云南的感恩和敬重,這和我們云南人對自己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云南,說到抗戰后方記憶的時候,云南人多有些慶幸地認為:那些從北京、上海等大地方來到云南,豐富了云南的文化,提升了云南的戰時地位;但事實不僅如此,一方面是文化人的匯集,另一方面,也是云南土地的接納,正因為有了云南的接納,這些文化的火種,才會在一個烽火時代被歷史留存,而中國文化的命脈,也就在云南紅土地的承托下,最終被保住了。想想莫高窟失寶的不幸,想想皕宋樓去國的不甘,云南的淳樸與寬厚,應該讓人肅然起敬。
這是可以讓我們自信的第一個現象。
讓我們自信的現象之二,是一副長聯。清人孫髯翁,以大觀樓楹聯聞名于世,此聯不但篇幅宏大,更重要的是,氣象闊朗,文風瀟灑,處處顯現的是自在自如的生命狀態和文化品格,抄之暢快,讀之淋漓,試看這樣的語辭:“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有文采而無矯飾,氣通達而不做作,沒有八股文章的了無生趣,也沒有桐城學派的書憤苦讀,不是文字管制下的小心翼翼,更不是落魄學人的酸苦吟說,相比同期中原、沿海、江浙的地區文風,這副長聯,反而多了不少靈動的天然文氣,且,其中還蘊含了非常真摯的對西南風光的喜愛和自信——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時至今日,我們的自信去到哪里了?當我們看到,獵奇、情愛、野蠻、落后成為吸引旅游者的噱頭,當我沒看到這種噱頭被進一步放大進入文藝創作,當我們看到經濟開發者帶著優越插入云南生態的平衡圈,當我們看到原生的云南文化被迫改換基礎、接受“文明開化”,我們就會陷入深深的不安和擔憂之中。
因此,在創作中,我們愿意、也期待著,將云南與中土并置,表示:云南從來就不是一個居于人下的地域,云南文化也不應該是一個偏安西南一隅的“等待開發”的形象,云南,是中國西南邊疆的七彩形象,獨一無二,如果因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表現出了自棄傾向,實則謬然。
這是我們的愿望,更是我們的責任。
因著這樣的出發點,我們讓崔十郎來到云南,又讓踏搖娘千里跟隨從軍,也來到云南,讓兩人的情感線索,與云南發生一次撞擊,碰撞出歷史深處的火花,這也未嘗不可。
四
今年是2015年,離《踏搖娘》的首輪演出,已經過去了兩年。這兩年來,我們師徒忙于各自的教學任務、研究事務,吳老師更是要忙于繁重的行政事務,對于《踏搖娘》這個劇本,居然到今天才再度打量。
應著玉溪市花燈劇院李鴻源老師的作曲,我邊聽邊讀劇本,讀完劇本之后,我們依然認為,這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也是一部很有意味的作品,要說到編劇對作品的認識,我們愿意從如下幾點來具體談談:
首先. 傳奇故事的劇目,它不是一般地塑造一個英雄或者是辨別一個道德善惡的劇目,而是通過這個傳奇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力量和人性力量傳遞一些藝術信息和人生況味的劇目。中外戲劇史上或者電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多是寫“人”著稱的,有很多是以寫“事”著稱的,我們創作的立足點就是在寫一個傳奇故事,就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像梁祝這一類的包含了人情、人性、社會內容在其中的故事。從這些事兒中所品出的、析出的,是不一樣的人生況味兒和特別的命運內容。
第二.這個作品要以樂舞來貫穿花燈,就是一種典型的樂舞的藝術樣式,人聲為音,物、器演奏出來的是樂,而音、樂都有混融的樂舞,這正是花燈的特點。這里面除了花燈的唱段,還有《蘭陵王破陣舞》,蘭陵破陣舞和踏搖娘舞蹈,分別作為男性舞蹈和女性舞蹈貫穿始終,群眾的演戲和兩個人物的交流都要注意攥緊男女舞蹈體系的意識,每一環節的前進,舞蹈交織、纏繞、綿延著,緊緊扣在那種舞蹈的節奏上。每一個場面,每一個細節,每一次舞蹈處理,都必須在舞蹈系統當中承擔分量,因此,無論是市井的踏歌,還是營中軍儺,無論是單個舞蹈的展示,或者是群眾場面的處理,都要在這個舞蹈體系中把“舞”的因素用足、用好、用妙。當然,它是花燈的舞步,這就需要我們的舞蹈編導想方設法尋求“變化中的不變,不變中的變化”,花燈舞蹈主題,西域的、東南亞佛國禪姿的,便無不要用心體現這種創作意圖。
第三.在花燈歌舞里邊,扇子、繡球、彩綢一類小道具是非常重要的表現工具,要用足用好扇子在整個《踏搖娘》劇目的演出過程當中承擔的功用:它應該既繼承花燈的扇舞的傳統,又突出扇子作為面具可開、可合、可隱、可顯的運用便利性,因此要構建一個扇舞的系統,不同形狀的扇子是不同文化含義、不同色彩的面具,也是不同的場景渲染的文化符號,因此,無論是蘭陵王破陣舞,還是踏搖娘在街頭踏歌,或者是其他群眾場面,都要用扇子完成面具的遮蔽功能、轉換功能,扇子既是人物的形象符號,又是假定性的功能屏障;所以,舞美對扇子的設計,要下十分功夫。材質、色澤、款式、畫面、面具形象,都要與群眾場面的舞隊、人物交鋒交流的細節、場面渲染的需要相配合,要將扇子用好、用足、用妙。扇子是面具、扇子是舞蹈道具、扇子是假定性屏障。
第四.面具要把扇面作為基礎平臺來構建一個面具的符號系統,舞美設計要在扇面所表現的面具形狀、色彩以及與它出現的細節場面所表達的情緒、所呈現的意蘊相配合,整個面具構成的場面位于壯觀的時候,要讓人嘆為觀止,表現男歡女愛、情深意切的時候,要極盡纏綿。面具是一個命運符號,面具是一種咫尺相隔卻永不能相會的命運阻隔,面具是人生的讖語,面具是文化意蘊、人生況味兒,因此,如果面具是體現文化意蘊的話,扇子就是美學呈現的平臺。
第五.踏搖娘的命運線索是一個兩小無猜時節的“定情等郎”——10年不歸聞噩耗后的“嫁錯郎”——無顏相認的“丟郎”——滿心急切地“追郎”——費盡心機的“留郎”——悵恨凄涼的“失郎”——的動作線索,這要體現在情節的貫穿動作里邊;一送、再送;苦留尋、苦等;痛別,淚舞,是干凈的動作線索。兩次匆匆別離,兩次迎娶的承諾、一生一世的等待,構成整個劇目的文學結構和動作節奏。
第六. 為什么要唐明皇和李龜年出場?一是增加歷史文化的厚重色彩,像是唐三彩的稠濃;二是將梨園老郎唐明皇的風月游戲嗜好與安史之亂的悲劇、草民的民間離亂悲劇作一種隱性的邏輯關聯,讓觀眾從李、楊皇家愛情悲劇到踏搖娘、崔十郎市井小民的生活悲劇之間建立某種社會歷史的聯系,讀明白一些歷史內容;三是結構上是一個套層——敘述中的敘述;節奏上是一種調整,發展中的停頓。敘述結構與表現內容,在意義上是有邏輯關聯和意義暗示的:梨園人生的皇帝關心的是人間悲歡的戲劇性!他是悲劇的制造者,也是悲劇的承擔者,問題是他至死都未曾醒悟。絕不要理解為單純的敘述形式,那是藝術技術主義、形式主義的誤區。
以上,是編劇對《踏搖娘》的自我認知。
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