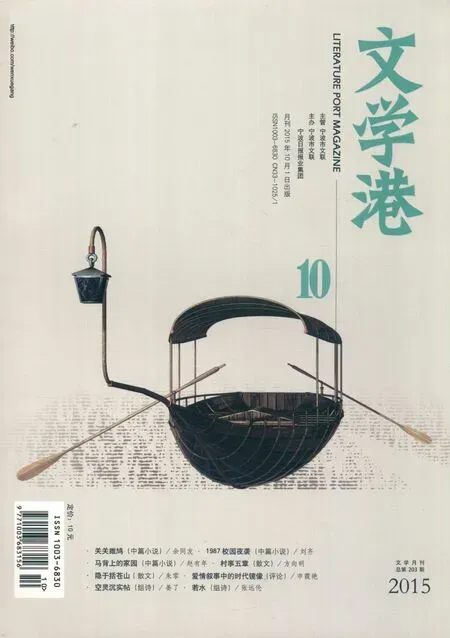放手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
謝志強
放手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
謝志強
一個戰爭與愛情的故事。或說,是一個戰爭中男人與女人的故事:買辦的女兒和兩個男人,一個是中國人陳小羊,一個是美國人華爾。
按照常理,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得去接近她,但是陳小羊選擇了遠離。不但選擇了遠離,還投奔有買辦資助戰爭洋人參加戰爭的敵對一方——太平軍。而洋槍隊的組織和率領者華爾則是對付太平軍的另一方。這樣,必定有故事,出故事。
尋找是小說的一個母體。此前,趙柏田出過一部長篇小說《赫德的情人》,那是一個關于尋找的故事,赫德的兒子來中國尋找父親赫德的情人,最終尋找的對象成了一個民族。但《買辦的女兒》里的陳小羊尋找的方式,采取了疏遠并且投奔到敵對方面進行另一種尋找——打敗情敵華爾所在的聯軍、洋槍隊,從而消除情敵。我想到卡爾維諾的一篇小說的主人公也是尋找,參戰的目的就是為了復仇,利用戰爭復私仇,以至戰爭結束,仍不歇手。可將趙柏田的兩部小說視為姐妹篇。赫德也出現在《買辦的女兒》里,是個次要人物。有意味的是兩部小說的開端(或序章)均設在寧波,由此拓展人物活動的更大空間。
但是,不要為這個表層的故事外殼所迷惑,不要以為買辦的女兒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其實,這僅僅是個由頭和起點。或說,是小說意義上的國內戰爭故事的邏輯起點和基石。因為,涉及到這部小說的一個關鍵的難點:敘述視角的確立。
這些年,趙柏田沉浸在“歷史“之中,從中提取素材,然后,交替采用兩種表達式:散文和小說。散文的主角往往是大人物(名人賢士),他只能在有限史料的束縛中敘述,可以看出他搜尋、考證史料的嚴謹和艱辛。有時,我想,一個歷史的細節“解密”,過去的史料會崩盤會失真。趙柏田的小說就灑脫、從容多了,他從史料中殘缺之處起飛,用想象創造另一種“歷史”的真實。他給歷史小說帶來了別致的樣式。兩部小說里的人物尋找的過程,均顯示出考證性質的精準和細密。《買辦的女兒》序章廢墟中新建的“月湖盛園”可留給后人現場考證。他還營造出了一個彌散著氣息、氣氛、氣味的“月湖盛園”。
小說關注的是小人物。選擇陳小羊承擔那場國內戰爭敘述者(農民起義的太平軍對清政府的聯軍、洋人的洋槍隊)。既是冷兵器向熱兵器的轉換期,也是大清國的封閉走向被動開放的轉折期。現在,史學界習慣把中日甲午戰爭視為現代性的轉折點,趙柏田的小說隱含著一個史觀:甲午戰爭僅是個總的“爆發點”,此前的淤積要上溯到太平天國運動。所謂內亂外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段內戰的苦難記憶——現代性的前夜,仍延續了造反和鎮壓的千年模式。小說里有關夜的敘述,是一種隱喻,之后夜色漸濃。
以陳小羊的視角,表現戰爭中的人。趙柏田設定的這個視角,可謂用心良苦。《買辦的女兒》這部小說的成敗,取決于陳小羊這個人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功能性。因此,賦予了陳小羊諸多身份:買辦手下會英語的小伙計,與買辦的女兒青梅竹馬,忠王的義子、特使、軍火采購員、間諜以及華爾的情敵。買辦又是華爾洋槍隊的資助人(洋槍隊是當時中國的一個怪胎)。
小說寫的是關系。確定了人物基本關系,那么,作為小人物、小視角陳小羊擁有如此的身份、任務、性格,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游走在交戰雙方,本意是“尋找”戀人和情敵,以“在場”的姿態所見所聞——對戰爭知情到什么范圍和程度,就有了可信的基礎,常常是第一人稱的有限視角兼有了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由此,展現出整個戰爭的全景和進程。但是,作者主要還是寫戰爭中的人。主要人物又側重戀情。戰爭和愛情、愛情與尋找、個體與戰爭,通過陳小洋將這樣的關系有機地聯系起來。以小示大。
從而引出小說真正意蘊,可歸納為主題詞:思念,位置。尋找和夢想落實在思念和位置上。
所有人物的位置因戰亂而身不由己地發生了變化。作為情敵,陳小羊的愛的夢想,華爾的錢的夢想(還包括趁機以買辦的女兒作交易)都最終破滅。小說里寫了許多夢想(中國夢,美國夢)。戰爭是個絞肉機,身份的變化,使得人物在戰爭中的位置處于險境。
趙柏田著重寫了戰爭中的愛情——陳小羊單相思的愛,相當執著、執迷。正因如此,才有了這部小說的主體部分:思念的表達。
貫穿全書的人物陳小羊表達思念的方式有兩種:情書和獨白。
當下的網絡時代,陳小羊這樣的思念已經成了稀罕。思念是書信時代的特殊情感,因為,它跟距離和封閉相關。趙柏田把握了十九世紀的一個時代特征——小小的物件也就是遺存至今的七封情書,來表現陳小羊的思念之情。
全書,一個序章,一個尾聲,主體部分七章,由七封情書和獨白構成。作者放手讓貫穿全書的陳小羊說話,其實是愛的傾述。因為愛,才有那么多話要說。獨白的特點是沒有聆聽者,起先,還有幻覺中單相思的“你”:買辦的女兒梅。隨著戰爭的殘酷,那個傾述的對象漸漸隱去,仿佛預示著梅的消逝。
情書和獨白這兩種表達式,對象是同一個人——買辦的女人,而且,情書引出獨白,獨白補充情書,隨著戰爭的惡化,兩者像愛戀的兩個人那樣,漸漸疏遠,似乎戰爭在消除愛戀的痕跡。明顯的兩套筆法:情書,主觀的意象(比如第一封信起首一句的棗紅馬)充滿詩意,而且熱;獨白,客觀的紀實(比如:記錄戰爭進程的時間月、日、時,以及死亡人數),透出冷漠,還很冷。
獨白表現出的戰爭全景,使我想到希臘古典史學家希羅多德《歷史》的筆法:縝密、精確。希羅多德是個講故事的高手。趙柏田在《買辦的女兒》里發揮出他歷史研究的底氣,像撰史書一樣寫小說中的戰爭。暗示出陳小羊也是趙柏田對那場國內戰爭的態度和看法。陳小羊這個見證者,掌握了戰爭的能見度,甚至,偶爾也去掌控,但戰爭中的人,都是那么渺小那么無奈。各方力量為了各自利益,糾結一起,把戰爭推向高潮。
思念是中國文學傳統的重要母體。一個國家變局中的一個人的思念,思念展現出一個國家的亂象。那是史書上不屑記載的小人物的境遇,恰恰是小說關注的重心。
閱讀三十余萬字小說《買辦的女兒》過程中,我像眼睜睜地看著滾雪球。這個歷史戰爭題材的故事,買辦的女兒僅是一個核,在戰爭的雪地里滾動,漫天大雪,雪球無情冷漠地滾動,越滾越大,把各方面各種人(洋人、海盜、冒險家、戀人、官員、商人)統統卷入,各種利益、權力、位置、身份、夢想、欲望裹挾在雪球里而不由自主,更何況脆弱的戀情。這僅僅是發生在蘇寧滬的戰爭一角,卻表現了天朝覆沒,預示了甲午戰爭。
趙柏田也通過陳小羊的視角,啟用了一種超越戰爭的視角。亂局中總需要有清醒的人。一個是懷才不遇的王瀚,第五章,陳小羊和王瀚邂逅,王瀚對時局的分析和預測:亂象之始。然后,一個細節——拉開窗,江風浩蕩,灌滿屋子。像是打開了謎一樣的黑屋。
另一個是洋人林德琍,他迷失在戰爭迷霧里,失卻了愛妻后失望、醒悟,他要記錄“這段充滿血與火的演變過程”,以寫作來自我救贖,他預言了戰爭的意義和前景。還有,第一章末尾,華爾少年時追隨一只蝴蝶而墜入大海,預示了他的宿命,還暗示了蝴蝶效應——戰爭風暴。細節不經意就有了寓意。
夢想從商卻從軍的陳小羊在轉化為陳保羅的過程中,其第一人稱的敘述,仿佛作者已沉湎在陳小羊這個人物里,但忽視了陳小羊的學養,他能那么書卷氣甚至淵博嗎?偶爾,也感覺陳小羊的視角夠不著,出現不在場而展現戰爭的廣闊的情況。
這部小說,眾多人物,有的在史書上有記載,有的是入不了史書的小人物。大人物,小人物,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在戰爭中都有一個相對完整的運程。表現時,趙柏田采用了兩種方法,一種是像希羅多德記史的筆法,像寫歷史那樣。
另一種是博爾赫斯小說的方法,即真實的人物和虛構的人物混搭在一起,史料與想象融合在一起,真假難辨,創造出如真如實的小說效果。這樣游刃有余,得益于他對史料充分、扎實的掌握和研究。國外有很多學院派的小說家,例如,意大利的安貝托·艾柯,兼學者與作家于一身,寫歷史題材的小說。作家可分兩類。一類是從書籍到小說,博爾赫斯、艾柯、尤瑟納爾等均用這種方式創作,書籍就是他(她)的生活。另一類是從經歷到小說。海明威的小說差不多就是經歷的轉化。當然還有兩類結合的作家。趙柏田屬于從書籍(主要是史料)里提取素材的學者型作家。
這是一部長篇充滿了聲音的小說。如果說《序章·花廳往事》彌漫著懷舊氣息的話,那么主體的七章響徹了聲音。序章的氣息引出了主體的聲音。然后,放手,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陳小羊的情書和獨白——傾述了戰爭,還通過引述的方式,叫其他人發出聲音(連僅有幾百字記敘的一個農民的兒子,也發出了吶喊式的聲音)。這種聲音被戰爭喧囂所覆蓋(有興趣的讀者可統計小說列出的死亡人數,那是曾發出過但已發不出聲音的生命);終于,聲音由小說的語言固定,成為了歷史的真實。
(《買辦的女兒》,作者趙伯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