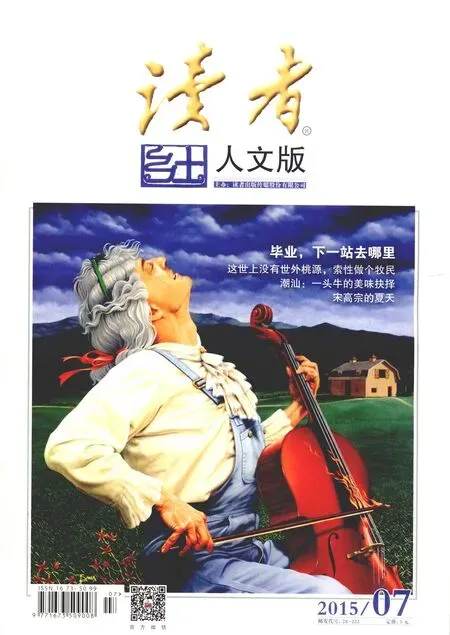夏日隨感
文/btr
夏日隨感
文/btr
癢
有些事,在發生的當下你渾然不覺;你發現時,已是事后。夏日被蚊子叮咬,便是如此。你很少能有機會目擊蚊子的作案全過程:它僅有2.5毫克左右的身體輕盈地降落在你裸露的肌膚上,然后用它的6根口器溫柔地刺進你的身體—比體檢時找不準靜脈的笨拙護士高明得多—等它以每秒594次的速度拍打著翅膀揚長而去時,你根本不會知道這一切已經發生。像麥田圈一般神秘的蚊子腫塊將漸漸隆起,你會覺得癢,而這癢的感覺,就是你在不經意間向昆蟲界的紅十字會義務獻血后的收據。夏日之癢是一種后見之明式的、遲鈍的敏感。科學界人士會說這是人的身體對含有蟻酸、抗凝血劑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質的蚊子唾液的過敏反應;而文學界一般認為,它是一種隱喻,是微小的失去之后身體對于欲望的覺醒。
穿堂風
夏天,你無法怪罪那些在弄堂口赤膊讀晚報的爺叔們,只要你懂穿堂風。是啊,他們露著B罩杯的胸和F罩杯的肚腩,稀疏的頭發映照著黃昏街邊剛開的路燈,在隔壁飄來的一陣干煎帶魚和毛蟹年糕混雜的香氣中乘涼。他們或許沒有環保意識,但他們真心喜歡夏日的穿堂風。這是一種或許可以申請成為文化遺產的風,在這多數人已遷進不知隔壁鄰居叫什么的公寓時代,它已經成了一種局部地區的風,一種過去時的風。穿堂風是那個時代夏天的官方福利,具有親民的力量,它令爺叔們那些或被解讀成粗魯的裸露變成自然的、天體主義的、環保的元素。穿堂風,因此也是潮流之先風。
知了
據說世界上最著名的蟬來自美國,名叫“17年蟬”,它們在地下蟄伏整整17年后才破土而出。所謂“知了”,其實是境由心生,一如不同人聽見蟬在盛夏“知了,知了”地鳴叫時,會有不同的反應一樣。煩躁者聽了愈加煩躁;淡定的人則或將之視為某種恒久的夏日布景,使聽覺如同洗了一個盆浴一般;而另有一些人將這整樹的蟬鳴視作一個整體,在它們無意的和聲里聽出了和諧的意思;但一個自稱對知了“知了”的人說,蟬鳴是夏日之肆意,是想唱就唱,是明明白白地“知了”。
席子的清涼感
對于喜歡席子的清涼感的人而言,開足空調裹在被子里睡,簡直就是對夏天的背叛。空調制造的小環境有一種暴力般的氣息,它不由分說,就好像在朗誦某段關于“人定勝天”的宣言,直到第二天清晨的鼻涕流下前,都無人反駁。而席子是順勢而為的溫柔的清涼。微涼,如同微醺,是對邊界的探尋,它便呈現出夏夜最本真的一面。在有點涼的席子上睡,有時依舊覺得有點熱,但這不就是夏天應該有的感覺嗎?
夏天永不結束般的倦怠
學生們的暑假會在8月31日準時結束,然而夏天不。在夏天的某個時刻,你總會有一種“就好像要永遠如此”的錯覺。在這個城市,夏天是漫長的。日復一日之后的倦怠感,像一盤小賭注的麻將一般令人生厭。尤其當臺風不再來,當雷暴云團失了蹤影,當知了不再歌唱、連蚊子也懶得叮咬時,夏天進入了空窗期。人們心中隱隱期待夏天倒塌,然而氣象臺的首席預報員永遠不會倦怠,他會適時出現在晚間新聞里,向市民們一遍遍解釋,氣象意義上夏天的結束,是指當連續5天平均氣溫在22攝氏度以下時,再追溯那5天中的第一天,那便是夏日之終、秋日之始。
(呂博一摘自《周末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