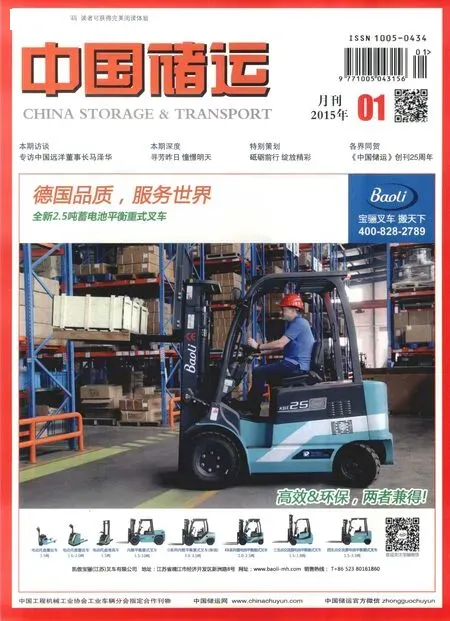依憲治國才能推進(jìn)社會轉(zhuǎn)型
文/李煒光
依憲治國才能推進(jìn)社會轉(zhuǎn)型
文/李煒光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依憲治國”的方針,要求全國上下“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zhǔn)則,并且負(fù)有維護(hù)憲法尊嚴(yán)、保證憲法實(shí)施的職責(zé)。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并把每年的十二月四日確定為國家憲法日,這在我國,無疑是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件了。
憲法為一國之“元規(guī)則”,主要用于約制國家公權(quán)力。無憲法亦無憲政,或有憲法而無憲政,均可以視為“無憲”狀態(tài)。“無憲”則政府角色定位不準(zhǔn),與市場和社會的界限劃分不清,對于轉(zhuǎn)型社會來說,更容易出現(xiàn)體制復(fù)歸、政府職能和規(guī)模持續(xù)擴(kuò)張以及分權(quán)改革半途而廢的問題。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政府的行為模式發(fā)生了過度集權(quán)的傾向,行政權(quán)力無邊界擴(kuò)張,耗費(fèi)巨量納稅人資財?shù)墓こ添?xiàng)目與官員的個人私利密切相聯(lián),不能被置于有效的約束和監(jiān)督之下,這種徹底官僚化的權(quán)力運(yùn)作體系給我們社會帶來的危害,不亞于任何舊時代的政治腐敗。
改革開放36年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這條路走的并不順暢,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在放開和引入市場的同時,它本身不但沒有依市場要求退出,而是愈加強(qiáng)勢地參與其中,成為當(dāng)今社會中最強(qiáng)大的市場主體,不僅指揮市場、駕馭市場、調(diào)控市場,還直接參與市場的競爭和運(yùn)作。在2008年以后的幾年里,政府干預(yù)之手幾乎運(yùn)用到了極致,成了全社會最大的投資主體。
問題在于,這個熱運(yùn)行多年的體制,嚴(yán)格說并非真正的市場經(jīng)濟(jì),而是某種混雜了計劃經(jīng)濟(jì)殘留物的混合體制,它或許能在短時間內(nèi)保持較高的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卻在推動現(xiàn)代國家轉(zhuǎn)型方面難有建樹。事實(shí)證明這種“政府推動型”的高增長果然難以為繼,因?yàn)樾聞?chuàng)價值多歸于政府,結(jié)果只是政府動員和汲取資源的能力變大。資源消耗得越快,民間得到的就越少,經(jīng)濟(jì)陷入停滯和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四萬億”的刺激政策本應(yīng)維持一個中等時段的增長效應(yīng),結(jié)果只過了兩年就掉頭向下,2012年就不得不啟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刺激政策,而新屆政府的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只堅持了不到一年多就因“經(jīng)濟(jì)太差已超出了總理承受范圍”,而在2014年末到來之時轉(zhuǎn)而實(shí)行央行降息的政策,宏觀調(diào)控重回“凱恩斯之路”。
這樣看來,經(jīng)濟(jì)學(xué)中所謂政府失靈,就不只是簡單的“政策失靈”問題,而是政府保障經(jīng)濟(jì)社會正常運(yùn)行的功能出現(xiàn)了系統(tǒng)性失靈。更大的危害在于,這個已然失靈的政府卻還擁有巨大的和不受約束的權(quán)力,缺乏外部力量督促其在法治和民主的軌道上運(yùn)行,這樣的政府,注定會成為市場運(yùn)行首當(dāng)其沖的對手,與民爭利,與市場爭地盤,終將導(dǎo)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和社會轉(zhuǎn)型的失敗。因此,我們有必要強(qiáng)調(diào)以下的判斷:所有偏廢政治體制改革的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遲早會陷入權(quán)力的合法性危機(jī)和普遍的腐敗困境,此情此景,其實(shí)已經(jīng)在我們的生活中真實(shí)發(fā)生了。
所以,“依憲治國”的首要問題便是政府守法,而主要不是指公民守法。所謂政府守法,就是政府權(quán)力受預(yù)先制定規(guī)則的約束和監(jiān)督,包括監(jiān)督監(jiān)督者的權(quán)力。社會中不能存有絕對的、不受制約的權(quán)力,不論這權(quán)力來自于何方、歸何人掌握。因?yàn)橹挥袘椫浦鞑拍芗s束住權(quán)力,也只有經(jīng)歷憲政民主的洗禮,才能使當(dāng)權(quán)者和社會公眾懂得自己應(yīng)該承擔(dān)什么樣的責(zé)任、義務(wù)和遵守什么樣的法律。
一個現(xiàn)代國家在設(shè)置它的“元”規(guī)則時,首先要在稅收和預(yù)算上著力,用立憲的方式,給政府財政權(quán)力預(yù)設(shè)法律邊界。政府之手必須保持干凈,保持利益中性,并訴諸“知情權(quán)”來接受公民的審查。成熟的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和民主政體、權(quán)力制衡和相互監(jiān)督機(jī)制、新聞與言論表達(dá)自由和與此相適配的財政信息披露制,這三大原理構(gòu)成了政府合法性的來源。現(xiàn)在不少學(xué)者常錯置語境,以為政府天生具有自我約束能力,而熱衷于建議開征那些只有在強(qiáng)力約束下才可以開征的稅種,以及可以開支的項(xiàng)目,其結(jié)果很可能是災(zāi)難性的。
我們一直習(xí)慣于將中國的制度變遷視為“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其實(shí)它遠(yuǎn)非經(jīng)濟(jì)問題所能概括,而是政治、文化和社會的整體性、全方位的轉(zhuǎn)型,或曰現(xiàn)代國家建構(gòu),現(xiàn)在這種認(rèn)識顯然已經(jīng)陳舊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應(yīng)當(dāng)就是“依憲治國”,理由很簡單,只有憲制才具有這種博大的涵蓋性和綜合性。
用我曾經(jīng)的一篇文章的標(biāo)題為結(jié)語:憲法的陽光照耀著中國。

勢……不可擋 梅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