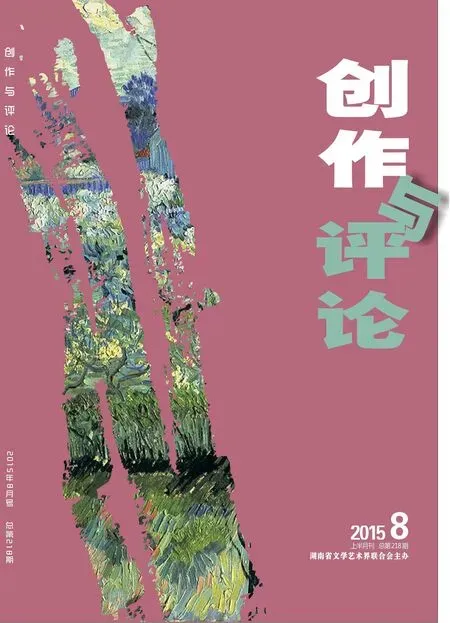生之殛
○ 熊育群
一
營田,岳陽屈原管理區中心鎮。汨羅江由東向西流入洞庭湖,營田既是汨羅江的入湖口,也是湘江、資江的入湖口,岳飛在這里曾剿滅過楊么的農民起義軍。當年長沙會戰打響,這里發生過最悲慘的一幕。
1939年9月23日,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眼看新墻河就要攻破之際,他派出上村干男支隊從第二道防線汨羅江防線后面包抄過來,凌晨偷襲了營田。日軍就像一把刀插入中國守軍防線的左翼,這一刀不但使新墻河、汨羅江二道防線不攻自潰,還可切斷兩道防線守軍的南退之路,同時向守軍側背給予重重一擊。
我一直無法把連天的戰火與這個偏僻寧靜的小鎮聯系起來。爆炸與濃煙就在這些連片的房屋中出現,悲慘的情景簡直不能想象!一場日軍投入兵力10萬、國軍30萬部隊參戰的世界級戰爭在這里打響!這一天如此血腥,用血流成河不足以說明人的驚悚、恐怖與沉痛。戰爭在人們的睡夢中降臨。僅營田一帶被殺害的百姓就有800多人,國軍戰士犧牲1200多人。1000多間房屋被燒毀。火海中的營田街有人來不及躲避就葬身于火海,燒焦的尸體從樓上滾下來。連剛入殮的死人也燒成了灰。有人披著熊熊烈火逃生,日軍發現立馬補一槍。人們逃到離營田街三十多華里的馮家塅,男女老少站在一片墳塋上,看著火光沖天的營田街,無不失聲痛哭。
巷口吳村鄭德清伯父一家,全家四人被殺,女人懷有身孕,被殺后,日軍又把她的肚子破開,肚子里滾出一個“哇哇”哭的孩子,日本兵一刀將孩子刺死。三歲的孩子哭喊著爸爸媽媽,撲到了媽媽的懷里,一個日本兵一刀戳進孩子的肛門,將孩子挑起來,高高拋向空中,周圍的日軍哈哈大笑,鼓起了掌。
太山屋易敬生一家三口,易敬生是私塾老師,他認定日軍不會殺讀書人,因此沒有逃。日軍一進門就把他抓了起來,一把按倒在地,來了個五花大綁。隨即一槍打死了他的老婆。當著易敬生的面,他們撲向他的女兒,剝光了她的衣服,玩弄一番后,施行輪奸,一直把她輪奸至死。易敬生不停地掙扎、咒罵。日軍用鐵絲把他吊到橫梁上,淋上煤油,把家具砸爛,堆放在一起,點了一把火。易敬生火中還在不停地詛咒……
二
許多年里帶著這份沉痛的記憶,我總是在反復問自己:日本軍隊為何如此兇殘?這一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這個一衣帶水的近鄰我們為何至今都缺乏了解它的愿望?誰能保證悲劇不再重演?
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之前的甲午年,旅順已經慘遭屠城,兩萬多人被殺。有一對母子,母親被殺于巷口,嬰兒爬到母親身上找奶吃,孩子的嘴與母親的奶頭被淚水和奶水凍在了一起,收尸的人都難以分開他們。只是43年,悲劇就重演了,更加殘暴更加血腥的屠殺幾乎波及了整個國土。
痛定思痛,我開始注意日本這個大和民族,從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 開始,我讀一切研究日本的書籍,從小泉八云的《日本與日本人》、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網野善彥的《日本社會的歷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歷史》、奈良本辰也的 《京都流年》……我進入日本的歷史文化,尋找著緣由,我渴望了解它的國民性。
讀川端康成的《雪國》、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聲》 等當代作家的小說,一種凄美的情境令我心魂惻然,它們有一種致命的吸引。這情境有東方含蓄、蘊籍之美,而它的哀傷、凄婉與悒郁卻是大和民族獨有的。凄美也在浮世繪的畫中出現,甚至在神社廟宇紅的鳥居白的紙垂上也能讀出。日本人從櫻花的絢麗、短暫與落英繽紛中尋找凄美,把它選為國花。武士就喜歡在櫻花樹下剖腹,為情義、為報恩、為洗刷污名赴死。這一切沉沉底色便是死亡,是死亡的意識。大和民族是一個對死亡有沖動和激情的民族,其“空寂”“幽玄”“物哀”的審美傳統便是死之幽谷開放出的花朵。
“菊”與“刀”兩種相互矛盾的東西一同成為大和民族的象征,正如它的好斗與和善、野蠻與文雅、尚武與愛美、順從與抗爭、忠誠與叛變、保守與喜新、傲慢與自卑……這種喜好極端的國民性就如和辻哲郎的《風土——人類學的考察》寫到的,處在季風氣候的島國季節性與突發性相容,熱帶氣候與寒帶氣候交替,塑造了日本“寧靜的激情”、“戰斗的恬淡”的國民性格。
《坂上之云》 是表現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歷史的電視劇,劇中舉國上下由維新鼓動起來的朝氣與強國意識有如島國的溫泉,灼熱、霧氣蒸騰。明治維新廢除等級制,取消武士階層,人人平等。他們像從前學習中國一樣,全面學習西方。其亦步亦趨的學習姿態被西方人譏諷為“猴子”。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在這里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不受威脅而不得不戰,所謂的威脅便是一旦一方控制朝鮮,沒有控制朝鮮的國家就感到了“威脅”。日俄戰爭爭奪中國東北的殖民權益,卻被說成保護朝鮮不被沙俄染指。朝鮮的“安全”又要靠中國東北來保障了!而東北變為滿州國后,它的安全又要靠華北來保障了!他們一步步的擴張都找得到堂皇的理由。這種強人邏輯,沒有侵略,沒有是非,先籌劃先開槍的反成了無辜者,而被殖民者不存在了,他們不配享有安全與自由,就如他們所說的進入了等級秩序世界。直到今天,吞并朝鮮仍被稱作合并,侵華稱作進入,釣魚島主權歸屬之爭,參拜靖國神社,仍是強詞奪理的邏輯。正在推行的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參與全球軍事行動,理由仍是為了國家安全。
日本“近代化教父”福澤渝吉的《文明論概略》 在明治維新時期出現,他引導日本把眼光投向西方,他在《脫亞論》 中宣稱日本脫亞入歐。“禽獸論”也出自他的書中:“禽獸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國,日本也是禽獸中的一國,應加入吞食者行列,與文明人一起尋求良餌,以在亞洲東陲,創立一個新的西洋國”。這就是日本的征服經。
同一時期,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內村鑒三的《典型的日本人》 在給國人強調日本的獨特性時,也開始為大和民族是優秀民族大造輿論。
迅速強大起來的日本,國民自信心不但從美國“黑船來襲”的驚嚇中得到了恢復,而且繼續膨脹,其結果是開始孳生起蓬勃的野心。這時,大亞洲主義思想出現,日本由“脫亞入歐”戰略轉向“排歐入亞”。他們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大陸才是他們的出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出現了,一個被西方欺凌的國家轉過身來瘋狂地欺凌自己的鄰邦。
三百多年前,豐臣秀吉武力掃平戰國群雄,統一日本,又出兵朝鮮,他那時就夢想著親自渡海,坐鎮寧波,攻占中國,將日本國都遷到北京。日本舊夢重拾,談論經略大陸的話題,變成了維新大業討論的問題。
與希特勒一樣,日本灌輸自己民族為優等民族的觀點,甚至認為全世界只有他們是神的子民,天皇來自神界,日本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是一個神國,是天地間最初形成的國家,是萬國的主宰,因此,全世界都應該成為日本的郡縣。偏激的思想越走越遠,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甚至認為日本的風景也優于亞洲鄰國,可與西歐并駕齊驅,連活火山也得到了勇壯的贊頌,他把這些與國民精神聯系起來,以此鼓舞新興帝國日本的士氣。志賀重昂在這本地理學啟蒙書中準確地預測了甲午戰爭。
有人提出了日本要拯救亞洲,大東亞范圍內的國家都是同一人種,亞洲人應該幫助亞洲人。日本有責任把“支那”從白人手中解放出來,建立起一個大東亞共榮圈。弘揚大義于八纮,締造神輿為一宇。
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言論: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還有英國、俄國從東亞驅逐出去。打一場亞洲人自衛自存的圣戰,勘定禍亂,光復和平。各國都應該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立自己的位置,這樣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斗。這一秩序的領導者只能是日本,因為日本是唯一真心自上而下建立了等級制度的國家。唯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之大業。
膨脹的繼續發酵必定導致對其他民族的鄙視,日本以救世主自居,最后發展到不把別的民族當人。中國留日學生就被日本人稱為“豚尾奴”。
可怕的思想一萌芽,它就像一劑興奮劑,甚至是迷藥。它讓人越來越偏離真相,越來越癲狂,接連的刺殺與宮廷政變,直到軍人當政的極權統治出現,廣場、街頭運動開始了,它直接變成了陰謀家的武器,不只是對外也用于對內。
三
幾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在大理街頭閑逛,在一家舊書店無意間發現了馬正建寫的《湘水瀟瀟——湖南會戰紀實》,書中引用了一個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上世紀六十年代寫的《不堪之回首》 一書中的內容,這是一個有關中秋節的故事,她在1939年中秋節踏上了我老家的土地,作為慰問團一員前來慰問皇軍,這是她費盡了心力才爭取到的機會。
沒想到真的見到了她新婚后參軍出征的丈夫。經歷千辛萬苦,一對夫妻在戰場見了面,雖然部隊給他們放了兩天假,但打仗部隊沒有駐地,他們還得跟著部隊走。他們坐在最后一輛收容車上,兩手相扣,難舍難分。沒想到收容車拋錨了,前面的車都走遠了,這時,樹林里面響起了槍聲。
她的丈夫近藤三郎拿著槍就跳下了駕駛室,與車廂上的兩個士兵一道還擊。槍戰中近藤三郎被打死,近藤富士之把他抱在懷里,輕輕呼喚著他的名字,要他跟她回家。
近藤富士之被中國軍隊俘虜了。
這一段文字讓我震動、深思。第一次看到一個日本女人真實的思想感情流露,如果不是營田慘案的影響,我會傾注更多的同情心。作為一個人,我們之間究竟有多大的區別呢?它讓我回到了日常的生活,回到了常識。這個時候我有了新的寫作沖動。我覺得自己有了進入人物內心的能力。我要寫一對日本戀人和一對家鄉的戀人,在這場戰爭發動之前,他們的生活與生存狀態其實并無多大區別,真摯的愛情,待人接物的友善,日常生活里的溫情。戰爭來臨,這一切急劇變化,這個出征的日本青年懷抱報效天皇的忠誠,告別親人,遠赴征途,從一個正常人一步步變成殺人魔王。我從隨后獲得的侵華士兵日記里看到了大量豐富的細節,看到了這一變化的歷程。
戰爭扭曲人性,摧毀生命,它一經發動,就像一個機器,誰都無法控制了。兩對毫不相干的戀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這是荒誕的現實,卻是戰爭的邏輯。從個人到民族到國家,悲劇在一步步滑進。營田發生的如地獄般的景象變成了現實。
但是,日軍為何如此殘暴?!
帶著諸多的疑問,壬辰年春天我去了日本的九州和關西。甲午年冬天又一次去了東京、房總半島、伊豆半島和北海道,一個月里我仔細地體驗著、觀察著。
在房總半島千葉縣鴨川市江見町見到了岡部喜一,他的父親就是侵華士兵,是步兵第二一二聯隊第一機槍中隊的機槍手,從昭和十四年到十九年,他參加了魯東、魯西、魯南、魯中作戰,陣光作戰、華南作戰、浙贛作戰、中原會戰、武號作戰、勇號作戰,輝二號、三號作戰以及勢三號作戰,作戰之多時間之長都是令我驚訝的。他在高齡去世,在他家客廳佛堂中放著他的照片,清瘦的臉上深深的八字紋分開了頰骨與人中,一副憨厚的老農形象。他的法號喜翁全徹居士作為牌位擺在右側,正中是佛祖的銅像。按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人死后靈魂都能與神佛同在。它的靈魂已跟佛祖在一起了。這就是當年以機槍掃射殺人無數的士兵?!
岡部喜一的父親從不談他在中國的經歷,一提起他就感到難受。岡部喜一說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是,客廳顯眼的位置掛著一個鏡框,里面是毛筆字寫的中隊歌、參加的作戰和時間,中間是三個伏在機槍上的士兵的線描像,大號字的部隊名稱寫在上面,兩邊各飾有一顆五角星。岡部喜一說他父親是在家被強行征兵走的,當時不去就要坐牢。
一棟百年老宅,巨大的坡屋頂從四面傾斜而下,翠竹樹木長滿山岡,墓地與神社在山坡下彩幡飄揚。冬日的稻田之上,群鴉鳴叫,鷹在低空翱翔,來自海上的風托舉著它的雙翅。屋內百年火塘仍燃著紅紅的炭火,取暖、烤魚、燒水,賓主圍爐而坐,晏晏笑語。一個人在這里出生、成長、遠征、歸來、耕作、終老,看不見他的一生與罪惡有染,秘密全在他的緘默里,帶入了墳墓。即便是罪惡,這里的人也早已忘卻,一切就這樣翻過去了。
找人翻譯,中隊歌唱的是:“黃河的流淌/為楊柳新芽帶去青蔥/春天里/聚集在軍旗下/我們是第一機槍部隊/啊,戰友呀/騎上我們的愛馬/奔走在魯西無邊的泥濘里/借手中的韁繩傳遞給它一個永恒的信念/留存在那馬蹄下的/是崇高的豐功和偉績”。
在滿田清家我看到了一套十六卷本的《昭和日本史》,第三卷是《日中戰爭》,打開來,圖文并茂,我看到了當年他們準備慶賀武漢淪陷的照片,圓柱形的大燈籠上寫著大大的“祝漢口陷落”。接著是學生參加陸軍墾荒訓練的隊伍,少年們舉槍向校園里的天皇照片致敬,幼兒參加軍隊體驗活動,小女孩用紅蘿卜喂馬,表示對軍隊戰馬的慰問,幼兒的劍道訓練,兒童軍小隊的選拔,婦女支前集體勞動的場面,市民排隊購買“支那事變報國債券”,炸毀的街道上行進的軍隊,歡送參軍上前線的人潮與旗幟的海洋,城市里各種群體活動,各種行軍打仗的場景……對于戰爭,只有過程與技術性的描述,所有的屠殺都看不見了。
詢問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的看法,就連二松學舍大學年過花甲的教授源川彥峰也說不知道,他說自己出生于二戰之后,但政府從沒有說出過真相,他所受的教育也沒有這方面的內容。
想著營田田野調查那些日本兵的行為,我很想告訴他這一切,但沒有說話的語境。對他來說,這些是遙遠陳舊的歷史了,與現實生活沒有關系。
真的沒有關系了?當然不是。當事者還在,被傷害者仍然感受到又一次的傷害,特別是日本右翼開始占據統治地位,銷煙味似乎越來越濃。
在靖國神社,每天都在展出一個二戰士兵的遺書。神社四周栽種的紀念樹斛樹,獻木者大都是海陸空部隊、遺族會、戰友會、軍校。神社前的常陸丸殉難紀念碑,是日俄戰爭被俄艦擊沉的運兵船,題詞者是元帥伯爵東鄉平八郎,他就是甲午戰爭下令向中國運兵船“高升”號開炮的日軍“浪速”號巡洋艦艦長。還有田中支隊忠魂碑、慰靈之泉、戰跡之石。戰跡之石的石頭來自沖繩、硫黃島、馬尼拉郊外等各個戰場。即便千葉縣安房鴨川這樣偏僻的小城市,也有紀念的神社,忠魂碑也是東鄉平八郎所題。
特別是神社北面的帕爾博士表揚碑,2005年建立,立碑表揚其功績。帕爾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擔任印度代表法官,他是法官團中唯一提出判處被告團全體成員無罪意見的人。
但是,面對具體的人,老農民、教授、學生、店員,我又無從說起。翻譯梁鎮輝制止我的眼神在明確地告訴我:這沒有必要,這會造成不友好的氣氛。糾纏這樣的問題變得不合時宜。
奈良東大寺,有捐款者在泥瓦上留言,這些留言的瓦燒制后在寺院翻修時將嵌入屋頂。一個壯年男子用毛筆認認真真寫下:“世界和平”。
源川彥峰教授帶著一個班的學生,以《論語》 為題材,在鴨川町的一個漁村進行創作,學生們以篆書刻寫了“禮樂”“忠恕”“德不孤,必有鄰”……對儒家文化,學生們十分喜愛,他們真誠地向我請教。
在熱海,賓館服務員全體出門送行,他們一次次深深鞠躬,一個女子跑得氣喘吁吁,她發現房間丟下的東西,趕緊沖下樓來。酒店里,無論用具的設計還是服務都極盡體貼之能事。凡問路,他們必熱情指引,有的親自帶路。睡在鴨川的幾晚,大門、臥室都不用上鎖。各地神社的繪馬,寫滿了家人平安、學業有成、良緣成就、無病息災的祈愿……他們與那殘酷的一幕的確風馬牛不相及了。
但是,在大和民族的精神深處,恥感文化、武士道精神,他們看重的信仰與清潔的藝術的生活,這些民族重要的特性也發生了變化嗎?那些喜歡盲從的習慣,那些內外有別、強大的集體意識,部落時代遺留下來的這些特性也在改變?他們有時連“氣氛”也可以讓一個人放棄自己的意見。
武士道視偷生為羞恥,把求生的愿望看作卑怯,二戰時它賦予暴力宗教一般神圣的意義:“每一顆子彈都必須注入帝國的光輝,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精神”。殘忍與審美竟然可以揉和在一起,越是殘忍越顯得美。死亡成了一種表達手段,一種抒情的方式,舍身赴死的儀式化甚至達到了“凄美”的至境。日本人對復仇和捐軀盡忠津津樂道,四十七士為主尋仇而集體剖腹,日本人將之代代傳頌。
現在,赤穗城四十七士的墓地成了旅游地。在東京成田機場,我在書店仍然看到了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還有《日本刀知識》。靖國神社當年鍛打日本刀的匠人還在打著刀。東京日本武道館,第三十八回日本古武道演武大會開始,這天,入夜時分,下起了一場早春的囉囉細雨,舊江戶城田安門的古城道上,傘若長龍,人流如鯽。年輕人對演武的熱情不減。在明治神宮至誠館,練習劍道、射箭的人也都是年輕人。城西國際大學渡邊淳一院長的女兒也遠道從鴨川來東京學習劍法。這些能否證明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留在大和民族的生活中?
四
一個民族把刀對準另一個民族總有自身的緣由與過程。我進入歷史,探尋它的源頭,其初始階段無疑便是教育。
十九世紀晚期,日本以新兵訓練的方式培養小學老師,師范生入住軍營,接受嚴格的紀律訓練與思想教化。上世紀30年代,《國體主義》《臣民之道》相繼頒布,教育體制軍事化,小學生排隊要求步調一致,學生如果不從,教師打學生耳光,狠的用竹棍、木劍抽打,更狠的,一是命令學生負重跪地,二是冬天赤腳站在雪地里,三是圍著操場跑步,直到力竭倒地。
他們奉行的邏輯是:“我打你不是因為我恨你,而是因為我關心你,你以為我把自己累得雙手紅腫流血是瘋了嗎?”這樣的邏輯放大來便是:戰爭不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戰爭的受害者從中獲益,暴力是取得勝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勝利將對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框架下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中國。
故意縱容南京大屠殺的甲級戰犯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就曾這樣說:“我去前線并不是與敵人作戰,而是懷著撫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國……我們必須將這場戰爭視為促使中國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我們深愛他們。這就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兄長對弟弟的不端行為忍無可忍時,為使他改邪歸正,不得不對他進行嚴懲。”
再看希特勒這段話:“心懷愛國之情,奔赴戰場時感覺如同去舞場赴宴一般。”瘋狂的人心理的扭曲變態也是一樣的。殺人魔王有殺人魔王的邏輯,那時日本人甚至把中國人比喻成細菌,殺人不再當作是在殺人了。當日本兵開始殺中國人時,在他們的心里就跟拍死蒼蠅蚊子差不多了。
那個年代,日本玩具店里也充斥了坦克、頭盔、步槍、高射炮、軍號、榴彈炮和士兵的玩具,男孩子握著竹竿當槍在街頭玩打仗游戲,有人將木棍捆在背后,扮演人肉炸彈自殺式襲擊。
老師大都換成了軍官,他們向學生灌輸日本天定命運就是要征服亞洲,大和民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優秀種族,而協助國家完成這一神圣使命是每個學生的責任。年齡小的男孩操木制槍訓練,大一點就使用真槍,槍桿比他們人還高。他們灌輸對中國人的仇恨和蔑視,視中國人為低于人類的物種。曾有一個男孩上生物課解剖青蛙時嚇哭了,老師敲他的頭吼道:一只爛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長大后還要殺一兩百個中國佬呢。
這一切,背后無疑藏著不可告人的擴張野心,島國的危機意識,經濟的衰退,使得他們需要新的領土來避免饑荒。
從什么時候日本人開始蔑視中國?曾經他們把中國當作自己的老師,視為天朝上國。日本先民彌生人、渡來人就來自這個遙遠的大陸,他們是蒙古人種。日本的文字、佛教、建筑,甚至官階、律令都來自中國。日本古代的歷史都要從中國的《史記》《漢書》等典籍中尋找,一千多年前日本還沒有歷史,古墳時代,他們連自己土地上留下的巨墳也搞不清楚。
他們學習漢字,學習中國的典籍和詩歌,學習中國畫和書法,甚至庭園建造也模仿中國山水畫。儒家文化更是深入人心,孔子的《論語》、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他們都認真閱讀。白樂天、李白、杜甫的詩,還要背誦。日本俳句的蘊藉雅致,與唐詩氣韻是相通的,它們感觸于風物,都有對時序與自然的感興,充滿禪的意境。他們迷戀竹林七賢、蘭亭雅集、雪夜訪戴。漢文化在古代日本只有貴族才能學習和掌握。
說什么華夷變態,說中國經累世紊亂,被異族統治,已經不是正統的漢人了,甚至罵中國人為豚尾奴。這一切,轉折點就在清兵入關,特別是鴉片戰爭中國神話徹底破滅了,中國人卻仍然那么自大,那么自以為是,顢頇,腐朽不堪,日本人尊敬中國的歷史從此終結。他們眼里只有強者。他們喜好狐假虎威。
踏上中國土地的士兵人手一本《軍人敕諭》, 《軍人敕諭》 與《教育敕語》 一樣是圣典,一個針對軍人,一個針對師生。 《軍人敕諭》 是一份長達數頁的文件,綱目分明,文字嚴謹。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義務。忠是大節,是一切道德的準繩。盡忠的軍人必有真正的大勇。軍人要逐字背誦,每天早晨默想十分鐘。祭祀日、新兵入伍、期滿復員要隆重宣讀。宣讀之時,從安放處恭恭敬敬取出,聽眾畢恭畢敬,全場鴉雀無聲,比基督徒對待摩西十誡和舊約五書還要神圣莊嚴。如若念錯,捧讀者要引咎自殺。
《教育敕語》 至今在明治神宮的神樂殿里可以免費領取。
侵華士兵最初無不相信這場戰爭是正義的圣戰。應征入伍的士兵為能到中國去為天皇效忠,有的激動得跪了下來,認為沒有什么比上戰場更能表達對皇上的忠誠了。“效忠天皇重于泰山,個人生命輕如鴻毛”“寧當護國之鬼,不受生俘之辱”“為了東洋和平,為了建立新秩序”“殺人不是罪惡,那是對祖國的忠誠”“中日戰爭是圣戰,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這些話幾乎天天在士兵耳邊響起。
有士兵想到,既然自己的生命輕于鴻毛,中國人的生命且不更輕?這種踐踏生命的邏輯讓屠殺變得更加順理成章。
一個正常的人殺人必須有正當的理由,還必須有恨。保持理性很難殺人。為了克服新兵這種心理,日軍專門把俘虜拿來試刀,逼著新兵無端端當面把一個人殺死,就是要讓他發瘋。有的下不了手,軍官就當場示范。殺過人的士兵上戰場開槍殺人就沒有那么困難了。這是一種心理訓練,也是在培養戰爭機器。
日軍以地方為建制,戰友都是老鄉,一旦有士兵戰死,必然引發同伴的仇恨。雙方會因此而殺紅眼。這時候戰爭完全以殺人為目的。有的日本士兵在想家的時候,也會莫名地恨中國人。到了最后,為了睡一個安穩覺,日軍會把全村的人殺光。有的士兵把殺人當成了取樂。人的命比豬還不值錢。
這種由正常人一步步變成殺人魔鬼的過程記錄在一個個日軍士兵日記里。大和民族是一個喜歡記日記的民族,很多老兵寫了日記,寫了他們怎樣來到中國,怎樣投入戰斗,怎樣殺人,一天又一天怎么度過。我尋找這樣的日記, 《東史郎日記》、《荻島靜夫日記》和太田毅寫的《松山——全軍覆滅戰場的證言》,每一本得來都不容易。長篇小說《己卯年雨雪》 中幾乎所有日軍殺人的細節和戰場的殘酷體驗都來自這些真實的記錄,我并非不能虛構,而是不敢也不想虛構。
后來又找到了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室寫的《一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的《國軍抗日戰史專輯》,還有當年湘陰縣縣長謝寶樹的日記《守土日記》,醞釀了十年的小說終于找到了一條路徑,他們的現身說法讓我進入了故事現場,創造和還原一段歷史終于成為可能了。
許多日本士兵回國后不愿談論他們在中國的經歷,他們不愿回憶這樣悲慘的往事,有的生死之交的戰友也不愿出來參加聚會。長崎縣一個叫上野正義的通信兵回國后成了打漁人,他在佐賀火車站奇跡般遇到了同一個中隊的戰友龜川肇,他們曾在云南松山全軍覆滅時逃了出來,逃跑路上他曾想自殺。他們都以為對方死了。那晚相聚談到天亮,分手后至死也再沒有聯系了。《松山——全軍覆滅戰場的證言》 的作者太田毅談到采寫的緣由,就是要告訴人們軍隊上層作戰的愚蠢和無情。而很多老兵承認:“中國人的心是溫暖的。”
中國作家寫抗戰題材小說鮮有以日本人為主角的。這一場戰爭是兩個國家間的交戰,我們叫抗日戰爭,日本叫日中戰爭,任何撇開對方自己寫自己的行為,總是有遺憾的,很難全面,容易淪為自說自話。要真實地呈現這場戰爭,離不開日本人,好的小說須走出國門,也讓日本人信服,除非他們就是有意要否認這一場侵略戰爭。我想,超越雙方的立場,從仇恨中抬起頭來,看到戰爭給兩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尋找真正的罪惡,這對一個作家不僅是良知,也是責任。
我要寫仇恨與寬恕,寫人類之愛,寫戰爭之痛,那種無法撫平無法想象的痛,即使活著心靈也永無寧日,正如營田那個黑色的日子,它是親歷者一生也走不出的噩夢。戰爭中的人性與命運,戰爭對人血淋淋的摧毀,人類道德的大崩潰,廣泛的惡行,悲劇性的生存,愛情的悲慘……我希望這一切不只是激起普遍的悲憫,還有對于人性與現實的反省。
而民國時期的洞庭湖,那個遠逝如同夢幻般的世界,有著奇異又魔幻的生存圖景,遠不只是動蕩與悲壯,它從戰爭的硝煙間正朦朧又清晰地呈現出來……
我一次次網上搜尋,重回1939年9月23日這個日子,它在各種不同的方式里呈現,那時的禁忌與節日,節氣與星期,天干與地支,運程與生肖,平年與閏年……既遙遠又親近,仿佛靠近了那時期人們的生活。
我一次次走到營田百骨塔,那場偷襲唯一留下的遺跡。1200多將士在此戰死,老鄉們埋了親人又含淚收集了400多位烈士的尸骨,埋葬在這里。這里紅磚水泥的樓房遍布,擠占得墓地越來越窄,雜草蔓生,鳥在枝上筑巢,荒涼衰敗,香火全無。
大戰既然不知,百骨塔自然遺忘一角,像個神秘事件的入口。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圍湖造田建立屈原農場,營田變成農場場部,來自四面八方的農民遷入這里。墓地薛岳題寫的“浩氣長存”碑文還在,兩邊是挽聯:“虎賁三千熱血一腔無反顧,秋風入月寒潮萬里有余哀。”每一次默誦,哀傷的情緒總是潮水一樣淹沒我。我想,等這本書出版后,把書在墓前燒了,以我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來祭奠英靈。
只求靈魂安息,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