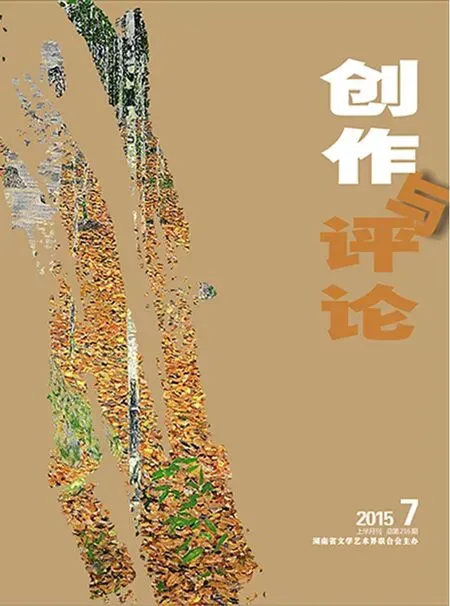現代性視野中的“鄉愁”
——李健鄉土小說創作評析
○衛華
現代性視野中的“鄉愁”
——李健鄉土小說創作評析
○衛華
以湘中梅山為場域,湖南籍作家李健創作了一系列鄉土文學作品,從《霜天霜地》《陽光撒徹山地》《約定坳螞蟻》到《白鼠》《泥巴魚》再到《幸福的花朵》《天上的鴨子》等,都是其中的精彩之作。作品承繼汪曾祺、沈從文等京派鄉土文學的精神氣韻,將梅山,這一本是偏僻鄙陋、乏人問津的湘中山區,描述得風姿卓越,引人入勝。而同時,他也敘寫了在現代城市化進程的喧囂沖擊下,梅山人的掙扎與裂變: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城市與鄉村,多次元的二元對撞中,李健有現代性的鄉愁。
一
李健的鄉村文學系列,首先是有根據地的。著名文論家謝有順曾言,好的小說家大都有一個自己的寫作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可能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也可能是精神學意義上的。福克納一生都在寫他那郵票大小的故鄉,而魯迅的小說,基本上是他故鄉發生的故事,沈從文的如是,莫言的如是,張承志的如是,史鐵生的如是,賈平凹的也如是。李健也如是,他文本里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地方——湖南一個叫梅山的地方。李健自己曾明確提及這個地域概念:“我作品中的梅山,并不具體指某一座山——那只是一個寬泛的地域概念,昔時包括邵陽、隆回、新化、漣源、安化、益陽等地。我是湖南新化人,新化地處梅山腹地,是生我養我的地方。”①看來作者有著自覺而明晰的文學地域意識。據學者考證,梅山文化的核心圈,發祥地新化縣和安化縣,它是居住在古稱梅山溪峒一帶的人民,世世代代所創造和傳承的一種地域的民族傳統文化,是瑤族和苗族等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互相影響和融合的產物。②這里有奇山秀水,盛產神話和巫儺,崇尚勤勞、勇悍、寧折不彎的精神,既尚文更重武。李健的小說在這梅山之地書寫著他熟悉的故鄉故事。梅山特色的人物、情節、細節、場景順手拈來,無不活靈活現。方言土語,社會風尚,民間傳說,以及該地區的獨特景色,鋪陳一地。
小說突出展現了梅山由于相對封閉而得以保存的獨特風情民景:炫目在陽光里的山地、山地里的樹和田園,濃香四溢的桃樹,肥碩得仿佛隨時撐破皮漫出水來的樹木、藤條,處處聽聞的麥巴鳥叫聲,燕子正在含泥筑巢的山洞。為了驗證景致出處的真實,李健還特意在博客上貼出了老家的照片,或是云海淹沒了梯田,或是漁舟唱晚,或是郁郁蔥蔥的腹地,或者水車勞作的聲息,高塔上的火燒云,已經打烊了的安寧的舊街巷,的確美翻了。作者又是一個寫景狀物的高手,《到陽光一邊去》描寫一頭叫“騷人”的牛犢:“騷人的毛發就像秋天沒墜的楓葉,紅潤光澤,看上去像一棵冬去春來復蘇的小草,青蔥結實。它是泊良老漢以前的一頭老母牛下的牛犢,整天蹦蹦跳跳,還經常獨自鉆出牛欄到外面瘋跑一會兒,蠻騷的。泊良老漢輕輕撫摸它毛茸茸的背脊,打心眼里喜愛,就叫它‘騷人’。”纏繞著梅山特色的地域風情,小說場景總是寫得非常細膩、從容,描寫收麥、種花生、趕麻雀、挑水、剖篾編篾、喂豬、打簸箕等各種農活,還有喊風、盜墓、文物做舊、玩陀螺、驅鬼、押寶等,對湘山區風景、房屋、甚至古墓,還有神秘色彩的神話傳說,也做了細致入微的描寫。這些東西水乳交融地有機生長在故事中,作者如數家珍。這些風俗民情描寫,使小說充溢著微苦而又溫馨的日常生活氣息,又為作品中人物營造出一種淡雅而朦朧的氛圍,賦予小說里人物一種特別的生命神性,使作品在平靜敘述中涌蕩著魅人的浪漫情趣。
和這山水相映襯的是生活在其間的,單純質樸而又堅強韌性的梅山人。小說《泥巴魚》描寫的同時喜歡一個男人的兩個女人一輩子的紛擾和理解。她們的紛擾緣于喜歡上同一個人,又同時緣于對土地的情感。土地和愛情都在訴說著她們的傳奇和苦澀,但兩位主人公的善良、執著、堅韌很好地沖淡了個人的悲苦困頓,讀者讀到一個光亮清幽,卻又深沉質樸的鄉村世界。不管外界天地在如何地變化折騰,李健筆下的這個世界正以梅山的節奏樸實而沉穩地進行著自己的生活。短篇《恩牛碑》思考的是人與牛之間的生命體恤與關懷。林四海是個老實人,他的心思全都花在田里土里,從不去琢磨人。種什么作物,什么作物適宜什么季節,犁是犁,鏵是鏵,沒浪費過土地光陰。一年下來,同樣的土地,總比人家多收三五擔谷物。就是這個老實人,養的牛比別人家的都要壯實。最終牛救了林四海的兒子,還報了主人的深恩。鄉土小說中,寫人與牛的故事不少,這篇小說繼承了這一敘事傳統。一頭牛的世界有多渺小,又有多遼闊?人與牛的溫情,實際上敘述的是人與那片土地之間相互關愛的深情。
美國小說家赫姆林·加蘭1894年寫就的理論著作《破碎的偶象》,強調“地方色彩”對文學至關重要,他認為:“顯然,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地方色彩又以比作一個人無窮地、不斷地涌現出來的魅力。我們首先對差別發生興趣,雷同從來不能吸引我們,不能象差別那樣有刺激性,那樣令人鼓舞。如果文學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學就要毀滅了。”③
梅山這塊神秘而具有靈性的土地養育了李健,梅山文化中獨特的地域風情氣氛,不僅作為題材進入現代鄉土小說,也對創作主體的思想、意識文化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就像素樸、單純、和諧的神性湘西孕育了沈從文,迷信、傾軋、缺少誠與愛的豀鎮孕育了彭家煌,交織著暴虐與優美的洞庭湖畔孕育了葉紫。小說中所展現的貧窮而幽美的自然環境,雄強浪漫、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以及小說人物強烈的生存意識和責任感,都源于這種文化氛圍的熏陶。湘楚文化不僅是小說生長的土壤,也是它的基本內容。李健對梅山文化的關注和闡釋都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在以現代理念反觀故土時,雖然他也看到了故土的落后、愚昧和動亂,但湘楚文化中那特有的自然神性和浪漫激情,對他還是有著無法抗拒的魅力。梅山地域文化是他這類小說中人物存在的生態,又浸潤于人物的潛意識中,流淌在人物的血管里面。李健對于梅山文化的表現是出乎其中、入乎其內。
西方作家格林說過,一個人在二十歲以前,他的寫作風格基本上已經形成了,此后一生的寫作無非是在回憶他二十歲之前的經驗和生活。④這話是有意思的。有時,一個人就是一片土地,一片土地也是一個人。換言之,梅山成就了李健,李健也成就了梅山。
二
地域是解讀李健小說的一個重要文化基礎,包含著作者對故鄉的深情,城鄉碰撞則是切入其鄉土文學的結構基點,顯現出他不僅是優秀的風景攝影師,也是一個理性客觀的思考者。在山水田園的抒情中,李健忠實地看到故鄉梅山,作為一個落后鄉村,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著現代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震蕩與沖擊。
城市裹挾中行走的鄉村是踉踉蹌蹌的。中篇《約定坳螞蟻》講誠實善良的青年椿寶入贅到田名正家,打算娶他那尚未成年的女孩香蓮為妻。香蓮原本喜歡椿寶,可是抵不住現代生活的誘惑而選擇了一個商業嗅覺異常靈敏的“新”青年,與之私奔并未婚先孕,但新青年并沒有迎娶香蓮的打算。幾番變故后,田名正郁郁而終,淳樸的香蓮已然麻木,唯有椿寶不時悲戚地吶喊。短篇《彈花匠》也是這樣一個痛苦的鄉村故事。小山村村婦銀花在城里打工,被工廠老板奸污,墮落,然后將城里的污濁帶回鄉村,與村里許多男人發生關系,進而與公公有了奸情,她丈夫彈花匠四聾子,苦苦經歷被人們譏諷羞辱和自己痛苦的隱忍之后,終于用一根繩子把銀花給勒殺了。兩個故事都在敘寫城市誘惑給梅山鄉里人帶來的巨大禍端。設想,如果椿寶、香蓮所生活的約定坳沒有受到現代風氣的傳染,那么他們很可能會在舊有的生活軌道上如常運行,平靜度過那貧窮但并不缺少快樂的一生。可是轉折時期的價值觀念變動,使得他們的人生充滿了風險,他們最終也被卷入到了風險當中。而彈花匠四聾子,如果沒有叫妻子上城打工,后面所有的屈辱血腥也不會發生。城市是污濁的、道德敗壞的,這是李健鄉村小說里“城市”意象首先出現的內涵。
并且,它們共有一個情節:無辜少女 (村婦)被城里人奸污。這是鄉村小說里常出現的情節范式。情節的反復出現意味著它是一個結構性隱喻,象征著城市對鄉村的脅迫和侵害,反過來也印證鄉村純凈傳統文明的窘迫前程。而面對鄉村的被侮辱被迫害,鄉下人在隱忍之后,選擇“殺妻”。“殺妻”也是一個隱喻,隱喻鄉村對城市的抵抗和決裂,隱喻鄉下人在頑強地維護偏僻山村的純潔和道德。但是,鄉下人真的能夠維護鄉村道德秩序的純潔,抗爭銀花所帶來的城市污濁之氣嗎?作者明顯是同情四聾子的,讓四聾子被診斷患有精神病而無罪釋放,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而已。
鄉村的落魄,根植于鄉村的愚昧。中篇《白鼠》女主人公陀螺十五歲時乳房開始發育,但脖子也開始大起來。村人聚到一處,免不了議論陀螺的大脖子——這是異象,意味著陀螺必定短壽,并且還克夫。沒有人愿意娶陀螺,她主動上門,和一個瘸腿的男人結了婚。陀螺在這里按部就班生活,和所有人一樣,割麥子,然后種紅薯,但很快在她家閣樓上她看見了一只白鼠。在梅山地域,見到白鼠是個更大的兇相,這讓陀螺膽戰心驚,惶惑不安。對于陀螺們的舊生活,作家這樣概括:“陀螺覺得自己就像那兒童手中的陀螺。略所不同的是,那陀螺需要人拉或用鞭抽打,才可以旋轉。而陀螺是自己抽打自己,不停地讓自己旋轉。”《霜天霜地》里華吉與秀姑的好事被樂山嫂撞到,被認為不吉利,直接導致兩人最后以死的方式告別人世。
還有閉塞和貧窮。《約定坳螞蟻》中香蓮的生活環境閉塞、孤獨,只有與酗酒的父親相依為命,艱難度日。生活賦予她的,既是精神上無法溝通的無盡隔膜,又是體力上的無盡勞作。“有時候,她真的想清閑地玩耍一天,不剁豬草煮潲,不清理豬欄衛生,看它還敢不敢翹尾巴。但她又擔心真的虧待了豬餓死了豬,怕遭父親的打罵,家里也損失不起,因此她只是想想,從不敢付諸行動。”
擺脫貧窮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是現代性的最基本涵義。世紀以來的現代化努力,特別是鄉土中國的現代化一直努力于改變落后的生產狀態和低級生活水平。但這個過程是痛苦的,物質的追逐伴隨著鄉村人品性的巨變,有些人亦然葆有著善良、厚道,一些人卻完全變質,道德滑坡,自私自利,無情無義,一些人踟躇在這兩者中間,取舍不定。在巨大的歷史車輪面前,窮困鄉村在整體狀態上是螞蟻群,草芥般被驅趕和碾壓。
當然,李健也并非總是悲觀,商品經濟大潮席卷下的鄉村是被動的,卻也有一種主動。現代城市文明誘惑著這片鄉土上的蕓蕓眾生,特別是渴望打破祖輩生存定律,期望走出不一樣人生軌跡的年輕一代。這些渴望走出者還并沒有太多鮮明的自覺意識,經歷更多掙扎與苦惱。不過,他們畢竟開創了與“留守者”不同的另一種人生圖景,在闖蕩江湖、開闊眼界中有可能被現代洪水沖撞開思想的閘門,喚起他們掌握自己的命運主動權的意識。像《白鼠》中的陀螺,就頂住壓力,大膽接受了城里來的肖清涼提出的大棚種植反季節蔬菜大棚等科技建議,一步步走出了貧困。小說安排白鼠和肖清涼在陀螺的生活中同時出現,隨著情節進展逐步呈現對比效應:白鼠在鄉民生活中制造驚悚和禁忌,肖清涼帶來的是科學致富,以及纏繞半生大脖子病的祛除。肖清涼在這里明顯有“啟蒙者”的意味。傳統愚昧和科技文明孰是孰非,一看自明。到故事結尾,陀螺在醫院里看到了做實驗用的小白鼠,心里踏實了,有了那種撐起內心春天的力量。陀螺的內心希望,寄寓著作者對鄉村崛起的期待。
崛起的期待中,李健觸及的是一個鄉村現代性的話題。所謂鄉村現代性,通俗講來,就是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化問題。一方面敘述鄉土世界的溫寧潔靜,像土地一樣的質樸深沉;另一方面,書寫傳統文明品質在現代化軌道上發生的劇烈震蕩和轉型,它悲哀地消逝或者主動地迎合,李健的作品透露出鄉村社會現代發展的進程,并努力落實在生命的解放上。
三
事實上,這是整個20世紀中國鄉土文學的主題話語。20世紀中國鄉土文學一直關注著鄉土文明的沖突與演進,無論是對于鄉土人生的批判審視,還是對于走出鄉村的向往渴盼,鄉土現代轉化問題困擾著鄉土作家,并形成他們敘事的內在驅動力。
李健作品里有著對故鄉對土地濃烈而樸質的深情。短篇《天上的鴨子》描寫小梅和鴨倌阿遠的青澀戀情,伴隨四野的鮮花、青碧的湖水、滿屋子里香氣氤氳的老鴨湯,還有那照在鴨柵上濕漉漉的月光,一起朦朧生長,神韻直追汪曾祺的《受戒》,難怪新近名列《中國小說名家巔峰力作》。如他自己訪談里所言:“我從泥巴中來,身上有著泥巴的氣味,這樣的泥巴這樣的氣味,是內涵了梅山特性的。每當我一捉著筆或是一敲鍵盤,我的眼里就看到了梅山的泥巴,看到了和梅山的泥巴有關的事物。土里生萬物,地內產黃金。就我所知很多事物源于土地,又歸于土地。”⑤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單純而美麗,有著未受現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而這個自然界的一切都有靈性,禽獸在做夢,草木能談吐,大自然的“神性”成為鄉土世界沉默的主宰。由此不難判斷,李健作品的主體氣質可大致歸屬于上述第三種,即田園牧歌的創作類型。他在新時期,承繼沈從文、汪曾祺京派小說風格,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記憶深處的梅山桃源。
同樣,李健的作品也呈現出田園小說特有的鄉愁。作者反復表達自己游離在城市與鄉村的邊緣地帶:“雖然我在城市生活這么多年了,按理說身上的土性也應改造得差不多了,但我的鄉音總是把我出賣,沒辦法,我無法改變自己。因此,在內心上,我把自己自覺地歸于鄉里人一類。無論我寫什么題材,作品中的人物總歸丟不掉梅山地方的氣息。好像外面那些奢華與我無關。”⑥僑寓于長沙城,卻不屬于其置身的都會,甚而把城市體驗為狹窄、墮落和陰沉的所在,毫不掩飾自己對城市文化的隔膜和厭惡。李健的心靈不無矛盾地漂泊在現代都市與古樸的鄉村之間,轉化為作品文字里無所不在的濃淡哀愁。
這是自然的。作為一名客觀理性的觀察者,他看到社會轉型中的梅山也跟著發展變化。在這個緩慢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人心開始分化,欲望空前膨脹,思想觀念和物質財富落差加大,社會到處充滿浮躁。田名正們“非常平衡的人生模式”受到破壞,是順理成章的事。工業時代的物質化與欲望化,使鄉村世界難以保留“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幸福的花朵》以一個淪落城市火車站乞討生存的殘疾兒汪四千的流浪經歷,沉重寫出鄉村的墮落,以及城市的殘忍。城市文明的現代化危機使其不能再作為一個自明的方向存在。在現代性沖擊中,李健秉持著民生立場,對被碾壓的鄉村是同情的、愛惜的、寵愛的。這種底層關懷如此悲憫深沉,即便是汪四千的爺爺、利用它乞討的吳婆婆,他也憐憫他們的苦楚,認為是生活困頓中的窘迫逼使他們不自覺地惡。但社會現實發展的復雜變化,使得鄉土中國的現代化目標變得越來越模糊、暖昧,留給李健們越來越多以及越來越深的悵惘。
深的悵惘中,李健的田園寫作成為一種家園寫作。換言之,李健系列鄉土小說傾心打造的純美故鄉只是精神意義上的,是現代人尋找精神家園的一個心理空間。如沈從文在他《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所言明:“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⑦沈從文意圖在他寧靜超脫的鄉土作品中寄寓“人性”的主題,李健沒有這么明晰的概念表達,但敘寫梅山地域風情之時,文字背后的確在追尋一種文化態度和生命方式。
這種文化態度和生命方式生長在被記憶過濾后的鄉村。他反復強調他的鄉土氣息,在此,“城市人”與“鄉下人”,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社會身份,而主要是一種文化身份。他對“鄉下人”的自認,其實是其對自我文化身份的選擇與辨識,同時也標志了他對宗法鄉村所象征的傳統文化的寬容和認同心態。正是出于這種內蘊復雜的文化認同與價值選擇,他在貶抑城市的同時,竭盡美化鄉村,挖掘并張揚鄉土中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所以,小說里的故鄉處處充滿了善意,充滿了單純的愿望和訴說。而且這個梅山還是與世隔絕的,地理上的交通閉塞,正得以保留它的傳統德性和理想,完全沒有現代社會中那種緊張、自我膨脹與心靈的焦慮。這些與都市文明截然相反的鄉村圖景,構筑出抵御現代工業文明進擊的夢中桃源。
如此桃源是浪漫的、非現實的、理想化的,作者未必不懂社會的苦痛,只不過他是以率真淳樸、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邊緣性異質性的鄉土文化敘述,顯示處于弱勢的邊緣文化中沉靜深遠的生命力量,從而內在地對所謂都市文明社會的種種弊端構成了超越性的批判。這是一種審美批判,或者說,一種審美現代性意識構建了李健等鄉土小說作家的內在創作精神。
什么叫審美現代性?這么說吧,倘使說社會的現代化是一個匆匆趕路的人,那么,審美現代性就好比是那個不斷提醒方向和路徑的人。⑧那個匆匆趕路的人,崇拜科學和理性,對于市場和行政體制趨之若鶩,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科技文明所帶來的種種高效便利。的確,以都市為中心的社會現代化過程,給人類帶來的好處不可計量。但另一方面,當整個社會都陶醉在高速度文明所帶來的財富、成功、榮耀時,現代生活的問題和陰影卻如影如隨,緊密相生。現代生活的弊端太多了。所以,在現代化的內部產生了一種審美現代性,它的任務就是,當一味高揚前進的旗幟,拼命追趕先進,大踏步拓荒之時,它卻停下來反思一下:前進總是對的嗎,匆匆忙忙趕路是否遺落了什么,現代化建設是否真正生產了幸福,我們是否有更好的社會路徑或人生方式的選擇?李健的田園小說系列大體就是這種審美現代性思潮中的一種以文學形象體系形式出現的反思。
反思,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尋找或創造一個對更好的社會向往的理想烏托邦,不斷反襯出現存世界的黑暗和不公正,激勵人們對美好的新世界的追求。正如阿多諾所說,它“所要完成的任務不是保存過去,而是拯救過去的希望”⑨。或者,最簡單的層面,在文字世界營造一個純美的人性空間,氤氳了一層溫寧的心靈光韻,為現代城市人提供越來越匱乏的心靈雞湯。作家曹乃謙讀了李健的小說后坦言:“因為怕消失,所以愈珍惜。”⑩是的,讀這樣的文字有時就是儀式,醫治現代人共同的鄉愁。
《幸福的花朵》中的汪四千,頻繁思念著那個給了他容身之地的廢煤窯,以及窯洞周圍匍匐的桔梗花,做出一個眺望的姿態。鄉村何去何從?在隱隱的迷惘中,作者李健不斷反思并調整自己的現代性思路,模糊眺望著鄉土中國的未來。
注釋:
①⑤⑥且東、李健:《望著梅山,我就找到了路標》,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3fc6b6f0102e21u.htm
②劉楚魁:《管窺梅山文化對曾國藩思想性格的影響》,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40616047_0_ 1.html
③赫姆林·加蘭:《美國作家論文學》,三聯書店 1984年版。
④丁帆:《作為世界性母題的“鄉土小說”》,《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⑦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3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⑧周憲:《審美現代性的四個層面》,《文學評論》2002年第5期。
⑨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
⑩曹乃謙:《三瓣嘴》序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3BWW06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工業大學包裝設計藝術學院)
本欄目責任編輯 曹慶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