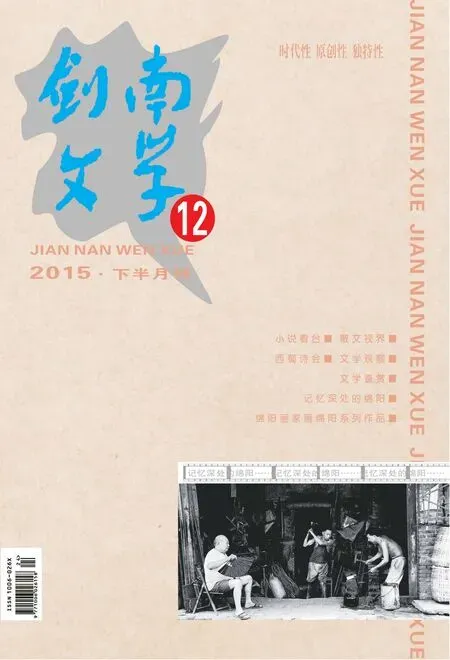黑人上帝:從《向蒼天呼吁》看美國黑人主體訴求策略
■李 秋
黑人上帝:從《向蒼天呼吁》看美國黑人主體訴求策略
■李 秋
本人通過對小說中基督教教會主題的梳理,探討了黑人在追尋身份認同的主體訴求,對白人主流文化之基督文化的內化成為黑人融入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必經之路,黑人主體如何構建其自身宗教文化又不迷失黑人民族性將是本文的主要話題。
《向蒼天呼吁》是美國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成名作,也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筆者認為美國黑人作家筆下所展現的黑人宗教是其構建黑人民族性,踏上尋根之旅的又一大主題。在《向蒼天呼吁》中,小說人物角色主要在場空間即是教堂,主人公約翰的父親、母親、姑姑成為十九世紀中后期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黑人教會發展的主要敘述者,和約翰一并敘述了黑人從廢奴運動到重建時期的黑人教會對黑人社區的影響。通過現時視角的重構,即 “當事人對過去經歷的敘述,不僅可以獲得先前的經歷,同時也可以獲得他們對那段經歷的理解”,揭開了美國黑人在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信仰崩塌和重建的需要。
一、黑人教會之承襲
早期的黑人皈依基督教源自白人奴隸制政治統治的需要,白人希望通過基督教律法規訓黑人奴隸的反抗情緒,在白人基督教的規訓下,黑人的膚色作為奴隸后代的標記,讓黑人臣服于白人之下,種族歧視在《圣經》中可以找到原型,以原罪論壓抑黑人人性,為奴隸制找到精神支撐,同時通過天堂許諾,安撫黑人的奴隸身份。受制于奴隸制的黑人,將基督教會作為宣泄情感和逃避現實的組織,弗雷澤指出,黑人教會是“存在于可怕白人世界中的避難所,”南北戰爭前黑人教會常常以隱秘的方式進行。黑奴解放運動后,黑人集會禁令取消,黑人與白人教會完全分離,大規模的建立了自己的教會,杰出的黑人領袖、社會學家W·E·B杜波依斯指出,“一旦黑人完全控制教會,本地黑人教會便會成為他們成員的社會生活中心,成為交流信息的主要媒介,甚至娛樂活動的組織者。”
在小說中,教堂是所有主要人物的在場空間,通過教徒的禱告和懺悔,在基督語境下還原美國黑人教會的記憶。故事圍繞一個禮拜日展開,約翰所居住的哈萊姆社區,有許多這樣的教堂,做禮拜是一個黑人家庭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內容,從開頭就可以看到,約翰“最早的記憶--多少也是他唯一的記憶--是禮拜天早上的忙碌和光明。”(鮑德溫,1984::1)黑人教會規訓著黑人社會生活,以“圣潔”的名義把黑人群體分裂為兩大陣營---以格蘭姆斯一家為代表的黑人基督信徒和通向教堂街區兩旁的黑人罪人形成鮮明的對比:罪人們衣衫襤褸,沉迷于肉體的享受—縱欲、酗酒、斗毆,而格蘭姆斯家卻正正經經,打扮光鮮,有條不紊的參加主日學校的各類活動—祈禱、歌唱、狂舞。黑人教會建立起以加布里埃爾為代表的權力話語,規訓的主體卻是黑人年輕一代和女性,在其倡導的“圣潔”生活下,伊萊沙和埃拉·梅青春朦朧的愛戀被斥為“罪孽”;剛剛進入十四歲的約翰在父親厭惡的眼神中,惶恐地“懺悔”;約翰的姑姑弗洛倫斯因其挑戰對“上帝”信仰,被母親和弟弟視為“異類”,約翰的母親伊麗莎白由于約翰的私生子身份在丈夫權威面前“失語”,而成年黑人男性基督徒卻是黑人家庭與教會的主宰,尤其是黑人牧師,他們與教民廣泛頻繁的接觸,使得“有色人不僅從他們所屬的教會布道壇那里獲取靈性的信息,而且還尋求特別的信息,”因此,黑人牧師身份在黑人社區中舉足輕重,不僅影響黑人精神世界,更是黑人追求政治自由,擺脫種族主義的重要領袖。弗雷澤也認為黑人教會具有政治經濟功能。但是黑人基督教經歷了白人絕對權力的洗腦,始終在模仿白人基督教會,加布里埃爾兼有家長和牧師身份,這使他同時構建了家庭權力,即對家人的隨意打罵,并以其標榜的“圣潔生活”規訓反對的聲音,而加布里埃爾的生命里并不是充滿了“圣潔”——在其個人記憶中他年輕時酗酒尋歡,“贖罪”后他通奸騙婚,家庭中他對約翰及其母親暴粗等等。于是黑人們在“天堂”的謊言中尋找慰藉,在“圣潔”的幌子下建立家長制,并以“罪人”的稱呼,規訓有質疑者,此外因為仇視,自動將黑人團體隔離于白人群體之外,甚至還在黑人群體內,建立隔離—基督徒與“罪人”。本故事中三個重要的場景,約翰的家、從家去向教堂的街區,火浸禮教堂,構成了隔離的區域。黑人群體對自身的分化,這樣的“選民”模式無疑體現了黑人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承襲。
分化后所謂的黑人主流群體,也并未對黑人生活做出很大的改善,面對白人的種族歧視,教會依然宣傳來世,堅持遷就和適應,因為“《圣經》是嚴厲的,圣潔之路是艱難的。”(鮑德溫,1984:6)因此在教會的權力話語下,黑人受白人奴役的歷史得以再現,這種再現,不僅僅再現廢奴運動后黑人在白人社會未能得到認同,還重構了黑人女性與年輕一代被奴役的歷史,黑人教會在白人基督話語下無法發揮治愈創傷的功能,反而進一步強化白人基督教文化規訓。正如對黛博拉(加布里埃爾的第一任妻子)受到白人凌辱后,被隔離在黑人群體之外,“在人們眼里,那天晚上使她失去了作為一個女人的權利。沒有一個男人會尊重和接近她,因為她對自己、對所有的男女黑人都是一種活著的恥辱。”(鮑德溫,1984:61)黑人對白人文化的承襲在此得到體現,黑人教會在標榜“圣潔”生活的同時,并未對黑人的不幸帶去慰藉,反而分化黑人群體,黛博拉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但在福音布道會時期,彼得長老對黛博拉的不幸卻加以嘲諷,“不錯,這里是有一位圣潔的女人!白皮膚男人的乳液塞滿了她的肚子,至今仍在里面發出這么大的酸味,以致她現在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愿意讓她嘗嘗更加豐富新鮮的東西的黑人。”(鮑德溫,1984:96),由此可見,黑人教會在改善黑人種族處境上的無作為和誤導。
二、向黑人上帝呼吁
造成黑人教會如此現狀卻是與二十世紀初期自由黑人在白人既定的社會秩序中找不到位置的狀態密切相關,教會和教會模式下的家庭給他們帶去自治體驗,杜波依斯就曾指出,教會是“黑人在北美第一次完全控制的機構”很顯然,這種自治體驗并未能使黑人走出白人文化的影響。盡很早放棄神職,鮑德溫一生沒有走出對黑人宗教的思考,Lynch指出,鮑德溫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反映出其對上帝身份的疑問。他另一部作品 《下一次烈火》中也明確提到,上帝是白人上帝,而黑人永遠不可能在他面前得到救贖。那么由加布里埃爾為代表的黑人教會也不可能為廢奴運動后的自由黑人帶去精神引導,反而承襲白人基督教繼續在精神上奴役黑人,其倡導的“圣潔之路”實質是想通過基督教“選民”模式分化黑人社區,以教會構建權力話語,而黑人女性和年輕一代卻處于這一模式的底層。
鮑德溫在《向蒼天呼吁》中暗示黑人的心靈去殖民化要從根本上推翻白人上帝,構建黑人上帝。在故事中,鮑德溫展示的黑人教會為這種構建能力提供了依據。比如他大篇幅的展示了黑人教會的祈禱畫面,與白人教會默默祈禱不同,黑人教會發展了原創的宗教靈歌(Spiritual),源自非洲黑人音樂,以鈴鼓、歌唱、舞蹈、眼淚、喊叫等表現形式充分表達了黑人感情流溢。宗教靈歌的發展證明黑人群體有能力構建自身文化,繼承和發揚非洲文化傳統,同時加上黑人群體本身對白人基督文化存在質疑,那么構建黑人上帝也就有了一種可能。而黑人神學體系在黑人神職人員的推動下也有所發展,馬兒庫賽·戈維(Garvey,Marcus)在20世紀20年代組織了非洲正統教會,并提出了黑人上帝,黑人耶穌,黑人圣母和黑人天使。黑人神學家柯恩也明確指出,“在被壓迫者的經歷形成了上帝的體驗這一點上,上帝是同被壓迫者一致的,否則他就是種族主義上帝。”
但是鮑德溫意識到,黑人種族文化不可能割裂所有的白人文化影響,那么只有當上帝以黑色展示出來,黑人用理性運用宗教,消除白人文化的負面影響,才能構建解決種族困境的空間權力話語。
(西華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本文受到西華師范大學校級項目資助,項目編號:11A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