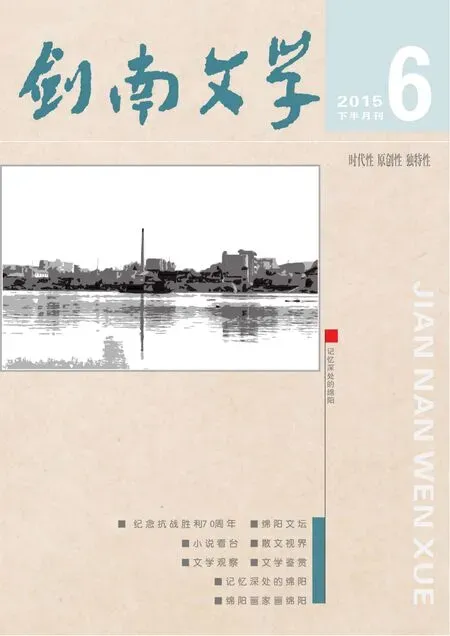影片《秋喜》的符號分析
■任穎瑩
影片《秋喜》的符號分析
■任穎瑩
《秋喜》作為一部諜戰片,導演并沒有按照傳統的范型來創作,而是采取了普通人的感知方式、敘事心態和價值眼光,精彩的實現了對個體生命的人文關懷。文章通過分析影片中的符號含義,使我們更加明確的了解影片的含義。
《秋喜》的故事是發生在建國后,廣州和平解放前,國共兩黨的最后較量。同為黃埔軍校校友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夏惠民和潛伏在特務機構里的地下黨晏海清,從語言到心靈的生死較量。導演采用了較為常規的電影敘事手法,將重點放在了對人物的塑造上,所以這部影片不再僅僅是一部簡單粗暴的諜戰大片,而是已經上升到人性高度。
影片一開始導演將我們帶入了一個情節上的誤區認為秋喜這個人物可能會是影片中的重要角色,但是隨著影片的發展我們發現秋喜并沒有介入整個故事情節,她與主要情節的疏離狀況,讓觀眾認為導演在敘事上的不嚴謹。其實秋喜這個人物的塑造是整個影片的靈魂,導演將自己想要傾注的思想全部通過這樣一個人物來體現,所以秋喜的設置不再是一個人而是導演思想上升到物化的一種表現,有極深的符號意義。
導演將秋喜設計成經常光腳走路的疍家女,這一形象是外在隱喻同時也是秋喜身份的認定。在賬房先生被殺那場戲后,晏海清惱怒自己的失誤差點毀掉一切計劃,回到家后他將臥室內的東西砸爛發泄,這時候秋喜光腳的出場徹底激怒了晏海清,他朝秋喜怒吼:“整天神神秘秘像個密探,我告訴你,我這輩子最恨的就是密探”。這句臺詞像我們揭露了“秋喜”作為群體的符號意義,即潛伏者。而秋喜的鞋是作為潛伏者向共產黨確認自己身份時的一種聯系,只有穿上鞋“秋喜”才可以直接的沒有任何隱藏的讓領導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行動。所以在秋喜死后,雨中秋喜的尸體是沒有穿鞋的,這是對于“秋喜”身份的揭示。鏡頭輕輕搖過,晏海清拿著秋喜的鞋靜靜地坐在臺階前,悲傷的氛圍象征著共產黨對于失去潛伏者的無能為力,只能憑借一雙鞋,一種無聲的身份驗證來緬懷她。
秋喜裸洗,這出戲可以說是這部影片的轉折點,如果說影片前半部分還屬于諜戰片的范疇那么從這里開始影片逐漸上升到了對人性的思考。在這出戲出現之前有一段對于它的鋪墊,夏惠民找到了共產黨的據點,而晏海清也整日為這事擔心,秋喜的獻身被晏海清拒絕。我們之前分析到秋喜代表的是潛伏者,那么在這里我們可以將這出戲理解成是對于潛伏者的考驗。在這之前晏海清的身份已經被夏惠民識別,所以“秋喜”在這個時候的出現是沒有任何遮掩的,而風雨對于秋喜身體的直接的沖刷所隱喻的是外界尤其是夏惠民之輩對于潛伏者人性的沖擊。
影片中多次有鴿子出現,這里的符號意義是,鴿子等同于秋喜,在現實生活中鴿子被人們冠以和平的象征,而在古代它則是人們的信使,作為雙方秘密傳遞信息的橋梁它同時也帶有密探的性質。而秋喜作為一個女孩身上所散發出來的純潔和鴿子一身潔白的羽毛所隱含的純潔不謀而合。
其實夏惠民對于晏海清的身份早已識破。在夏惠民審問九爺的時候還記得九爺是怎么回答夏惠民的嗎,“不夠氣,要補,一定要補”。這里隱藏著晏海清身份被識破的信息,“不夠氣(齊),要補(捕),一定要補(捕)”。晏海清原想要賬房先生去給陶區長送信,結果賬房先生先開槍打死了自己的人,最終導致了夏惠民識破晏海清的身份。而這個猜想在夏惠民安排自己的手下跟蹤晏海清時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驗證。
陶區長和晏海清在河邊談話一段中每句話,每個動作都被導演冠上了符號的象征意義。當晏海清得知自己在新中國建立后還要繼續擔任潛伏工作的消息后,舉棋不定,猶豫不決,很自然的摔碎了瓷碗,表現出他當時內心的掙扎。他先后兩次向湖面扔碎碗片,第一次沒有成功,他嘗試了第二次,碗片終于順利的到達對岸。導演將晏海清比作是一個小小的碗片,而河流及其兩岸則象征著大陸和臺灣,是跟隨大軍去往臺灣還是繼續留下完成大業,對于晏海清來說這是一次困難的抉擇,最終碗片的順利過岸也就潛在的告訴了我們晏海清的決定和他堅定的信念,繼續潛伏。
如果說秋喜是晏海清身邊的一個符號,那么惠紅蓮就是夏惠民身邊的一個強烈的符號。影片中的惠紅蓮僅僅是生活在最底層的戲子,她沒有任何的社會地位更沒有能力和這個社會抵抗,所以只能蜷縮在強權之下,就像是被蹂躪的人民,睜眼不能反抗,閉眼不能享受,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所以我們不難猜出惠紅蓮所隱喻的是在國民黨控制下的貧困人民。
在1949年,國民黨節節潰敗,對于無法挽回的頹勢很不甘心,它極力想要再次實現對廣州的全民控制,這種在政治上極度的占有欲,更加激起了百姓的不滿。夏惠民作為國民黨的工作人員,導演將這個角色隱喻為即將失勢的國民黨,而他對于惠紅蓮所表現的占有欲可以看成是國民黨對于人民的控制。
在保衛華南動員大會上晏海清正在為建國高興的跳舞,而夏惠民和惠紅蓮卻在極盡的歡愛。夏惠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于惠紅蓮的占有欲,也是國民黨對于民眾的控制欲。在影片的最后,導演為了突顯“惠紅蓮”這個角色的意義,安排了她在電臺唱喪曲的一幕,不僅表現了惠紅蓮作為個體心理的變化,更是表達了,在國民黨要垮臺之際,惠紅蓮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思想的一種轉變,即深受壓迫的百姓對于即將倒臺政權的痛惡。惠紅蓮主動向夏惠民提出不去臺灣,她知道只有這個地方才適合自己,離開了廣州離開了粵劇她沒有生存的地方,所以她說:“我不怕,改朝換代戲總是要聽的”。在惠紅蓮的最后一場演出前,她畫著戲妝對著鏡子說:“無論發生什么,我們唱戲的只活在戲里”。這是惠紅蓮的內心獨白也是民眾的真正想法,不管誰執政,我們都要守著家鄉過自己的生活。
影片最后夏惠民開槍打死了睡夢中的惠紅蓮,這是“夏惠民”內心獨占欲的體現。既然“你”不再屬于“我”,那么“我”要把“你”毀掉,讓別人也得不到。
影片中塑造的晏海清這個人物不再像以往諜戰片中的潛伏者那樣游刃有余,能夠運用自己的智慧和精細巧妙地與敵人周旋,圓滿地完成一個又一個任務。在這部影片里,晏海清從一開始就受到夏惠民的懷疑,執行任務時顯得那么的拙劣,遇到危險時不夠鎮定、不夠臨危不懼,甚至用吸食鴉片來減輕內心的痛苦。這些都可以看出晏海清并不是一個合格的潛伏者,但他也許是最真實的,潛伏者不都是傳奇,也不都是英雄。他們痛苦地、壓抑地活在敵人中間,當組織上讓他去臺灣時,他沒有計較,而是堅決地服從,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就是為了換取更大的勝利。支撐他的就是對革命的信仰,對黨的信仰。最后,當秋喜一身紅衣穿行在人群中的時候,晏海清的信仰實現了,這是他用生命換取的勝利。
影片對于夏惠民這個人物的表現,已不能簡單的把他界定為一個壞人了。對于晏海清他是上司也是兄長,在深夜廣州的路上,兩個喝的大醉的男人,唱著雄壯的國際歌,除去那個時代背景,這兩個人顯然是一對要好的知己。
在這部影片中晏海清的設置是一個 “純潔”的人,所謂純潔,是對美好未來的堅信,可是在那個殘酷的年代,光有信念是不夠的,所以在他遭受的折磨的同時,也他失去了自己要保護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而夏惠民一個瘋狂的失去信仰,殺人如麻的人,曾經他也許“純潔”過,也有過自己的信仰,但是現在他只是個惡魔。是什么讓他變成這個樣子?在影片的中間部分有一場戲,秋喜想讓晏海清幫她改名字,晏海清說了一句:“不是名字不好,是世道不好”。這個殘酷的社會讓一些人自甘墮落,也讓一些人泯滅人性,亂了心智。
撤退的命令下來后,夏惠民去找晏海清,他感嘆到:“大江東去,覆水難收。”這不僅僅是對時局的無奈,更多是感嘆自己對于大局的無能為力。夏惠民說,如果自己是共黨,他也可以有一番作為,我們不可否認夏惠民的能力,但是對于這樣一個選錯信仰的人來說,純潔早已離他而去。當他抓著純潔的秋喜對晏海清說:“我知道你為什么喜歡她,因為她純潔,你也純潔,我還純潔嗎?”晏海清回答到:“你是不是魔鬼我不知道,但是按照寧殺一千,不錯過一個的說法你轉頭就能把你身邊的這個人給殺了,她叫秋喜。”晏海清的回答已經告訴夏惠民了,你隨時會把一些無關的人殺掉,純潔早已不屬于你,你就是個魔鬼。當自己堅定的信仰被推翻的時候,其內心的惶恐,是無法隱藏的,就像是夏惠民一樣只能坐在臺階上歇斯底里的發泄,用“殘忍”來包裝自己,自欺欺人來支撐自己,表面風光下的絕望、痛苦更讓人同情。痛哭后的夏惠民并沒有試著找回自己的純潔而是像以往一樣繼續當著惡魔,因為丟失的信仰已經讓他沒有回頭路可走。
夏惠民和晏海清去看惠紅蓮的戲,夏惠民指著臺上的惠紅蓮說:“話說亂世之秋誰還有心思看戲,我看我們還是換另一出戲吧。”說完這句話后已經奄奄一息的陶區長被掉在屋頂上。這對于晏海清是殘忍的看著自己的同事正遭受著折磨,對他是巨大的打擊。其實陶區長也只是夏惠民想要讓晏海清變成惡魔的工具,最終他失敗了。膽小的晏海清沒有勇氣殺死自己的同伴,這讓夏惠民倍感失望,所以最后夏惠民打死了陶區長,這讓晏海清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即使這樣,夏惠民依然沒有停手,最終他設計晏海清親手打死了秋喜。夏惠民毀滅了晏海清的信仰,看著晏海清閃爍的眼神高興的說:“眼神里有了內容,我喜歡”。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從一個有著信仰純潔的人變成惡魔時候的樣子,對于晏海清的毀滅讓他感到興奮。在他走后又轉過身來說:“其實我也很純潔”。他是想告訴晏海清咱倆現在是一樣的,你親手殺死了自己純潔的信仰,而我的早已離去。
在片尾,晏海清質問夏惠民你為什么要殺死秋喜,夏惠民說:“不,你說錯了不是我殺死了秋喜,是你殺死了自己的純潔而已”。夏惠民試圖改變晏海清,但是他失敗了,晏海清義正言辭的回答他:“純潔是不會死的,他只會離你而去”。人性純潔的信仰是不會被人們扼殺掉的,她只是會暫時離開,等有一天你還可以將她喚醒。夏惠民也許純潔過但他現在只是個魔鬼,純潔對于他來說是死掉的,所以晏海清必須要殺掉他。
而夏惠民的回答更有趣:“那你必須死,別以為你是我的鏡子”。他也許有過對于現在身份的搖擺,但隨著自己不斷得到的滿足感,他開始迷戀現在的自己并從中或得了權力的快感。他也一直懷抱著關于信仰的想象而頗為自得,而晏海清對他理想身份的否定仿佛是一面鏡子能夠看穿夏惠民的內心,這讓夏惠民無法接受。夏惠民的死從宏觀的意義來說象征著國民黨終結了在內地的統治,而晏海清也毅然決然踏上了去往臺灣的革命之路,這個時候的他已經沒有了膽怯,只是對自己信仰的堅定。
最后影片在晏海清身負重傷艱難的走在騎樓下和秋喜走在勝利的隊伍中的兩組畫面之間來回切換。秋喜身著紅衣徜徉在夾道歡迎的人群旁,笑意盈面,那是潛伏者們由衷的欣喜。純潔稚嫩的秋喜,同純潔、嶄新、鮮嫩的新中國徹底融合。在這一幕中《秋喜》這部電影的名字也有了另一層含義,寓意新中國。
導演孫周在主旋律電影中小心翼翼的講述著自己的故事,他將諜戰電影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雖然這部電影也有不足,但是這樣的嘗試已經給中國的諜戰電影開辟出了一條新道路。我們希望在以后的諜戰電影中看的不再僅僅是組織統籌下的傳奇和英雄,而是個人人性光輝的散發。
(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