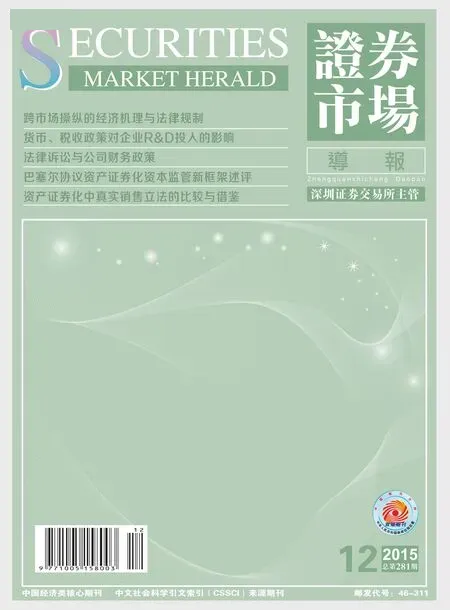我國上市公司并購議價能力的量化研究
趙瑋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引言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上市公司的并購事件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并購次數在2003~2013年間增長了約2倍多,從2003年的298例增長至2013年的699例,從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增長更為迅速1。可見,并購活動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由于并購在深化國有體制改革,改善資源配置,提升企業經營效率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實現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擴張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國政府非常重視并購活動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特別是在我國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當下,并購活動顯得愈發重要。
縱觀我國企業并購活動,雖然影響并購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但并購成交價格的確定無疑是并購活動的關鍵所在。并購成交價格體現了并購雙方相關利益角逐,它既是并購成功與否的關鍵,又影響著并購后企業經營業績。因而并購雙方都希望制定一個使自己利益達到最大的價格。并購雙方之間成交價格的確定,最重要的是雙方的談判,而買賣雙方的談判能力又離不開所掌握的信息。目前,我國大多并購事件表明成交價格對并購成敗至關重要,而并購雙方的討價還價能力則是獲得合理成交價格的關鍵所在,因此,有必要對企業并購價格的議價能力進行深一步的研究。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圍繞并購價格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相關內容大致可歸結如下:第一,影響并購價格的因素。現有文獻或是從并購雙方和市場因素來考察該問題,主要強調了目標公司的規模、企業性質、戰略目標、交易地位等因素的重要性(Robins和Wiersema,1995;Shelton,1988)[13][14];或是從財務狀況和交易特征視角,研究了目標方的抵制或是支持策略、目標方的行業特征、目標方的經營效率和競爭力、交易的支付方式以及交易比率對并購價格的影響(Gondhalekar et al.,2004;Laamanen,2007;Raman和Tamayo,2013;范從來和袁靜,2002;劉笑萍等,2009)[5][8][12][17][22];或是研究了管理層和公司治理對并購價格的影響,如目標公司的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管理層持股比率、高管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和認知特征等因素(Moeller,2005;馮根福和吳林江,2001;李善民和朱滔,2005)[9][18][19]。也有部分學者從其他并購參與者的視角展開分析,如財務顧問數量與質量、政府參與、連鎖董事的存在(Chahine和Ismail,2009;李增泉等,2005;潘洪波和余明桂,2011;陳仕華和盧昌崇,2013)[2][20][24][16]。第二,關于并購溢價的研究。國內外關于并購溢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購動因與并購溢價關系以及并購溢價的影響因素兩個方面。Slusky和Caves(1991)[15]認為并購溢價的部分動因可由代理動機因素與財務協同效應解釋。Hayward和Hambrick(1997)[6]指出CEO的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高度相關。國內學者朱寶憲和朱朝華(2003)[25]從并購雙方公司的財務指標對影響并購溢價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
可見,國內關于上市公司并購價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價、溢價以及影響因素等方面,而有關我國上市公司并購議價方面的研究幾不可見。我國上市公司并購議價能力如何?能否通過討價還價能力而為自己爭取到較大剩余?對這一問題,本文給于相應研究。
理論分析與建模
在并購交易市場中,主并購方企業與被并購方企業都擁有對方所沒有的私人信息,并購雙方具有一定的信息不對稱性。并購雙方通過討價還價達成最終的并購交易價格,顯然雙方均有一個自己可承受的價格底線,即主并購方企業具有一個它能夠接受的最高價格;被并購方存在一個它能接受的最低價格,而這個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之差定義為“剩余”2。顯然,最終并購交易價格依賴于雙方利用信息進行博弈的結果,而剩余的分配主要取決于并購雙方的討價還價能力。本文對并購雙方的議價能力進行了測度,主要方法為Kumbhakar et al.(2009)[7]提出的雙邊隨機邊界模型。
P—代表并購方企業所能接受的最高價格,P—為被并購方企業所能接受的最低價格,則并購雙方經過討價還價形成的成交價格P應當滿足如下條件:P—≤P≤P—,借鑒Polachek and Yoon(1987,1996)[10][11]與Gaynor and Polachek(1994)[4]的研究,假設成交價格P滿足下式:

每筆交易中,影響并購雙方討價還價能力的因素不盡相同,但當交易次數非常多時,我們可以估計出并購雙方的底線價格P—和P—,以及給定交易個體基本特征x下的“公允價格”:f(x)=E(τ|x),并且其滿足條件:P—≤f(x)≤P—。需要說明的是式(1)是一個典型的價格配比問題,而Acemoglu和Shimer(2000)[1]以及Flinn(2006)[3]研究了這種有效的配比價格問題,均認為這種價格是已知的或客觀存在并服從某種分布。由于并購活動的復雜性導致找到一個先驗性的“公平合理”的價格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事先假設公允價格不可知,但卻客觀存在,并且該價格由并購交易的特征所決定。因此確定好了影響并購交易特征因素后,利用雙邊隨機邊界模型估計出這些因素前面系數,則此價格便可以計算出來。被并購方企業會竭盡全力提高成交價格,而主并購方公司則希望降低成交價格。以公允價格為基準,式(1)可以分解為:

顯然式(2)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給定并購交易特征x下的公允價格f(x);第二部分λ[P—-f(x)]表示被并購方企業憑借自己的議價能力所獲得的剩余;第三部分(1-λ)[f(x)-P—]表示主并購方公司通過議價能力所獲得的剩余,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之和為總剩余,也就是前面我們定義的“剩余”。由于每筆并購其交易價格都圍繞公允價格上下波動,所以式(2)中議價能力因素可以寫成如下形式:

式(3)是一個典型的雙邊隨機前沿模型,盧洪友等(2011)[23]和劉海洋(2013)[21]等學者均采用該方法估計了不同市場中的議價能力。其中,f(x)=x'iβ,β是待估系數向量,xi為樣本個體特征向量,由用來刻畫單筆并購交易特征的變量構成。干擾項wi為式(2)中的第二部分,即被并購方企業所獲得的剩余,并且wi≥0。而干擾項ui對應著(2)中的第三部分,表示主并購方公司所獲剩余,并且ui≥0。由上述分析可知干擾項ui和wi都具有單邊分布的特征,因此假設二者均服從指數分布,即:ui~exp(σu,σ2u),wi~exp(σw,σ2w)。而vi是一般意義上的隨機干擾項,我們設其服從正態分布vi~N(0,σ2v)。式(3)利用最大似然估計法來估計,根據上述假定可推導出復合干擾項?i的概率密度函數如下:

其中,φ(·)和Φ(·)分別為標準正態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數和累積分布函數,其它參數的設定如下:

由此,我們可以得第i個觀測值所對應的對數似然函數,表示如下:

其中,θ={β,σv , σu , σw}為待估參數,通過上式最大化可以求得所有待估參數。得到參數之后便可以推導出并購成交價格形成過程中的ui和wi的條件分布,從而得出ui和wi的條件期望如下:

式(6)的估計結果代表了第i起并購事件的主并購方上市公司通過議價能力所獲得的剩余,而式(7)的估計結果則表示第i起并購事件的被并購方企業通過討價還價能力所獲得的剩余。可見我們無需事前假設并購雙方的議價能力,完全由模型的估計結果給定。而并購雙方議價能力導致成交價格與公允價格的偏離程度則由式(6)與式(7)之差獲得,也就是凈剩余。凈剩余NS可表示為:

研究數據與變量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跨國并購交易為研究對象,研究需要的跨國并購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子數據庫“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樣本篩選過程如下:(1)刪除包含未披露數據的樣本;(2)刪除樣本區間內被ST或PT的公司;(3)刪除并購交易總價低于1000元或者金額缺失的樣本;(4)若在某一會計年度,某一主并購方企業發生多于一次并購,則僅本年度交易規模最大并購事件入選樣本;(5)同一家主并購方上市公司在不同年度發生的并購交易,則分別作為不同的樣本計入相應年度的樣本;(6)多家上市公司聯合進行的并購,則分別作為兩個數據計入樣本。經過篩選后,共得到5119個觀測樣本。本文計量軟件主要是STATA11.0。
二、個體特征變量的確定
為了衡量公允價格,必須要選取并購交易個體特征變量。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擇如下并購交易特征變量,這些變量對應式(3)中的向量xi:(1)List,被并購方企業上市虛擬變量,如果目標公司為上市公司則List等于1,否則等于0。(2)Abroad,海外并購虛擬變量,若被并購方企業所屬國家不是中國,則Abroad等于1,否則等于0。(3)Assetm,資產收購虛擬變量,如果并購重組類型為資產收購時Assetm等于1,否則等于0。(4)Btype,標的類型虛擬變量,若標的類型為資產標的時Btype等于1,否則等于0。(5)Major,重大資產重組虛擬變量,若交易事件構成重大資產重組則Major等于1,否則等于0。(6)Cash,現金支付虛擬變量,如果并購事件的支付方式為現金支付則Cash等于1,否則等于0。(7)Stock,股票支付虛擬變量,如果支付方式為股票支付則Stock等于1,否則等于0。將上述7個變量帶入式(3)便得到雙邊隨機邊界模型如下:

表1 所涉及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本文所涉及變量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并購成交價格的對數lnValue的最大值為26.11,而最小值僅為8.359,標準差為1.887,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并購成交價格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變量List、Abroad的均值分別為0.0260與0.0520,表明在所用并購交易中,僅有2.6%的并購交易其被并購方為上市公司,存在5.2%的并購為跨國并購,可見我國上市公司大多傾向于兼并非上市企業,而且國內并購數量遠遠大于跨國并購數量。此外,變量Assetm、Btype、Major、Cash以及Stock的均值分別為0.965、0.352、0.0400、0.900和0.0580,表明樣本并購事件中,96.5%的并購為資產收購,約35%的并購事件其標的類型為資產標的、4%的并購為重大資產重組以及90%的并購其支付方式為現金支付,股票支付僅占了5.8%。
實證結果及分析
本節在公允價格因素分析的基礎上,通過估計雙邊隨機邊界模型式(9)和總方差分解,測度了并購雙方在成交價格形成過程中的議價能力以及雙方所獲得的剩余。首先,給出全樣本情況下的回歸結果,然后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在國內并購交易與跨國并購交易中議價能力的差異。

表2 雙邊隨機邊界模型估計結果(全樣本)
一、雙邊隨機邊界模型的估計:全樣本
1.公允價格的影響因素
利用包含5119例并購交易的全樣本數據,對式(9)進行估計,結果呈現于表2中。其中,模型1是利用OLS進行估計的結果,模型2至模型5為均是雙邊隨機邊界模型的結果。模型3考慮了年度效應,模型4考慮了行業效應,而模型5同時控制了年度和行業變量。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中,方差膨脹因子均值為1.59,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調整后的擬合度接近2,表明本文所選的解釋變量的擬合效果較好。與其他模型相比,模型5的LL值與LR值均為最大值,因此,隨后的方差分解和效應分析都根據模型5的估計結果展開。
由模型5的估計結果可知,變量List、Abroad、Assetm、Btype、Major和Stock均在5%或1%的顯著水平與價格顯著正相關。被并購方企業為上市公司、跨國并購、資產收購、資產標的、重大資產并購重組以及股票支付的并購交易,更有可能面臨著一個較高的成交價格。而現金支付虛擬變量的系數是負的并且與被解釋變量高度相關,表明現金支付的并購交易更有可能面臨一個較低的成交價格。
2.方差分解:并購雙方的議價能力對成交價格的影響程度
表3說明了并購雙方議價能力對成交價格形成的影響情況。由表3可知,主并購方企業議價能力對于成交價格的負向效應達到0.9579,被并購方企業討價還價能力對于成交價格的正向效應為0.7623,因此二者的凈效果為E(u-w)=σu-σw=0.1956,顯然,并購雙方議價能力的綜合效應為正值,表明主并購方企業比被并購方企業的議價能力更強。整體而言,雙方的討價還價能力會導致一個相對于公允價格更低的價格。從方差分解結果看,表明整體議價能力對成交價格的總影響中,主并購方公司的議價能力在議價能力的總影響中高達61.23%;而被并購方企業對成交價格的貢獻為38.77%。此外,lnValue無法解釋部分的總方差(σ2v+σ2u+σ2w)為2.6501,這其中56.55%的部分由并購雙方議價能力對成交價格的影響所貢獻。

表3 方差分解(全樣本)
3.并購雙方議價能力導致成交價格偏離程度
下面估算并購雙方的議價能力使成交價格相對于公允價格的偏離程度。偏離度分別為E(u|?)和E(w|?),分別代表主并購方公司議價能力與被并購方企業議價能力使成交價格偏離公允價格的百分比,這兩個數值由式(6)和式(7)估計出來。而在并購雙方共同作用下成交價格相對于公允價格的偏離程度可通過估計式(8)來獲得。表4給出了全樣本的估計結果,平均而言,主并購方上市公司的討價還價能力使成交價格比公允價格降低48.9%,而被并購方企業的議價能力導致成交價格較公允價格高出43.3%,兩者的凈效果造成我國上市公司并購價格低于公允價格5.6%。這意味著,總體來說,我國上市公司的議價能力還是較強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未上市的被并購方企業其盈利能力以及治理狀況均無法與上市公司相比(在本文樣本區間內,僅有135家被并購方企業是上市公司),而主并購方的上市公司比被并購方企業掌握更多的信息。
此外,表4的4~6列還呈現了并購雙方議價能力對成交價格影響的分布特征。由表4可知,我國上市公司在并購價格的決定過程中的議價能力具有異質性,同時,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都處于劣勢。具體而言,由第1四分位(Q1)的統計結果可知,在并購過程中,全樣本中有1/4的上市公司被目標企業獲取了11.7%的剩余。而從第3四分位(Q3)的統計結果來看,另有1/4的上市公司,在并購過程中獲取了高達22.8%的剩余。

表4 并購雙方議價能力和兩者凈效果的統計性描述(全樣本)
二、雙邊隨機邊界模型的估計:國內并購與跨國并購
為了探尋結論在我國上市公司在國內并購市場與國外并購市場中議價能力的異質性,同時考慮到結論的穩健性,將全樣本劃分為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兩組分別進行雙邊隨機邊界模型的估計3。將樣本按照被并購方企業所屬國別劃分為兩組后,國內并購組有4851個并購事件,占總樣本的94.76%,相應的跨國并購組有268個并購事件,占總樣本的5.24%。表5呈現了國內并購市場與跨國并購市場中,并購雙方討價還價中所獲得的剩余以及總剩余的比對結果。
由表5的結果可知,我國上市公司在實施國內并購與跨國并購時,其通過議價能力所獲得的剩余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在國內并購市場中,我國上市公司面臨著接受一個低于公允價格的成交價格,即我國上市公司相對于被并購方企業具備更強的議價能力,作為并購方的上市公司經討價還價后使得成交價格低于公允價格7.1%。而在跨國并購市場中情況則完全相反。表5結果表明由于并購雙方的議價能力的差距,我國上市公司需要比公允價格多支出5.5%的資金才能完成一例跨國并購事件。這意味著我國上市公司在跨國并購市場中討價還價能力較國外企業差,在談判過程中處于劣勢。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國上市公司對國外目標企業的未來盈利預期、品牌價值以及業務情況等都缺乏相應的了解,對合作伙伴的業務水平更是了解甚微。同時,我國多數企業對海外目前企業所屬國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風俗習慣甚至是語言都不熟悉,由此導致一系列管理摩擦或經營失誤而導致自己在價格談判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從而大大降低了跨國并購交易中的討價還價能力。另一方面,我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主要以現金支付為主(全樣本中約9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支付方式為現金支付),這無疑大大增加了并購價格(成本)。與此同時,由于跨國并購至少涉及兩種及以上的貨幣,因此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強弱程度也會影響到并購成本,從而影響到公司的討價還價能力。

表5 國內并購與跨國并購議價能力的差異
此外,表5還報告了不同市場中,并購雙方所獲得剩余以及總剩余的分布特征。在國內并購子樣本組中,第1四分位(Q1)上,并購雙方通過討價還價能力所獲凈剩余為負,表明存在1/4的上市公司損失了9.9%的剩余。而從第3四分位(Q3)的統計結果來看,另有1/4的上市公司,在國內并購過程中獲取了高達24%的剩余。而對于跨國并購子樣本組,由第1四分位(Q1)的結果可知,存在1/4的上市公司跨國并購損失了高達36.3%的剩余,而第3四分位(Q3)上,也存在1/4的上市公司跨國并購中獲得了約22%的剩余,可見不同分位的主并購方上市公司通過議價能力所獲得的剩余存在差異。
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2003~2013年間我國5119起并購事件,在雙邊隨機邊界模型框架下,首次對我國上市公司在國內外并購市場上的討價還價能力進行定量估算。結論如下:(1)全樣本測算結果表明,主并購方上市公司憑借其討價還價能力將以48.9%的幅度降低成交價格,而被并購方企業的議價能力以43.3%的幅度提高成交價格。這兩種相反的作用將使得成交價格相對于公允價格下降5.6%,然而子樣本估計結果表明,這其中主要是由國內并購市場所貢獻的。平均而言,我國上市公司都將接受一個低于公允價格的價格,只是不同上市公司所面對的下降幅度不同。(2)按照被并購方企業所屬國家分組后,兩組子樣本組中差異巨大,在國內并購市場中,我國上市公司面臨著接受一個低于公允價格的成交價格,成交價格相對于公允價格下降7.1%。在海外并購市場中,我國上市公司需要比公允價格多支出5.5%的資金才能完成一例跨國并購事件。
由上述結論可知,我國上市公司在國內并購市場上占據有利地位,而在海外并購市場上處于劣勢,鑒于此,提出以下幾方面建議:(1)加大對海外被并購方企業以及東道國市場的了解程度。在決定進行跨國并之前需要認真考慮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海外被并購方企業所在的行業的生命周期,如果是夕陽企業,則并購速度一定要放緩,并購決策需要謹小慎微;其二,擬并購的海外企業是否具有技術、品牌、市場、管理和人才優勢,如果存在,那么能否對此進行較好的吸收;其三,如果對海外目標進行并購,我國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能否防止在與國外對手進行談判中避免陷入被動局面。(2)謹慎的選擇合適的并購融資渠道。跨國并購需要大量資金,因此良好的融資支付結構是并購成功的關鍵,相較于國內并購而言,跨國并購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是跨國公司一般不會完全通過自有資金來完成,超額負債會導致企業一蹶不振。現階段我國金融市場的落后使得并購支付工具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上市公司在選擇支付方式是更要謹慎。(3)積極建立一支懂技術、懂管理、懂市場并熟悉海外環境的國際化人才隊伍。國際化專業人才隊伍的談判能力與并購成交價格的確定息息相關,只有提高談判能力,才能在跨國并購中確定一個相對公允的價格。
注釋
1.數據由國泰安“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整理而得。
2.此處的“剩余”借鑒經濟學中“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概念。
3.由于篇幅所限,子樣本雙邊隨機邊界模型結果與方差分解結果不進行披露,如由需要請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