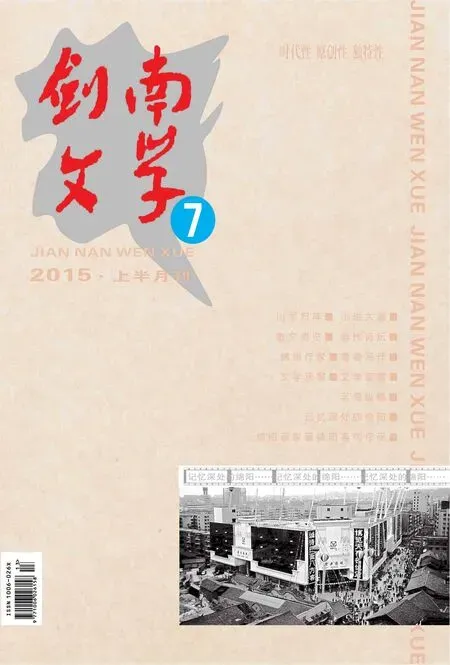我深深地愛戀我親親的母土……
——《往事老北川》代序
■母碧芳
我深深地愛戀我親親的母土……
——《往事老北川》代序
■母碧芳
家鄉還在,家鄉一直都還在那兒!
被稱之為震驚全球的那場大震已經過去好幾年了,我都還不能面對那慘絕人寰的現實。
我那山裹城、城繞水,縣城心窩里流淌著一條三色河的谷底小鎮喲,只要一想到她,心中就會涌動著那許許多多剪不斷,理不清的關于生命信息的符碼,地層深邃的秘密……就會聞到許許多多熟悉的味道……聽到許許多多熟悉的聲音……看到許許多多熟悉的身影——
白云深處的古碉、神奇烈烈的經幡;彎彎山澗中的晨風、艷艷的朝霞;藍天下羊兒跟著云兒跑、云兒繞著羊兒飄;土路夕陽下悠悠揚揚的羌笛、裊裊炊煙里深情款款的口弦;那些個會說話時就會唱歌,會走路后就會跳舞,一嗓子吼到了天上去了,腳根還扎在泥土里,從古至今基因里就有著山歌和舞蹈的羌族兄弟姐妹,他們羌繡盈身,炫幻神幽,揮舞著羌紅,可以拉著樹兒唱歌,也可以牽著云兒跳舞,讓情歌吼綠一片片山林,把歲月揉進一壇壇咂酒……在那里你隨便走走,就走進了原始,走進了古代。
一切一切都還那么熟悉、那么親切喲……
母土是一塊大磁鐵,我是她身上掉下來細碎的鐵沫,無能怎樣都要被她吸引回去的。
不知道那算第幾感,每次回去,撕裂的大山,橫陳的巨石都會牽動著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經。地震中要么全家都走了的人,要么就走得只剩下一個孤獨地活著的人,都那么活脫脫地站在我面前——我會頓感一種刻骨入膸、銷魂蝕魄的疼痛。
如果看見天空有一縷陰云,就覺得那似乎是一道隱喻,穿巡曲城那些斷壁殘垣時,我的腳步輕了又輕,生怕踩疼了我那滿目瘡痍、遍體鱗傷的母土,踩疼了我罹難同胞的魂靈……我甚至抱著一棵樹都像抱著一個久違的親人而啜泣不已……揮別時,總有一種生死絕別的感覺,總想把對親親母土深深的哀挽和愛戀儲在大山的皺折里,留在家鄉的記憶里……
回到市里了,老縣城還那么完整無缺地晃動在我腦海里……那些蟄伏多年的思緒象一群群蜜蜂,重行復重行在我那窮富交織、載欣載悲的母土上……
可是無論怎樣,我都得面對現實了,家鄉沒有了,老北川沒有了。現在她就是一座萬人塚、一座巨型的露天地震博物館、N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數據庫,成天供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吊唁、參觀、收集、考察及思索……
那里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似乎都成了零,但她卻還那么有價值,現在看到的老北川是一種文化、歷史、地質意義上的存在了。人們悉心地在那兒打撈著,一星兒一星兒地打起老北川的各色各種碎片。我也責無旁貸地加入到這個行列中---我試圖從文學的角度去打撈。老北川于我來說,山已不是那些山,河也不是那些河了,可心還是那顆心。命中注定鐘情的故鄉,讓我有一種神秘的皈依意識。我吃母土長出的五谷雜糧,穿戴大山云霧紡織的五彩霓裳。我笑過她的笑,哭過她的哭。應該說母土是一方啟迪我創作的精神資源、文化資源,更是催生、引發我想象力的磁場。從山之巔、谷之底沿著大地或沖或流、或高或低、或急或緩,一泄千里萬里的三色河是燃燒我一生的血液,在那禹山禹水中尋找記憶的密碼,那是我書寫的“母本”,我的生命與精神的源頭,我的全部知識、文化譜系的根基,我們的歷史、生活和經驗的真相。
當漸行漸遠的時間沉淀與當代生活的圖景和符號在深厚的地層中渾然雜沉,再歷經年代的風化而像地質斷層式的畫面呈現出來后,該是多么好的素材。
我總是想著我應該把一個個零碎的、個體的記憶匯集起來,構成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把在這片母土上我所經歷、所了解的往事寫下來,傳給后人。曾有個作家說過:“有些人寫什么或能寫什么幾乎是命定,甚至是非他莫屬的,他不寫,這東西就永遠不會出現。”往事鉤沉,翻洗一個民族的底片,再現一個民族的魂靈,這就是一種責任和使命啊!
關于家鄉的記憶清醒得一如我昨天才面臨過的人、事和現場,糾結得像山里那些盤根虬曲的老樹,怎么怎么都難以理出個頭緒。我與那些往事象來自前世的約定,它們是一定要在這時匯集來我筆下的。所以,2009年,我出版了5.12大型紀實文學《北川殤》之后,2010年我又以《百年母土》命名申報了中國作協重點扶持作品。申報時,我就想,管它怎樣,我都必須完成這部小說。但是真正動筆后,才發現這部小說命題太大,構架沉重,難以著筆。這時各種建議也來了,就有人建議寫地震、有人建議寫遷城、寫雙城記、寫重建,但我覺得這些好象都不能表達我的創作主詣。家園的泯滅、史料的缺失,故鄉在風塵廢墟中若隱若現。我總想把那個歷史的北川和我感知的北川經過淘洗、揉合,抽離后,再來動筆。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作家的寫作只為本民族所理解的話,那他是有罪的,因為這樣他會造成一個民族的短視。
最后想來思去,還是落腳在寫一群羌族釋比承傳人的故事上。因為一個民族的靈魂,便是他的文化,而羌族文化的魂靈,就是釋比文化。只有讓人解讀了這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才有可能解讀這個民族的生活故事。
可是,這于我來說又恰恰是很陌生的領域。雖然在母土生活了30多年,但所了解的博大精深、幽幻神秘的釋比文化僅僅是毛皮耳。因而,創作中的困惑是前幾部長篇小說都沒有遇到過的。這就要求我必須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先去走訪、閱讀、體驗、追憶、筆錄……慢慢地,我覺著這部小說走的是一條高難度和危險的創作路線,幾乎似神性的寫作,非“十年磨一劍”不可。所以我想,與其草率成書,不如慢慢熬煉,先執筆一部關于老北川的隨筆、散文和特寫。
于是就有了這部《往事老北川》。這部書的整體結構恰似一列多節車廂串成的小火車,她既是外向的、經驗式的、記錄式的、表現式的、再現式的傳統文本,也是內向的、內省的、思索的、拷問的觀念文本。在這部書中,除了一些新作外,還收輯了原來發表過的一些相關老北川的篇什,前面收輯了《家鄉有條三色河》、《云影里的阿爸許》、《一個山谷一個太陽》、《圣歌北川》四輯。后面又以《母土之外的視角》收錄幾篇走出故鄉之后所寫的比較大型的文章。
從家鄉那條三色河到羌韻悠悠的尚武村;到從獸油燈下到老屋殘夢;從春天那金黃的告別到一個山谷一個太陽;從今夜,我又是孩兒王到走過40年我們來相會;從竹語泉聲女壽星到老爸老媽鉆石婚;從云影里的阿爸“許”到總書記號召學習的時代楷模蘭輝;從“包餃子”的魔咒到兩次遷城;從紫土蒼綠到“武引”第一筆;我力圖以一種膠著性、情意性的語言風格和生動形象的人物、場景描繪,鞭辭入理的哲學思辨,全方位、大視角地闡述老北川的人文風情、時政變革以及我自身與周圍人等的心路歷程,表達我對親親母土的深深愛戀……
母土伴兒一生,鄉愁隨女百年。跨欄式寫作很痛苦,字字都象芒刺,刺進心窩;但寫這樣的文章也很享受,句句都在跳躍,閃著靈光。如果說這些比較接地氣的文章或多或少地于社會傳遞了一些正能量,并獲得過一些榮譽,那也歸功于母土對我的養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