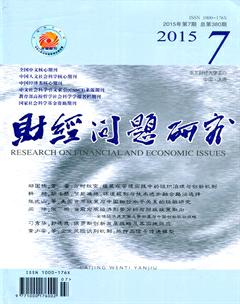我國制造業集群升級的影響因素研究
葉笛 林峰 劉震宇



摘 要:全球經濟動蕩給我國傳統制造業產業集群帶來了機遇與挑戰,順應產業轉型升級趨勢,是我國理論界與實業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本文圍繞核心企業轉型和集群成員互動與集群升級的內在關系這一基本問題進行研究,發現即便是核心企業轉型成功也有可能弱化本地集群,只有當其轉型通過集群成員實現資源整合協同效應時,轉型才能帶動整體集群升級發展。本文探尋實現核心企業轉型與產業集群協同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以期為尋求我國產業集群持續的成長動力與競爭優勢提供相應的建議和對策。
關鍵詞:制造業集群;核心企業;集群升級;企業轉型
中圖分類號:F42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7-0030-10
全球經濟動蕩給我國傳統制造業產業集群帶來了機遇與挑戰,順應產業轉型升級趨勢,改變我國地方產業集群在國際分工中的弱勢地位,增強集群競爭力是目前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界與實業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都意識到產業集群內核心企業(Core Enterprises)所擔任的任務和角色是異質獨特的[1-2]。同時,許多學者在研究如何維持我國產業集群的競爭力時都提出集群企業必須適時轉型與升級[3]。但目前的相關研究,在探討企業轉型績效和轉型能力的問題時往往僅考慮企業自身層面,未從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它所擁有的網絡資源和產業集群這一更廣泛的層面和情境來考慮,僅關注企業自身層面的因素而忽視它的網絡資源通常會使分析缺乏一定的遠見。王棟等[4]在分析企業轉型的因素時提出,研究戰略變化除了需要分析內部資源,更需要分析企業間網絡的作用。
集群核心企業在轉型過程中,必須選擇新的業務重點,改變原有網絡資源利用的方式,根據產業鏈和價值網絡不斷地重新篩選和剔除不勝任的合作伙伴,尋找新的網絡合作伙伴,并實現新的網絡資源整合,集群的創新能力與競爭力不僅僅依賴于核心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還依賴于集群網絡成員關系重構所帶來的資源整合重構的協同能力。現實中,地方政府鼓勵集群核心企業轉型升級,但卻不知轉型企業如何帶動整體集群升級?核心企業轉型是否能帶動其所在的產業集群升級,亦或對集群造成動蕩的消極影響是目前理論界關注的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鑒于此,本文將深入探討產業集群內核心企業的轉型升級是否能帶動實現集群成員之間資源整合與協同創新的良性互動,帶動集群網絡整體創新能力提升并實現整體的產業集群升級。
一、理論基礎與模型提出
1.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集群創新績效、集群競爭力
由于核心企業的網絡嵌入性特征,其通常處于企業網絡中的關鍵節點,有能力設計并運營與其他企業不同的更大網絡關系,同時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不斷地拓展外部市場,不斷擴展和重新構建合作網絡[5],改變業務結構型態,重新設計和改進運營創新網絡結構,對集群內各伙伴的生產研發活動進行協調,創造出適應未來的新型經營模式,甚至引導集群內企業網絡結構和促進集群整體的動態發展[6]。
核心企業的動態轉型能力的大小直接關系到整個集群價值鏈上下游相關伙伴企業的命運,較強的動態轉型能力將有助于核心企業不斷快速地捕捉新市場導向和消費需求,也體現在核心企業的吸收能力將不斷學習新的技術,根據新的市場需求開發有針對性的創新產品[7],不斷引導用戶新的消費熱點。同時,核心企業在利用自身垂直或半垂直一體化進行生產的同時,還要將部分業務向集群內的中小伙伴企業分包,給予合作伙伴必要的技術指導,其在轉型過程中,根據產業鏈和價值網絡不斷地重新篩選和剔除不勝任的企業,其客觀上對合作伙伴企業施加了壓力,激發其不斷改進生產力,不斷改善產品質量和服務水準,促進協同創新,不斷延續本地集群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a:集群核心企業轉型能力正向影響集群創新績效。
H1b:集群核心企業轉型能力正向影響集群競爭力。
2.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集群資源協同能力
國外學者在研究企業轉型過程中的動態能力問題時,發現幾乎所有的被調查企業為了業務的發展而不得不重構所存在的資源或獲取新的額外資源。核心企業成長主要源于企業內知識、企業外及集群網絡中知識資源再整合[8-9],核心企業維持持續競爭優勢過程中的轉型成長階段的關鍵因素在于企業的資源以及其所嵌入的環境下所連接和獲取的資源[10-11]。企業進行轉型必然會引起企業構成要素及要素間關系的多層面變動,核心企業轉型需要整合、重構、獲取本地集聚的各種內外部資源,釋放資源、形成新的資源結構。在研究企業網絡進化時,核心企業更容易把與其他企業隨機的接觸發展成為持續的合作關系,同時更容易吸引其他企業加入合作網絡,并且有能力以自身為中心來設計、建構各種復雜的聯結關系,更有效地促進網絡內資源的整合與協同。
核心企業通過集群企業網絡內不同節點的資源互補,將自身的資源與其他伙伴企業的資源聯合起來,提升其自身的資源基礎和資源配置可選擇性[12-13]。集群中核心企業與集群內其他伙伴企業之間有意識的互動、協調,學習過程中將促進知識、技術和關系等各種異質性資源的共享和再整合[14]。核心企業通過識別機會,根據自身的資源情況和戰略轉型需求,不斷地對網絡資源和價值進行重構與再整合,不斷地剔除和更換不再勝任的企業,也將推動集群內部資源整合,實現協同最優化,該動態轉型能力將引導整個集群網絡能力的變化。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a:集群核心企業轉型能力正向影響集群資源協同能力。
H2b: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在集群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影響集群創新績效的機制中起中介作用。
H2c: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在集群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影響集群競爭力的機制中起中介作用。
3.集群成員重組彈性與集群績效、集群競爭力
集群中的企業網絡關系不宜過于持久,因為持久的網絡關系并不是那么適合彈性專精的需求,并且將導致被關系鎖定的危險[15-16]。集群企業面對動態競爭的環境應具備更加迅速、敏捷和柔性地適應競爭變化的組織能力。根據市場的需要,集群成員需要不斷創新、不斷地評估自身具備的各種網絡資源,必要時改組甚至重構自身以及與集群網絡各主體的關系。
當集群成員能夠有效靈活彈性地重組企業網絡關系,并利用網絡聯結有效地整合分散的知識與資源時,就能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協同系統。整合或協調集群成員的行動、知識及目標所采取的策略或行動方式,以達成集群共同的目標。集群內成員重組關系的彈性越好,集群內部的互動發生頻率就越高,也越能激活集群內分散在各成員企業間的各種異質性資源,有助于增加集群的資源基礎,更好地促進集群內資源的整合[17]。同時,集群內部成員企業良好的重組彈性,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更好地匯集集群內部分散的創新資源、提升集群內部各種創新資源和知識的利用率,提升集群的創新績效。同時集群企業間協作,可以通過異質性的資源和能力互補形成更大的集群競爭力,通過企業間互動重組,接受新思想和新知識的碰撞,將有助于集群克服原有的路徑依賴,形成應對環境變化的新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a:集群成員企業重組彈性正向影響集群競爭力。
H3b:集群成員企業重組彈性正向影響集群創新績效。
H4a:集群成員企業重組彈性正向影響集群資源協同能力。
H4b: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在集群成員企業重組彈性影響集群創新績效的機制中起中介作用。
H4c: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在集群成員企業重組彈性影響集群競爭力的機制中起中介作用。
4.集群資源協同能力與集群創新績效、集群競爭力
集群發展中有兩個重要的杠桿必須關注:一是如何借助集群來集聚資源;二是如何借助集群,通過伙伴企業的協同作用而充分利用資源。集群資源整合的結果是提升現有能力或者形成新的能力,資源整合能力越強,則越有機會提升集群的核心能力。對于集群內的單個企業來說,通過企業網絡資源的協同可以獲取很多企業原本不具有的資源,集群企業經過對集群內各種能力與資源的整合,將會帶來更高的績效和競爭實力的提升,集群內各成員企業能力的提升最終將有助于集群整體的績效和競爭力的發展。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5a:集群資源協同能力正向影響集群競爭力。
H5b:集群資源協同能力正向影響集群創新績效。
5.核心企業網絡位置屬性
錢錫紅等[18]認為不同的網絡位置在企業網絡中代表不同的獲得新知識和資源的機會。Wasserman和 Faust[19]認為企業的績效、奪獲資源等行為都可以被解釋為企業在創新網絡中所處位置的函數。Owen-Smith 和 Powell[20]也認為占據優勢網絡位置的企業可通過其位置聯結不同的網絡節點來取得資源和控制資源。本文選取網絡中心度作為衡量個體網絡位置屬性的特征變量,核心企業越是位于集群網絡的中心位置 (網絡中心性),核心企業的轉型成長越有利于集群資源的整合和協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6:集群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對集群資源協同能力的影響受到集群核心企業網絡位置屬性的正向調節。
6.集群成員網絡聯結屬性
企業網絡中維持的聯結模式指的是節點之間存在或缺少一些關系,是企業網絡間相互關系的穩定模式。聯結強度反映了成員企業嵌入集群的網絡程度,描述企業與網絡內各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對資源的可獲得性和可利用性等特點。大量研究表明,企業之間的聯結關系是影響資源整合和創新績效的重要變量。有部分學者認為聯結關系建立得越持久,網絡關系越穩定,則越有利于成員間彼此信任關系和共有行為規范的建立,并增強網絡成員企業之間的信息與知識交流。但與本文的觀點相同,也有大量研究認為集群網絡內部的關系不宜過于持久,否則將存在著被關系鎖定和僵化的危險,并導致集群的衰退。因此,對聯結久度的考慮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加以分析。因此,本文提出關于聯結屬性影響集群成員重組彈性對集群資源協同整合能力的路徑假設:
H7:集群成員重組彈性對集群資源協同能力的影響受到集群企業聯結屬性的正向調節。
二、研究方法
1.變量測度
本文參照Churchill[21]關于調查問卷設計及測量工具開發步驟的相關建議,模型中構念采用或改編自現有文獻中的有效測量方法,采用Bock等[22]的反向翻譯(Backward Translation)方法,結合本國的語言習慣、特點和語義對相關的題項進行適當修改,確保中文和原文版本測量工具之間的一致性。并通過與企業界人士的討論和預調研進一步修改完善并形成最終正式的調查問卷題項。問卷題項的測量均采用李克特(Likert)7級量表,并參考相關方法以盡量降低潛在偏差對獲取真實有效數據的不利影響。以下部分具體闡述本研究概念模型所采用的測量量表。
(1)集群創新績效。
根據前文提出的概念模型,本文對集群升級的測量,采用集群創新績效與集群競爭力兩個潛變量,分別代表集群演進的內在動力表現與外部市場表現。根據Zaheer 和Bell[23]以及 Thorgren和Wincent[24]的測量量表進行改編設計。本文采用了3個題項來度量集群網絡的創新績效,由被訪問的集群企業根據近3年內本集群與競爭對手集群平均水平的比較情況來進行主觀評分。
(2)集群競爭力。
本文以集群競爭力作為集群升級的另外一個被解釋變量(因變量)。對集群競爭力的測量側重強調集群在戰略柔性與市場表現方面的競爭優勢。本文借鑒劉恒江和陳繼祥[25],朱小斌和林慶[26]等相關學者的研究思路,并根據Zaheer 和Bell以及Thorgren和Wincent的測量量表進行改編設計,本文采用了3個題項,包括成長速度、戰略競爭力與柔性,從市場占有率及獲利率等角度來度量集群競爭力。
(3)核心企業轉型能力。
筆者認為,核心企業轉型能力是嵌入產業集群中的核心企業動態能力的一種重要表現,本文在該構念和測量上參考動態能力的相關研究,改編和修改自現有研究的量表,并增加到七級李克特量表以提升量表信度,采用標準量表開發的程序。本文構建核心企業轉型能力構念,并將該構念作為一個形成型的二階因子模型,將一階構念作為高階潛變量的形成型的指標,避免二階因子的復雜性的同時也要確保構念能夠概括不同的情境。二階構念分別由3個一階因子(市場導向、吸收能力和協調能力)構成二階因子的全部維度,三個維度共同促成核心企業形成轉型能力。核心企業轉型能力的3個維度之間相互補充,其中市場導向采用6個題項來測量,即有效的產生、傳播和對市場信息的響應能力。吸收能力采用4個題項來測量,即有效的獲取、同化、轉化和開發集群的知識和資源的能力。協調能力采用3個題項來測量,有效的資源分配、任務分派以及行動同步。最終本文形成13個題項來測量核心企業轉型能力。
(4)集群成員重組彈性。
本文提出的集群成員重組彈性作為集群動態能力的另一方面表現,指的是集群企業能夠迅速有效搜索到具有潛能的合作伙伴,并通過網絡伙伴的重新選擇和組合來快速的關聯現有資源或重新配置資源,實現集群內各企業所擁有內外部的資源與技術的有效配置。伙伴之間實現重組彈性必須具有相匹配的專業技能和較連貫的工作流程。相關研究采用成員合作將提供相似的產品或服務、成員合作具有相似的溝通系統屬性、成員合作時具有相似的管理系統屬性和成員合作時具有相似的信息系統屬性4個題項的李克特5級量表進行測量。綜合借鑒相關文獻的觀點,本文對集群成員重組彈性變量采用5個題項來測量。
(5)集群資源協同能力。
本文將集群資源協同能力作為中介變量,集群的資源協同是將不同成員企業所擁有的知識和資源加以組合,形成新的知識和資源,本文將其作為一個形成型的二階潛變量,通過借鑒Fritsch 和 Kauffeld-Monz[27]的量表測量成員企業間資源界面整合表現,測量能夠有效地在戰略合作層面上整合各自的專業經驗與資源,實現良好的項目銜接和創新開發能力。
(6)集群核心企業網絡位置屬性和聯結屬性。
網絡位置中心度用來表示企業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特征,可用來衡量企業與其他企業進行交流的能力。借鑒Batjargal和Liu[28]的相關文獻,本文采用4個題項來測量。聯結強度也即關系強度,是集群網絡內企業聯結屬性的一個重要變量,代表企業嵌入于戰略網絡中程度的重要指標。基于Uzzi[29]和鄔愛其等的相關研究文獻和專家意見的結合,并考慮到問卷的實際可操作性,本文僅考慮一級企業網絡,最終采用3個題項來測量集群內企業的聯結強度,詢問集群內成員企業與主要供應商、客戶以及其他企業的合作交流程度。
(7)控制變量。
本文對可能對集群升級的創新績效和競爭力產生較大影響的其它變量進行控制,選取環境動蕩性作為控制變量之一,從市場動蕩性和技術動蕩性兩方面來評價環境動蕩性。市場動蕩性主要指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因素;技術動蕩性包括新產品的推出、對現有產品的改進、新工藝和新技術更新的速度與頻率等相關技術方面。其他的控制變量還包括了集群規模以及行業類型。這些控制變量與集群網絡動態演進的內在關系無關,但可能會對所選取的集群創新績效和集群競爭力指標等產生影響,例如,由于一般研究認為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在績效與創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目前仍無絕對論斷,因此,為盡量避免這一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對其進行控制,并將所選取的調研對象限制在制造業集群內。
2.調查方法控制
本文將調研范圍限定在江蘇、福建和廣東等東部沿海較為發達省市參與全球制造網絡的集群企業,將發放對象范圍限定于具有一定工作年限對所在地區產業集群有較為清晰認知的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本文對廣東、福建、江蘇和上海幾個地區的集群企業發放了385份正式調查問卷,回收了273份調查問卷,其中有210份有效問卷,問卷的回收率為70.900%(273 /385),有效回收率達到76.900%(210/273),因此可忽略本次問卷調研回收的未回答偏差。本文主要針對樣本的基本統計資料,包括企業所在地區、所屬產業類型、所處的部門環節類型、員工數量(企業規模)和伙伴企業合作類型等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分析樣本的類型、特性以及比例分配情況。本文使用SmartPLS 2.0來對所有的研究構念進行交叉因子載荷分析,將因子載荷值低于0.500的題項刪除,最終得到符合條件的變量表,如表1所示。
本文首先對受訪對象的樣本特征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本文模型是多段式,采用結構方程模型來同時檢驗多重關系,選擇PLS方法來檢驗假設。PLS方法可以分析多重題項和多構面的復雜結構模型,適合檢驗復雜的關系,其較可避免因素的不確定性,該方法在探索復雜關系方面的有效性已被大量的其他研究所證明,并且其當前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管理研究領域。PLS方法可以同時處理由反映型(Reflective)指標及構成型(Formative)兩種不同類型指標所組成的測量模型。本文綜合應用SPSS 15.0和SmartPLS 2.0等基于結構方程模型技術的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和假設檢驗。本文將首先評價測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其次利用結構模型來檢驗假設。
1.測量模型分析
(1)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首先考察量表的各題項在其相應的構念上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并將因子載荷量低于0.500的題項刪除,以確定最終量表,結果如表1所示。由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所有構念的測量量表都達到Cronbachs α系數和綜合信度ρc系數的最低要求,表明本文的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由于二階形成型構念不需要考慮收斂效度問題,因此表1數據顯示除其之外的其他潛變量的AVE值都在0.500以上,表明本文所有構念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為了滿足一定的區分效度,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必須小于0.900,AVE值的平方根必須大于內部構念之間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矩陣的結果如表2所示。AVE的值均大于所在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說明這些構念之間具有較高的區分效度。綜上,表2顯示了各構念的Cronbachs α、組合信度(CR)與平均變異萃取量(AVE)的值皆滿足前述標準,顯示本文所采用的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及收斂效度。
(2)二階潛變量分析。
筆者認為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包括市場導向、吸收能力以及協調能力。因此,將核心企業轉型能力作為二階形成型構念,檢驗采用二階形成型構念是否恰當。二階構念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可通過計算一階構念和二階構念權重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的運用來獲得:
HFTC=0.440HFMO+0.370HFAC+0.326HFCC(1)
CRIC=0.544CPR+0.517CRI (2)
形成型指標的因子載荷如表3所示,一階構念的所有權重對核心企業轉型能力的影響是顯著的(p<0.001)。一階因子之間的相關系數低于0.800,因為反映型模型的一階因子之間的相關系數將顯示出極高的相關關系(通常大于0.800)。因此,本文將該構念作為形成型的構念更為恰當。同時采用中介效應檢驗來判斷二階構念核心企業轉型能力是否完全中介一階構念(核心企業市場導向,核心企業吸收能力和核心企業協調能力)對于集群資源整合的影響,這一步驟確保二階構念更精簡地代表了一階構念的含義,同時確保二階構念能完全實現其對因變量的預測能力,根據理論進行預測。
(3)共線性問題分析。通過
計算一階構念的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核心企業市場導向的VIF=2.548,核心企業吸收能力的VIF=2.344,核心企業協調能力的VIF=1.428,集群伙伴協作的VIF=2.432 ,集群資源整合的VIF=2.432,VIF都較低,因此可排除共線性問題。
2.結構模型分析及假設檢驗
依次分析內部模型,考察變量間的路徑影響關系,并判斷實證研究模型的顯著性。
(1)內生變量的解釋力度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的結果可知,研究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與效度,針對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性架構,進行模型主效應的假設檢驗,采用偏最小二乘回歸分析進行假設檢驗。結構模型的解釋力度可通過各內生變量的R2值來進行評價。各內生變量的R2結果如圖1所示。結構模型中集群資源協同能力的R2值為80.200%,集群創新績效的R2值為61%,集群競爭力的R2值為60.200%,表明所構建的研究模型對各研究構念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路徑系數顯著性分析。
本文通過觀察各構念之間的路徑系數及其顯著性來判斷模型各結構變量之間的關系,模型中的路徑系數代表變量之間的直接影響效應。圖1展示了實證模型中各構念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本文采用基于PLS的Bootstrap重抽樣法(N=500)來確定出每一條結構路徑的顯著性水平,Bootstrap方法同時分析了每條路徑所相對應的t統計量(路徑上括號內的數字,它位于相應的路徑系數的下方)。根據t統計量來判斷路徑系數的顯著性,結果顯示,本文的基本結構模型中,除了HFTC(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CC(集群競爭力)以及CIP(集群創新績效)之間的路徑系數沒通過顯著性檢驗之外,其他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都具有一定的統計顯著性。
(3)研究假設檢驗。
筆者進行結構模型實證數據分析,根據 Bootstrap(N=500)的顯著性檢驗結果,檢驗每個假設是否獲得支持。通過標準化的路徑系數的T統計值來進行判斷,得出模型的所有路徑系數以及解釋方差的結果,結果顯示核心企業轉型能力(β=0.684, P<0.001)、集群成員重組彈性(β=0.265, p<0.001)與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集群成員重組彈性與集群創新績效(β=0.347, p<0.001)以及集群競爭力(β=0.349, p<0.001)存在正向的直接效應,在99%的顯著水平下,主效應研究假設H2a、H3a、H3b和H4a獲得支持。
此外,從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到集群績效和集群競爭力的路徑系數高度顯著(β=0.318, P<0.01;β=0.297 ,P<0.01),表明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在提升集群績效和集群競爭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集群資源協同能力與集群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同時也與集群競爭力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因此假設H5a和H5b得到支持。
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和集群成員重組彈性共同解釋了資源協同能力的80.2%的變異。資源協同能力分別解釋了60.2%的集群競爭力方差變異以及集群績效61%的方差變異。
(4)中介效應分析。
筆者認為集群資源協同能力是重要的中介變量,其中介前因變量: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集群成員重組彈性和集群績效和集群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依據Baron和Kenny對中介效應的判斷標準,對中介效應參數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在表4中,集群資源協同能力完全中介了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集群績效和集群競爭力之間的關系,同時集群資源協同能力部分中介了集群成員重組彈性與集群績效和集群競爭力之間的關系。集群資源協同能力是重要的中介變量。具體表現在:當將集群資源協同能力作為中介變量加入到研究模型中時,因變量集群績效的被解釋方差顯著地由R2=0.571提高到R2=0.588,同時另一個因變量集群競爭力的被解釋方差也顯著地由R2=0.571提升到R2=0.590。綜上,這些結果證明了本文的論證,表明集群資源協同能力是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集群創新績效和集群競爭力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量,假設H2b和H2c獲得支持。集群資源協同能力也是集群成員重組彈性與集群創新績效和集群競爭力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量,假設H4b和H4c獲得支持。
IV-Med SE表示自變量到中介變量的標準誤。Med-DV SE表示中介變量到因變量的標準誤;HFTC表示自變量核心企業轉型能力;CPSC表示自變量集群成員重組彈性;CC表示因變量集群競爭力;CIP表示因變量集群創新績效。
本文采用 Baron和Kenny建議的Aroian 檢驗方程,并采用相關程序進行Sobel效應檢驗。Sobel檢驗方程如下:
z-value=ab/SQRT(b2sa2 +a2sb2 +sa2sb2)(3)
Sobel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顯示統計量均大于1.960,雙尾顯著性小于0.050,因此,結果再次證明了集群資源協同能力是自變量核心企業轉型能力與集群成員重組彈性與因變量集群創新績效和集群競爭力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量。
(5)調節效應分析。
針對核心企業網絡位置屬性以及伙伴聯結屬性的調節效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調節效果并不顯著。
最后,本文包含了三個控制變量——網絡規模、行業類型以及環境動態性。結果顯示,網絡規模、行業類型以及環境動態性與本文的其他構念之間的關系均不顯著。
本文的各假設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四、結 論
實證數據顯示,實證模型的14個假設中有10 個假設得到了支持。本文分析結果認為,應該辯證地看待集群網絡內核心企業的轉型行為,若核心企業的轉型中,與集群內伙伴企業之間能夠實現有意識的良性互動,協調和聯結集群內部知識、技術和關系等各種異質性資源,并通過集群成員的協同形成集群資源整合協同能力,該能力將有助于集群整體競爭力和創新績效的提升。但核心企業轉型也可能存在失敗的情況,集群核心企業轉型即對現有產業鏈的延伸或多元化投資,將帶來原有價值鏈縱向一體化的解構, 致使集群成員價值鏈在時間和空間上發生了斷裂,必然引發集群網絡資源的重組。盡管核心企業具有一定轉型能力,但當核心企業的轉型如果沒有解決好集群資源協同問題,即便是核心企業的轉型成功也有可能弱化本地集群,與集群發展的趨勢相違背時,則有可能導致集群發展方向的錯誤,并抑制集群的績效和競爭力。這也說明必須關注與監控集群核心企業轉型,集群內部核心企業的發展和轉型只有兼顧集群內伙伴成員及其資源的協同共生,才能發揮其對集群升級的良性促進作用。研究結果正印證了核心企業轉型能力對集群升級的正向影響是通過集群資源協同能力這一重要的中介機制實現的。
本文構建的理論分析框架模型尚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其存在的局限之處可作為未來研究進一步完善的方向。
由于研究時間、精力和資源的限制,主要采取實證研究和數據調研的分析方法,未來的研究可結合質性研究、案例研究和對比分析研究,通過一定時間段上對代表性的集群網絡內的企業進行跟蹤訪談和縱向研究,并結合客觀性的公開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將有助于更切合實際地探索集群網絡內的構成要素和網絡演化各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路徑。
未來研究也可在本文探索的基礎上,對于集群網絡進行分類,針對我國地區不同產業類型和技術類型的集群網絡演化開展比較研究,或對我國地區性產業集群和國外具有相似性產業特征和技術特征的集群網絡之間對比研究,也可以研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集群網絡演化特點,為我國地區產業集群的深化發展和演進升級提供更有意義的戰略對策和政策建議。
本文對集群演進升級的界定主要是從技術和經濟角度的發展進步考慮,探討集群的創新績效和經濟競爭力,隨著時代發展,集群的發展將提出例如環境等其他對集群升級的更高層次的要求,本文并未涉及,筆者希望隨著我國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和相關理論的不斷完善,未來對該主題的研究范疇的界定將得到不斷的豐富和拓展。
參考文獻:
[1] 朱嘉紅,鄔愛其.基于焦點企業成長的集群演進機理與模仿失敗[J].外國經濟管理,2004,(2):33-37.
[2] 劉友金,羅發友.基于焦點企業成長的集群演進機理研究——以長沙工程機械集群為例[J].管理世界,2005,(10):159-161.
[3] 趙昌文,許召元.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企業轉型升級的調查研究[J].管理世界,2013,(4):8-15.
[4] 王棟,魏澤龍,沈灝. 轉型背景下企業外部關系網絡、戰略導向對戰略變化速度的影響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 2011,(6):76-84.
[5] 黨興華,王方.核心企業知識權力運用對技術創新網絡關系治理行為的影響——基于關系能力角度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12):78-85.
[6] 許強,應翔君.核心企業主導下傳統產業集群和高技術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網絡比較——基于多案例研究[J].軟科學,2012,(6):10-15.
[7] 汪秀婷,杜海波,江澄,張瀝之.技術創新網絡中核心企業對創新績效影響:溝通和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12):33-44.
[8] 張喜征,李明.知識云組合:企業轉型升級中知識資本重構策略[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11):91-94.
[9] Nerkar, A.,Paruchuri, S. Evolution of R&D Capabilities: The Role of Knowledge Networks within a Firm[J]. Management Science, 2005,51(4):771-785.
[10] 李群,李霄,丁躍進.后金融危機時期長三角地區外貿企業轉型升級研究[J].經濟縱橫,2011,(5):62-65.
[11] Naujok,N. Evolution of Alliance Networks and Resources of Firms 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Dissertation[D]. Bamberg:University Bamberg,2003.
[12] 方剛.基于資源觀的企業網絡能力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13] 徐元國.集群企業網絡演進與龍頭企業集團的形成機理[J].經濟地理,2010,(9):1493-1501.
[14] Dyer,J.H.,Nobeoka,K.Creating and Managing a High Performance Knowledge Sharing Network:The Case of Toyot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3):345-367.
[15] Kenis,P.,Knoke, D. How Organizational Field Networks Shape Inter Organizational Tie-Formation Rat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5): 275-293.
[16] 范志剛.基于企業網絡的戰略柔性與企業創新績效提升機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17] Tolstoy,D.,Agndal,H. Network Resources Combin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of Small Biotech Firm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J].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0,30(2):24-36.
[18] Sirmon,D. G., Hitt,M. A., Ireland, R. D.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inside the Black Box[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1):273-293.
[18] 錢錫紅,楊永福,徐萬里.企業網絡位置、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一個交互效應模型[J].管理世界,2010,(5):118-129.
[19] Wasserman,S.,Faust,K. Socai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0] Owen-Smith, J. ,Powell,W. W. Knowledge Networks in the Boston Biotechnology Community[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15(1):5-21.
[22] 彭新敏. 企業網絡對技術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研究:利用性—探索性學習的中介效應[D]. 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23] Dhanaraj, C. , Parkhe, A. Orchestrating Innovation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 (3): 659- 669.
[21] Churchill,G.A.J.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Better Measures of Marketing Construct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9,10(5):20-35.
[22] Bock, G.W.,Zmud,R.W.,Kim,Y.G.,Lee,J.N.Behavioral Intention Form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Examining the Roles of Extrinsic Motivators, Social-Psychological Forces,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J].MIS Quarterly, 2005,(11):50-61.
[23] Zaheer, A., Bell, G. G. Benefiting from Network Position: Firm Capabilities, Structural Holes, and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26(2): 809-825.
[24] Thorgren,S., Wincent,J. Designing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for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Network Configuration, Formation and Governance[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2009, 26(3):148-166.
[25] 劉恒江,陳繼祥.產業集群競爭力研究述評[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4,(10):2-9.
[26] 朱小斌,林慶.中小企業集群競爭優勢來源的演化差異——基于浙江紹興紡織業集群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 2008,(10):75-86.
[27] Fritsch,M., Kauffeld-Monz, M.The Impact of Network Structure on Knowledge Transfer: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4(1):21-38.
[28] Batjargal, B., Liu,M.Entrepreneurs Access to Private Equity in China: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5): 159-172.
[29] Uzzi,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 in the Interfirm Network:The Paradox of Embeddenss[J].Admin.Sci.Quart,1997, 42(3):35-67.
[33] Fornell, C.,Bookstein, F. L. Tw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LISREL and PLS Applied to Consumer Exit-Voice Theory[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2, 19(2): 440–452.
[34] Wasko, M.M.S. Faraj. Why should I share? Examining Knowledge Contribution in Electronic Networks of Practice[J]. MIS Quarterly, 2005,29(1):1-23.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pgrad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lust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nergy of Cor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Cluster Members
Ye Di1 , Liu Zheng-Yu2, Lin Feng3
(1.3.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36202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XiamenUniversity, Xiamen,Fujian,362021,China)
Abstract:Chinas traditional industry clusters mee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the global economy goes ups and downs. Following the trend of industry upgradation is a highlight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oma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inciples of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as industry clusters in order to pursuit and establish its enduring growing dr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is paper gives research into dynamic evolution of cluster network, centering on its inher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structure flexibility of cluster members and defin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the core enterprises in cluster network”, finds out the dynamic and persistent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the core enterprises on network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ilemma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upgradation of Chinas cluster network.
Key words: Core enterprises; Clusterupgradation;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Synerg
(責任編輯:巴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