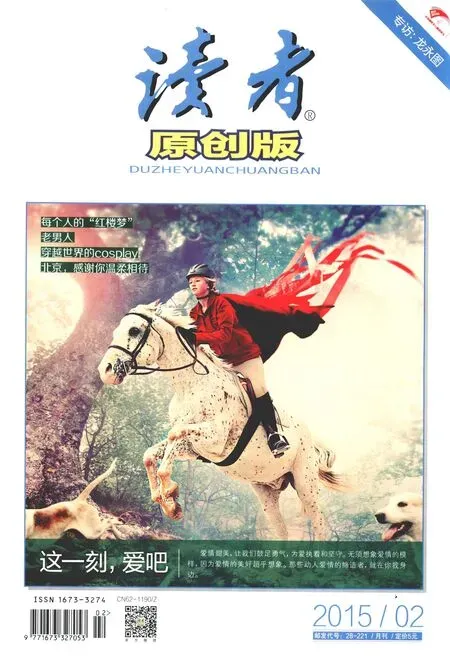龍永圖:大道至簡
文 _ 本刊特約記者 陳 敏
龍永圖:大道至簡
文 _ 本刊特約記者 陳 敏

2015年1月,龍永圖和白巖松合著的《中國,再啟動》出版。
這兩位都是奮斗改變命運的典型,一位來自貴州大山,一位來自呼倫貝爾的小鎮;一位從外交部的普通職員成為“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的政府高官;一位則從報社編輯變成家喻戶曉的名嘴。
作為世俗眼光里的成功人士,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來路,預測中國的未來?他們對個人的痛苦和幸福、時代的焦慮和信任危機、永恒的青春和信仰問題,有什么見解?
世上沒有一勞永逸的東西,而思考和變化永不停止。
我感興趣的,是書中兩人從不同視角出發對同一個問題的闡釋,既互相碰撞,又互相交融,讓人看到經歷后的智慧,思考后的提升。
采訪龍永圖前,我擔心他會比較累,這是他當天接受的第三個采訪。畢竟,他已經是72歲的人了。第一眼見到龍部長,就發現自己的擔心是多余的。他西裝革履,耳聰目明,交談中,邏輯縝密,談笑風生。
我想起白巖松在新書中對他的描述,說龍部長干事總是精氣神十足,而這種力量,來自“久違的理想主義和責任感”。白巖松說:“一個不把‘官’當官做的人,注定也不存在功成身
龍永圖,原外經貿部副部長。1992年,龍永圖介入中國復關談判。1997年2月,龍永圖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負責貿易談判及多邊經濟與法律事務。2001年11月,他在第一線領導的長達15年的“入世”談判圓滿落幕,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2003年初,龍永圖出任博鰲亞洲論壇的秘書長,致力于讓博鰲論壇成為最活躍的國際經濟論壇。退。龍永圖先生如同一個老兵,永遠不會退出戰場,只會優雅而執著地老去。離開副部長的位置,他做博鰲論壇的秘書長,又做與20國集團相關的工作,即便已如此繁忙,他又在故鄉貴州的電視臺開了一檔《論道》的電視節目,讓各路高人,在他遙遠而親近的故鄉,去議論、觀察最廣闊的世界。”

現在的龍永圖正在參與“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工作,案頭堆著高高的文件,為此殫精竭慮。然而,他活得比很多年輕人都有活力,內心一直裝著整個中國的進步、富裕這樣的大問題,躬耕不休。同時,他信奉“簡樸才健康”的生活理念,笑言“大道至簡”。
72歲的龍部長,讓我看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在世間行走時最徹底的實踐。正因為這樣的力量,“中國,再啟動”不會只是書名,而將照進每個人的生活。
怎樣把中國的故事說好,是很大的挑戰
《讀者·原創版》:您在國外居住了多年,國外對中國的評價有沒有什么大的變化?
龍永圖:總體上來講,國外對中國還是有很多的誤解。有個關鍵的原因,是中國發展太快,突然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國外出現了很多復雜的看法,有些是害怕,有些是質疑,還有一些是嫉妒。比如說我們和日本的關系,雖然我們之間有領土主權的糾紛,但是我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國一下子超過了日本。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一直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戰后在美國的幫助下成了世界第二大國。他們沒想到中國發展這么快。對中國的崛起,他們內心沒有準備,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對中國崛起有很多的誤解。中國經濟上升的時間正好是他們的經濟走下坡路的時代,一上一下反差很大,對他們的刺激也挺大。
《讀者·原創版》: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并不完全表示接受和敬佩?
龍永圖:對,中國的發展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是快,其他國家需要時間去消化,而我們在這樣短的時間里也沒有很好地來講述中國的故事;第二個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與很多國家意識形態不一樣,所以西方很多人戴著有色眼鏡看我們,有很強的政治色彩。
也有少數國家面對中國的崛起是敬佩的,像巴基斯坦等國。
《讀者·原創版》:您對此有什么好的建議?
龍永圖:外國人對中國不夠了解,帶來了復雜的國際局面。
還有一個原因,過去我們出國的人很少,現在每年中國有一億人次出去。有一些人素質比較差,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影響很壞。西方的媒體一炒作,使得怎樣提高國民素質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緊迫了。
中國的對外宣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怎樣把中國的故事說好,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讀者·原創版》:國內也有不少憤青。生活條件好了,年輕人依舊對社會有不滿。
龍永圖:任何國家都有憤青,中國也是如此。以前大家吃大鍋飯,要挨餓都挨餓,要穿帶補丁的褲子大家都穿,都是一樣的,所以人們的心態比較平和。改革開放30多年,貧富差距拉大了,即便是自己比過去好得多,但是一看比自己更好的,馬上產生心理落差。這是造成目前憤青增加的原因。
怎樣使大家的心態更好一點?需要信仰。
有中國特色的智庫變得非常重要
《讀者·原創版》:您在新書中提到基辛格的一句話,“信仰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您說,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生涯里面,您最想摘掉“觀察員”的帽子,并為此奮斗了很多年。現在您有沒有很想完成的目標?
龍永圖:最近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說,要打造一些有中國特色的智庫。我覺得中國很缺智庫,在處理一些國際、國內問題的時候,大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很多意見,特別是對國際問題,大家七嘴八舌,把本來簡單的事情搞得很復雜。現在互聯網輿論也很多元化,怎樣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之下,提出一些理智的、專業的意見?這樣一是便于中央決策,二是能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所以有中國特色的智庫變得非常重要,我正在參與其中。

龍永圖和白巖松

《讀者·原創版》:您剛才提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這個“中國特色”怎么理解?
龍永圖:中國特色的智庫就是指按照中國目前的國情,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智庫。比如關于轉基因產品的問題,很多觀點都不專業,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甚至違背一些常識,擾亂民心。最近我看到袁隆平的觀點,他肯定了轉基因產品。像這樣的科學家出來,在他的專業領域講話,才會真正引導輿論。所以,智庫必須很專業,老百姓才會信任和接受。
我在國際貿易談判當中應該算是比較專業的。前一段時間大家都在反對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時候,我就出來講話,我說這不是美國人搞出來的,也不是一個要把中國邊緣化的陰謀。把事情講清楚了,中央最后接受了這個意見,對TPP采取開放的態度,采取樂見其成的態度。
這就是智庫的作用。
《讀者·原創版》:所以,您對建設智庫有很高的期望。
龍永圖:我們現在的輿論環境是多元化的,允許百花齊放,但還是要有權威、理智、專業的意見引導輿論。到了這個年齡,我也不想做別的。我們退下來的一批官員,還有院士、教授,還可以貢獻力量,都感到很高興。我們在參與一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工作,研究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問題,包括碰到一些具體問題時怎么解決。
《讀者·原創版》:現在談中國企業如何走出去,您認為優勢和劣勢各自在哪里?
龍永圖:以前講弱國無外交,即使企業走出去,人家也不相信你。現在中國變得強大了,外匯儲備充裕,在外面也建高鐵、橋梁、港口……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這是很難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會得到基本的信任,這個信譽度是很大的資本。
還有個優勢在于中國搞了30多年制造業累積的經驗。中國是“世界工廠”,在制造業領域有優勢,也有一批人才。
但是,我們缺乏國際化的人才,缺乏真正懂外語、懂國外的規則、懂國外的法律的人。中國的企業文化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比較大,到了國外都想找關系,找捷徑,而不是靠法律、靠自己的努力解決問題,這是企業文化的弱點。還有,雖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相當一部分人吃不了苦,到了國外第一件事就是找中餐,沒有中國飯吃就活不了,適應性比較差。
《讀者·原創版》:找關系、拼爹、怕吃苦、不夠踏實……談到這些現狀,您會覺得焦慮嗎?
龍永圖:不要著急,年輕人有一個成熟和成長的過程。有時候經歷一兩件重要的事情,年輕人會改變自己的一些思維方式,這種自我的教育是特別重要的。你成天給他灌輸一些內容,他反而有逆反心理。在政治環境、商業環境和社會環境都逐漸改善,變得更好之后,他也會在這個環境中調節過來,這需要多給他一些時間,多一些陪伴。

龍永圖對話馬云
大道至簡
《讀者·原創版》:在新書中,您回憶起下鄉割稻的時候,父親特意在您的口袋里放了三顆糖;有一年中秋,弟弟給您留了半塊月餅。您覺得這種包含在物質之中的情感才是更珍貴的。現在物質豐富了,反而有很多人覺得物質本身更值得追求。您怎么看?
龍永圖:現在人們對于親情看得比較淡。以前我每次出國,帶一點兒小東西回來,家人都挺高興,現在不同了。物質的東西太多了以后,精神的東西慢慢變得少了。原來的那些物質,一塊糖上面附著很濃厚的親情;現在物質的東西就是物質的東西,它里面沒有感情的色彩。
《讀者·原創版》:因為它太容易得到。
龍永圖:是,現在物質太豐富了。我們也不能指責大家對物質的追求不對,但是怎么把握“度”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讀者·原創版》:您經歷過貧窮,這個烙印也很深,您是否想過,“我的理想就是賺到一百萬,或者是一千萬”,以此作為目標對抗貧窮?
龍永圖:我從來不這樣想,我覺得貧窮并不可恥,因為貧窮不是因為我懶,而是因為當時國家很窮。很幸運,我參與了一個歷史進程,見證了一個國家從貧窮走向富強,同時自己也獲得了地位和財富,過上了比較體面的生活。就像鄧小平講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真正搞社會主義,就不能讓老百姓窮下去。
我在新書里面也曾自嘲,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是3000美元,錢很多,可以在紐約的大商場買30套很好的西裝。但是我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國家了,就穿件地攤上淘來的便宜西裝,也不覺得很丟人,因為“窮”是那個時代造成的。
《讀者·原創版》:當時上交工資是組織要求的嗎?
龍永圖:是要求的,但我們那一代人不會抱怨。那時候我覺得我能夠到聯合國去工作已經非常光榮了,西裝差一點就差一點吧。但是有的時候和其他國家的人在一起,也覺得很尷尬。每天午飯的時候,我都是到聯合國工作人員的餐廳去吃快餐,他們都是今天吃意大利餐,明天吃法國餐。我每次吃飯前都感覺很緊張,總是悄悄提前五分鐘就走了,免得人家到辦公室叫我,說“今天咱們到法國餐館去吧”。
《讀者·原創版》:那個時代的貧窮會讓您覺得拘束緊張,您怎么用另外的力量去平衡?
龍永圖:我當時覺得自己很優秀,在聯合國工作時,哪怕最開始只是一個最低級別的外交官,我提出的意見大家都很認可。國家大使開會的時候,當時中國搞經濟的外交官不懂英文,所以請我去參加小范圍的協商會議,大家開玩笑稱我是“龍大使”,我感覺很自豪。
《讀者·原創版》:這樣的心態真值得學習。您認為個人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分別是什么?
龍永圖:我前一段時間在企業家大會上講,我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從簡單到復雜,再回歸簡單。我們的社會也好,個人也好,最后都是回歸簡單,回歸自然,過很低碳、很儉樸的生活,過得很健康。人與人之間相處很融洽,沒有鉤心斗角。

龍永圖對話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
社會越來越簡單,這里面有很深的含義。
《讀者·原創版》:這是否跟您在國外生活的經歷也有關?
龍永圖:越發達的國家,人們的生活越簡單。最有錢的人,他最后會追求簡單,注重家庭,過非常健康的生活。大道至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