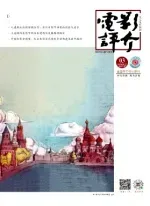淺析網絡小說改編青春電影的特色——以《何以笙簫默》為例
段惠芳
近幾年來,懷舊題材的青春電影以一股小清新之勢在華語影壇的關注度不斷攀升,不僅成功地將觀眾的視線從好萊塢大片拉回本土電影視線,而且展現出爭奪華語電影市場份額的強勁之勢。這些懷舊青春題材的電影共同特征都是由網絡點擊高的小說改編而成。2013年,趙薇處女作《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網絡作家辛夷塢同名小說)憑借7.91億元票房成為當年全國票房收入第二名的國產片,2014年《匆匆那年》(網絡作家九夜茴同名小說)收獲5.79億元的票房。2015年劉滿軍執導的《何以笙簫默》(顧漫同名小說改編)、蘇有朋執導的處女作《左耳》(饒雪漫同名小說改編)同樣受到熱捧,其中,《何以笙簫默》是網絡作家顧漫于2003年9月發表在晉江原創網的連載小說,有著上億的閱讀量,總積分高達2900萬。2015年1月10日,東方衛視和江蘇衛視同時播出其電視劇版,日播放量超過同檔期其他6部新劇的總和。《何以笙簫默》小說的暢銷和電視劇的熱播為其積累了很高的人氣;商業化的運行操作,題材選擇上符合了觀眾的欣賞口味、上映時間定位于五一假期,取得3.54億票房的不俗成績乃意料之中。
下面以《何以笙簫默》為主要案例,集中探討網絡小說改編青春電影在題材選擇、敘事策略和包裝宣傳上的特色,分析流行文化對電影創作的滲透,以及青春題材電影未來發展的生存之道。
一、網絡小說改編青春電影的題材選擇

電影《何以笙簫默》海報
1991年,全球第一個華文網路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問世,標志著網絡文學將成為中國文壇的組成部分。伴隨中國電影的蓬勃發展,電影技術和視頻制作技術的日新月異和更新普及,網絡的傳播效應使得越來越多的文學愛好者加入到寫作大軍,他們大都是業余的,精英文學受到極大的消解。2012 年舉行的“‘文學改編影視的第二次浪潮’主題論壇”上,導演李少紅就曾指出,網絡文學是影視產業鏈的重要一環。“網絡寫手聯手影視制作機構把草根文學與更多的社會化產業連接了起來,網絡文學已成為影視劇改編的沃土。”[1]網絡文學改編成電視劇、電影,與傳統文學不同的是依據網絡平臺,內容上更加貼近生活,往往帶有濃烈的時尚感和青春氣息。
這些網絡作者大都是出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這一代人是看著動畫片玩著網絡長大的,他們是伴隨著歐洲、美國電影成長起來的,因此,與精英作家相比,他們能更好地把握和選擇市場,這也是他們的作品更易于被影視改編的重要原因。與傳統文學相比,他們的文學作品更接地氣,走親民路線的生存之道即站在讀者的角度,講的是身邊的故事,能引起讀者(觀眾)的集體記憶狂歡。青春懷舊在網絡小說創作中非常突出,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生產中的重要內容,他們本身擁有廣泛的受眾群體和超人氣的市場效應,因此,青春網絡人氣小說能夠得到眾多影視導演的青睞。
中國并不缺乏青春題材的電影,青春題材在電影界已形成一種傳統。新中國成立17年和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中的青春很少深入內心,去探尋青春的真相和成長的真實。陳懷皚的《青春之歌》(1959)、黃蜀芹的《青春萬歲》(1983)等,這時候的電影主要是起著“號角”的作用,在特定的社會機制下對青少年起著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雖然拍了大量青春題材的影片,如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1995)、賈樟柯的《小武》(1998)和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2001)等,但這些電影拘泥于導演的個人表達和自我抒寫,主要借助青春和校園來抒寫導演對社會、時代和人生的揭露和反思,電影往往顯得壓抑和悲情。近年來,由網絡小說改編的青春電影,雖然延續了青春題材的傳統,但走溫情路線,將電影的策略和精神文化特質歸納為“消解歷史與溫暖在地”。[2]
網絡小說改編的青春題材電影,形成了清新的風格、唯美的畫面和流暢的敘事,使這類影片更迎合年輕觀眾的欣賞口味,高票房的收入正體現了大眾文化載體的一次集體反射,中國電影在網絡文學改編的劇本中的引領下走下圣壇,進入大眾視野,積極參與到主流文化的建構之中。同時,新世紀青春電影的主題和形式的多樣化,也折射了近幾年來電影文化多元發展的態勢。從《藍宇》(2001,改編子聿網絡小說《北京故事》)的同性戀問題,到《艋舺》(2010,改編九把刀同名網絡小說)的黑道情節,網絡作家和導演們用年輕觀眾認同的話語,分享他們成長的感悟和對人生的思考。
二、青春電影的敘事策略
當前,國產電影市場的低迷,導致了很多導演在創作上傾向于小成本電影制作。古裝片和戰爭片市場的不景氣,越來越多的導演將目光放在當紅網絡小說改編的青春電影制作上,初戀、校園文化和真摯友情,都成為青春電影的取材內容。從敘事策略上看,這些影片通過零星化、片段化的敘事、鏡頭的剪輯和轉換、將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戀愛或暗戀的故事娓娓道來,讓人們可以感覺到青春的純真美好和愛情的溫馨浪漫。同時,這類影片也繼承了好萊塢的敘事傳統,故事具有一定的懸念和戲劇性。例如,《匆匆那年》采用時空交錯式結構,把15年前高中到大學的過去時空和高中同學參加趙燁婚禮的現在空間,通過鏡頭的不斷切換和交替來展現男女主人公們步入社會后回首校園青春的故事。這類青春抒發的最大情懷就是“懷舊”,情節設置的慣例是,愛情最后都逃不脫分手的命運,“不悔夢歸處,只恨太匆匆”,方茴的一句話道出了青春的無悔。然而《何以笙簫默》打破了校園愛情有憾的情節慣例,男女主人公在分手7年后的重聚,青春成長的無知和尷尬通過“愛的救贖和洗禮”,最終譜寫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愛情頌歌。
青春是每一個人的黃金時代,這正是青春片擁有不竭票房號召力的根源。網絡文學改編的影片《何以笙簫默》以展現初戀的校園青春為題材,使觀影者能從中找到自我鏡像的認同感。通過片段化的橋段敘述,二人校園相遇相識、相知相愛、誤會別離場景逐步呈現在觀眾面前,細膩地刻畫了校園簡約唯美的愛情,引發觀眾的集體狂歡記憶。《何以笙簫默》以現實作為敘述的基礎,影片的整體結構就是在現實與回憶之間反復交錯形成的大量蒙太奇,7年前的青春校園與7年后的今天穿插進行,把校園戀愛綻放的純真和至誠發揮到了極致。
從敘事策略上看,大量運用圖解式符號表達“懷舊”的青春情感,因其在敘事系統中能提供特定的象征功能。比如郁蔥綠蔭的校園、揮灑汗水的操場、明亮寬敞的教室、親密熱鬧的學生宿舍等青春校園的場景符號,都見證了何以琛和趙默笙的相遇、相識、相戀的純美愛情。尤其是突出表現愛情的發生建立在逆光的大淺焦特寫鏡頭上,陽光里穿白襯衣膚色干凈的何以琛倚靠在樹下讀書,就這樣不經意間闖入了趙默笙的鏡頭里,愛情就在這一眼發生了,接著上演了一個女追男的長鏡頭,何以琛發現被偷拍、生氣離開,趙默笙緊緊追隨、急于辯解,并成功要到男主角的聯系方式,生動地表現了男主角的羞澀謹慎與女主角的活潑開朗的性格。引發80后懷舊的另一敘事元素,是富有濃郁校園印記的人物外形符號——齊耳短發、白襯衫、校服和貫穿影片始終的道具——借書證的證件照;意境之美的留白運用也突出了該影片的青春風格,如趙默笙名字來自徐志摩的詩句“……悄悄是別離的笙簫……沉默是今晚的康橋”等。由網絡小說改編的青春電影,導演們在電影作品中不斷嘗試引入各種文化元素來豐富鏡像表現,創造視覺奇觀,從而帶給觀眾全新的銀幕體驗。
三、青春電影的包裝宣傳
熱門網絡小說改編青春電影獲得“名利雙贏”的佳績,不僅是導演們追求電影本體語言上的探索,而且在包裝宣傳上也表現出商業頭腦和創新能力。電影作為一門視聽藝術,音樂的運用也是影片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何以笙簫默》請具有社會知名度、粉絲數量眾多的張靚穎、黃曉明和那英演唱劇中插曲和主題曲,通過他們的知名度也帶動了該劇的商業推廣;其二,該片中使用了已在受眾群體中產生一定影響力、耳熟能詳的歌曲作為插曲“You Are My Sunshine”,推動影視劇的收視高潮。
選角也是《何以笙簫默》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部影片都選用的國內一線演員或當紅小生來挑大梁,對于偶像劇的借鑒清晰可見。女主角楊冪外形甜美、清純可人,與導演心目中的“趙默笙”形象吻合。在男主角的選擇上,《何以笙簫默》也是遵循了偶像路線,挑選了高達帥氣的“男神”黃曉明飾演“校草”級人物何以琛。影片中賞心悅目的情侶組合符合唯美動人愛情故事的青春題材。
此外,《何以笙簫默》也是影視文化產業與網絡小說領域的一次跨界合作。顧漫是目前極具人氣的作家,其作品深受年輕人的追捧,作品《杉杉來吃》改編成電視劇《杉杉來了》獲得很高的收視率。電影《何以笙簫默》的制作充分利用了改編自同名網絡小說的優勢,小說版《何以笙簫默》積累的龐大的讀者群,電視劇版《何以笙簫默》超高的人氣,成為電影版的票房保證。
網絡小說改編的青春電影不斷涌現,導演在打造自己的作品時,常常融合各種類型片元素,力求將一些傳統的故事套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演繹,從而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和審美標準。《何以笙簫默》其故事框架是典型的“精英男+平凡女”的愛情套路,但影片中導演新增了人物——Willian,他默默愛著何以琛,從頭到尾提醒“別忘了吃藥”,從而引發了當前比較爭議熱門的同性戀話題的思考。在宣傳上,導演別出心裁地在水密碼官方微博上連載著《何以脫口秀》的小漫畫,成為引發觀眾觀賞興趣的重要手段。《何以笙簫默》獨特的表現方式和市場宣傳策略,對小成本電影拓展生存空間和沖擊商業票房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結語
盡管與傳統出版、文學期刊相比,網絡文學文學性和敘事技巧仍顯稚嫩,但網絡文學展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創作力。根據網絡文學改編的小成本制作的青春題材影片,與主旋律電影、好萊塢影片拼殺,仍能取得不俗的票房收入,但青春題材的影片除了懷舊與傷感之外,還應有感悟、鼓勵、鞭策等多能夠種情感表達,青春片應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1]李文浩,姜太軍.產業化背景下文學改編的契機與挑戰——以《失戀33天》和《等風來》為例[J].江西社會科學,2014(5):96-102.
[2]李道新.消解歷史與溫暖在地——2009年臺灣電影的情感訴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質[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0(1):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