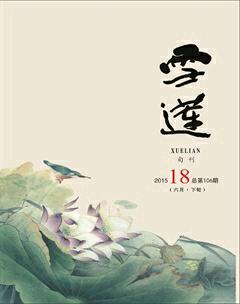孟子性善論與柏拉圖靈魂回憶說的比較
尹伶伊
【摘 要】在孟子的思想體系中,性善論始終作為整個體系的核心。當中,孟子提出了人們與生俱來的本性是善的觀點。由此,孟子還提出了“四心”和“四端”的觀點,并進一步深入闡釋。柏拉圖的靈魂回憶說則認為靈魂生活在理念世界中,并關照著理念世界。同時也認為只有靈魂是完美的,人的靈魂墮落到軀體之中會受到軀體的污染。
【關鍵詞】孟子;性善論;柏拉圖;靈魂回憶說
一、孟子的“性善論”
在繼承與發展了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之后,孟子提出作為人類相近的本性,人性之所以會產生差異,大部分是受到了后天的社會實踐和風俗習慣的深刻影響,進而在對人性善惡的分辨過程中對人的本質進行了明確的規定,最終才使“性善論”的學說得以產生。
善性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本性,這體現在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這“四心”反映出“仁義禮智”這四德,也規定并且制約著人與人的關系。它們本是人所共有的社會屬性,也是人區別于禽獸的根本屬性。“性善論”思想的終極理想是把作為個體的人性善推及至整個國家階級統治的道德共識。統治者忠于在國家政治上實施“仁政”,揚善棄惡,依順天道,以民意為重,最終實現賢人治國的仁義天下。現將“性善論”的幾個內涵簡析如下:
人本性向善。告子主張“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其中之意是指人性從本質上說不分善惡,就好似水流不可能始終從東向西流淌。孟子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依孟子看,人性如同水流總是從高處流向低處一樣。人性生來就是善的,而是因為在之后蒙受了外界俗世的干擾發生了變化,這本身有別于人性本質向善。
人區別于禽獸。告子認為“生之謂性”,也就是說人生來所有都是天性,“食色,性也。”指的是人的飲食和男女情感從本質上看也屬于人的天性,這種觀點在孟子看來,根本區別于禽獸,他認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認為告子的論述從本質上混淆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根本差異,并用“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進行了駁斥。孟子認為,人區別于禽獸的本質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的不忍之心包含“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這四心,如果人失去這四心,就失去了人的本性,也就不能稱之為人。
人善性的推及。孟子把人的四心推及到人的道德意識之中就是“仁、義、禮、智”,即“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將人具有的道德“四端”看作人軀體的四肢,缺一不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矣。”他認為人的道德“四端”與人不斷追求的道德標準不同,必須將其推及開來。故孟子說:“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只有將人的“四端”推及并完善,才能轉化成四海之德,便能安定天下。反之,對父母盡孝都做不到。
二、柏拉圖的“靈魂回憶說”
“靈魂”一詞來自于古希臘語中的“psyche”,其字面意思是幽靈,它標志著人的生命力,死后便拋之而去。所以大多古希臘的思想家們常常會思考人死后靈魂究竟去了哪里。其中,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不朽的,它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并關照著理念世界。同時,他認為只有神的靈魂才是完美的,而人的靈魂墮落到軀體之中會受到軀體的污染。
靈魂是永恒的。柏拉圖關于靈魂的學說不僅論證了如何認識理念,而且是對人性理論的研究,成為了后來西方基督教靈魂不死的形而上源頭。在《斐多篇》中,他描述了蘇格拉底直面死亡的淡定,不僅塑造了哲學家的智慧、勇氣及完美的人格,而且還升華了蘇格拉底靈魂不朽的信念,從而轉化為靈魂永恒理論。由于深受古希臘靈魂不死的傳統神源影響,柏拉圖認為人的肉體如同世界萬物一般,是產生感性世界的物質載體,具有生與死的形態。然而靈魂則擁有理性的力量,與“理念”息息相關,是永恒的象征。
靈魂先于肉體而存在。柏拉圖運用靈魂馬車的神話寓言說明了我們的視野觀察一切事物而順其自然的得到接納,并非肉體感官的認識與默認,而是由于我們的靈魂擁有一切事物的記憶。從世間萬物到宇宙之巔的善的法則都是靈魂對前世的回憶。
靈魂的解脫。柏拉圖指出必須依靠哲學的力量才能將靈魂從肉體中解放出來。由于人被肉體的情欲纏繞,給靈魂帶來毀滅,
使靈魂原本可以看到的肉體之外的真理變得模糊,最終導致靈魂的墮落。因此,只有不懈地追求哲學的真理與理智,才能使人無論生死,都能脫離世間的苦海。同時,柏拉圖將純粹理性狀態的靈魂劃分為理智、激情和欲望,分別表現為智慧、勇敢、節制三種德性。為了使靈魂發揮德性,三個部分必須由理智統領,才能使靈魂達到和諧統一,最終實現靈魂的完美凈化。
三、 “性善論”與“靈魂回憶說”的比較
(一)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就像水自然往低處流。他將良心稱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礎,并且是上天賦予人的,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人之所以能向善是因為人有實現善的本能,這就是性善的本質。柏拉圖的“理性的靈魂是人的本性”也體現出他是一位性善論者。他所說的理念世界中的理性就相當于孟子的“本心”。
(二)從不為善與人的本性來看。孟子強調人作惡是違背本性的表現,但與人性本善并不沖突。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和情意思相同都是性,人順應本性就會做出符合仁義的行為,不為善只是因為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導致暫時遮蔽和違背了自己善的本性,是一種外在的因素。柏拉圖認為人不為善有一定的必然性,這與他將靈魂做了三種區分有一定關聯。
(三)從如何至善的角度來看,孟子強調教育對人性培養的重要性。他把人的惡行歸結于沒有好好保養自己的本心,從而做出違背本性的行為。孟子主張“求其放心”的人格修養功夫。柏拉圖也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他認為學習就是回憶,經過適當的訓練,就可以回憶起曾關照過的理念,知識是靈魂固有的,需要教育和學習將它喚醒,知識幫助人們關注靈魂中的理性。不同的是,孟子強調人格修養,柏拉圖強調智力訓練和道德修養的統一。
總之,孟子的“性善論”和柏拉圖的“靈魂回憶說”都承認了人性本善,也引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怎樣進行德行的修養。研究二人的哲學思想,對人的價值實現和人們的生活具有深刻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