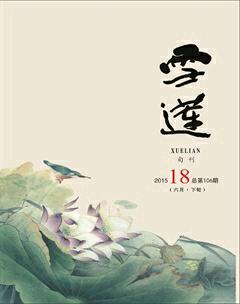20世紀初留日學生對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傳播
王艷
【摘 要】20世紀初,中國主要從日本輸入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留日學生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將創辦報刊作為主要傳播方式,大量引進能夠直接推動國內政治改革的新思想,體現了他們的傳播是有目的、有選擇、有組織的。
【關鍵詞】留日學生;民主政治理論;傳播主體;傳播方式
一、身負使命的學習者
在清末“留學救國”的社會思潮推動下,曾經掀起了一股留學日本的熱潮,留學與否甚至成為是否愛國的標志。在社會輿論和上層人士的推動下,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13人赴日留學,此后人數逐年增加,到1905年達八千人,可能是到那時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他們大部分進入專門接納中國學生的學校就讀,其課程根據留日學生的特點設置。如日華學堂于1898年在東京創立,設置正科和特別科,科目包括法學、日語、英語、德語、文學、地理等;創立于1904年9月的經緯學堂是明治大學的下屬機構,其課程包括刑律科、警務科、師范科等;早稻田大學也于1905年9月設立清國留學生部,其本科包括師范科、政治理財科、商科等。
當時學習政法的人最多,因為人們認為日本崛起正是因為政治改革的成功。國內新政改革的需要促使他們熱衷法政學科。1904年5月,日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的設立更使這類學生激增,“夫法政乃中國今日之最重之急務,自此科之設,其發達如此之速且盛”。他們在學校接受到了系統的法政教育,促使他們更關注政法類的新學問。
時人期望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將西方文化全面引進中國,特別是在政治制度層面上學習西方,所以留日學生們積極將所學的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向國內傳播。特別是日俄戰爭對國人思想的影響非常大,當立憲的日本戰勝專制的俄國之后,“在政治主義上也使人對于立憲自由增加一層新信仰”。受日本國內政治、社會環境的影響,留學生們更加熱衷于對民主政治的宣傳。學生中有的是青少年,有的是已有功名的士大夫,他們大都具有一定的判斷力,能夠從學校所學中選擇適合中國的政治學說,傳播到國內。
二、從接受者到傳播者
“受眾的群體背景或社會背景是決定他們對事物的態度和行動的重要因素”,當留日學生從接受者轉變為傳播者,他們“不但掌握著傳播工具與手段,而且決定著信息內容的取舍選擇”。傳播方式上,他們注重效率。傳播內容上,他們關注國內需求,選擇政治改革所需的經典著作。作為新理論的傳播者,他們在選擇內容時,是根據國內的情況而定,并非盲目選擇。留日學生是傳播主體,他們兼具接受者和傳播者兩種角色,他們的理論素養與傳播熱情,直接影響到傳播質量,他們選擇何種方式對傳播范圍和傳播效果有直接影響。在當時的中國,所有傳播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人員中,留日學生的熱情是最高的。留日學生從身負使命的接受者到熱情洋溢的傳播者,這兩種角色的轉變只在旦夕之間,他們幾乎是“朝受課程于講室,夕即移譯以餉祖國”。
作為受眾的留日學生,他們的價值取向、思想高度和時代背景影響他們的選擇。當他們轉變為傳播者,同樣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很自然地會以自己的理解去代替國內的受眾。他們能否真正理解國內民眾的接受力呢?他們極有可能選擇曾經給自己很大刺激的著作,將之譯介到國內,這些譯作即承載著留學生自己的理想。留學生在日本學習期間接觸到的新思想,特別是課程所學知識對他們的影響很大,如留學生翻譯的《日本憲法與各國憲法比較》,是日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所學的課程之一。留日學生的選擇雖然不能代表全部的國內民眾,但是他們的選擇確實影響了很大一部分國內民眾。
1903年以前,留學生已經成立了幾家翻譯社團,如譯書匯編社(1900年)、教科書譯輯社(1901年)、湖南編譯社(1902年)、國學社(1903年)等,這些翻譯社團都進行了有組織、有選擇的翻譯活動。1902至1903年,留日學生人數增加迅速,留學生創辦的刊物已經形成較穩定的讀者群,所以他們的譯述事業也特別興盛,這也導致有些書被多次翻譯,但是那些書亦是名家所著,符合社會需求,受到國內民眾歡迎。
二、重實效的傳播方式
新學說的引進及其影響范圍與效果,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傳播方式的選擇是很關鍵的一環。因為報刊具有傳播速度快、發行量大、傳播范圍廣、輿論影響大等優勢,所以留日學生首選報刊作為傳播媒介。梁啟超曾于1899年在《清議報》上說:“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于兵學藝學,而政治
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政治學被梁啟超看作“開國智強國基之急務”“本原之學”,這可以說是當時的知識分子的共識。
在1903年以前,由留日學生創辦的報刊主要有《開智錄》《譯書匯編》《國民報》《游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留日學生創辦的月刊《譯書匯編》,刊載民主政治理論文章最多,其宗旨便是“采擇東西各國政治之書,務播文明思想于國民”,該刊主要載歐美政法類名著,先連載譯文,連載完畢發行單行本。《游學譯編》是由留學生團體湖南編譯社創辦的月刊,該刊政治氣味較濃,不僅刊載譯文,也選譯與中國有關的報紙雜志上的論文,經常引用日本的學說和時論,不過還是以刊載譯文為主。初期的留學生并不具備做新聞報刊的條件,雖然如此,留學生創辦的雜志如《江蘇》《湖北學生界》等的水準還是比當時國內的雜志要高很多,因此擁有廣大的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報刊上的政法類文章是為了適應國內政治改革的需求,體現了他們對民主政治理論的選擇。因辦刊的資金來源不穩定,初期發行量較小,留學生創辦的報刊起初生存艱難,留學生必須有所選擇,他們看重的是西書的知名度,中國讀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對中國的有用度和適用度。其中大多是轉譯自日文的西書,很多都是經典之作,因此留日學生創辦的報刊才漸漸發展起來,在國內贏得大量讀者。
三、結語
關于留日學生引進新思想,人們常常稱之為“梁啟超式”的輸入,實際上不能如此籠統地評價。雖然梁啟超評價的是壬寅、癸卯(1902-1903)間的情況,但是在1904年以前,留日學生創辦的雜志、翻譯團體已經有很多,并且做出了不小的貢獻。留日學生帶著明確的目的奔赴日本留學,承擔著救亡圖存的使命,在日本忍辱負重地學習,將新知識以最快的方式傳播到國內。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引進大量新思想,本身對日語的掌握或許都不能說精通,又急于求成,所以就會出現“本末不具,派別不明”等情況。20世紀初“西方民主學說主要是通過日本的途徑介紹進來的”,那時擺在留日學生眼前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的成績,他們課業所學的亦是經典教材,且目中所見亦是受到日本社會歡迎而被時代認可的著作。因為自身的一些局限,導致留學生對西方政治理論的理解出現偏差,無法辨明本末之別,這也在所難免。
參考文獻:
[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