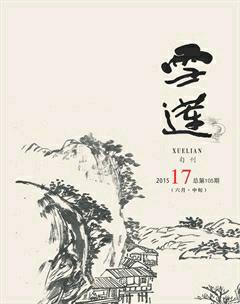論劉咸炘對魯迅唐傳奇觀的考評
梁冬
【摘 ?要】唐傳奇是中國小說發展的重要階段,是中國古典小說成熟的標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唐傳奇的興起、發展及作品收錄都進行了分析。劉咸炘則在魯迅的基礎上,從“辨體”的角度,對唐傳奇做了進一步的探究,他認為唐傳奇不同于六朝志怪小說,并提出唐傳奇最大的特點在于“行文逶迤”。
【關鍵詞】劉咸炘;魯迅;唐傳奇;《中國小說史略》
唐代之時,傳奇體小說誕生,并逐漸成為一代文學之盛,但歷代史家卻對傳奇作品鮮有收錄。《新唐書·藝文志》僅收錄了《補江總白猿傳》一篇傳奇,其他皆不著錄,明代胡應麟把小說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承認傳奇是小說,但是這種承認也有條件,只有那些體近史傳的作品如《飛燕外傳》《霍小玉傳》等,才能算作小說。到了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又把胡應麟“小說”分類中叢談、辨訂、箴規三類歸入子部雜家類,將志怪、雜錄兩類調整為雜事、異聞、瑣記三類,收入小說家,而傳奇類并沒有收錄。直至晚晴民國時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首列“唐之傳奇文”專節,唐傳奇才逐漸受到重視,而此后的學者也在此書的基礎上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
劉咸炘作為魯迅同時期的蜀中“天才學者”,對魯迅及其書是頗為推崇的,他曾向李生惠推薦中學文學史教材,在論及小說時,他說:“說用周豫才之書。”甚至他還將自己所寫《小說裁論》一文進行刪補,與魯迅觀點相同的,就保留魯迅的論述。他說:“其后蔣氏《小說考證》,周氏《小說史略》相繼出。甲子秋,乃取吾書之見彼書者刪之,而惟存其論。”但劉咸炘的某些觀點仍與魯迅有不同之處,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唐傳奇興衰的原因;二是唐傳奇的作品收錄。
一、唐傳奇的興衰
關于唐傳奇的源起,魯迅說:“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認為唐傳奇是承接六朝志怪小說而來,但劉咸炘卻有不同意見,他并不認為唐傳奇是六朝志怪小說的變體,而是一種新興文體。而六朝志怪小說在后世自有發展,比如《前定錄》《稽神錄》等。他說:“傳奇之興,自屬別創,貌雖似承六朝志怪之書,而實則非也。六朝志怪書搜神、冥祥之體,唐世亦有傳者,如《前定錄》《稽神錄》之類。至宋復多,其文體實非傳奇也。”這種看法源于劉咸炘的小說觀。劉咸炘認為小說就是有宗旨、理論不成體系、內容不真實的文學作品。而劉義慶《宣驗記》、王琰《冥祥記》、干寶《搜神記》等書,在劉咸炘看來“其雖意在勸懲,而本以此為征驗,欲生人之信,觀者雖或不信,而作者固以為信,非采取傳說,揚厲文飾以達己意之比也”,即是說從作者主觀上來講,這些書只是如實道來,并不存在虛構的成分,因此不當歸于小說類,而唐傳奇也就不可能承接六朝志怪之書。
至于唐傳奇的興起,劉咸炘與魯迅的看法則是一致的,都認為與“行卷”有關。魯迅言:“顧世間則甚風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為行卷。”劉咸炘則引宋人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八“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后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但兩人不同的是,劉咸炘還提到了唐傳奇所用筆法——“詩賦、駢文”,他說:“據此,是傳奇乃與詩賦同為舉業,故其文用詩賦之法,自詩變為騷,擴為賦,又擴而為七林、設辭、碑頌諸文。駢儷既成,希于一切篇翰,且溢入子、史,今又變擴而為志怪之書。統觀前后,固其勢耳。”言下之意,是說唐傳奇多用駢文寫成,但這個看法并不正確,傳奇作品雖然包含有駢文的因素,但其本身更多的是散文,這也導致劉咸炘在唐傳奇衰落的原因分析上出現錯誤。
對于唐傳奇的衰落,劉咸炘認為是因為古文運動的緣故,他說:“傳奇流派之不昌,乃正因古文之故,其詞旨既多浮薄,為學者所詆,而韓、柳一派日益盛行,至于宋初,遂掩文壇。”劉咸炘認為唐傳奇的衰落是受到古文運動反對駢儷的影響,但恰恰相反,唐傳奇與古文在題材內容、表現手法等方面其實存在著相互影響、促進的關系。至于到宋初時,傳奇掩于文壇,主要是因為當時學者參與類書編纂,無暇小說創作,以及詞與通俗小說的興起等各種因素的影響。
二、唐傳奇的作品收錄
唐傳奇作品的收錄,單篇方面,魯迅有《唐宋傳奇集》,叢錄方面,有《中國小說史略》,但劉咸炘認為魯迅“所取俱甚慎,然猶時有濫者”,且有些作品并未收錄,因此他從單篇、叢錄兩個方面作了考證。
首先,單篇作品方面。這個方面亦可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魯迅收錄,但劉咸炘認為不一定是傳奇作品的,有吳兢《開元升平源》、陳鴻《東城老父傳》、李公佐《謝小娥傳》、李吉甫《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柳珵《上清傳》、沈亞之《馮燕傳》,言《開元升平源》“以傳記為小說也”,《東城老父傳》《謝小娥傳》“二篇皆不甚似傳奇”,《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上清傳》“皆非傳奇”,《馮燕傳》“直非傳奇也”,但劉咸炘并沒有說明原因,推測來看,應當是以上作品多用史傳筆法,文筆簡質,并不符合劉咸炘關于唐傳奇“描寫纖委而文詞艷麗,凡敘事纖則必增,麗則必飾,煒曄揚厲”的看法。如《開元升平源》,“吳兢以史才著稱,此篇在藝術上平平,其敘述方法接近史書”,又如《編次鄭欽說辨大同古銘論》“小說以任昇之與鄭欽悅的兩封信為全篇主體,又以簡要的敘述和描寫進行銜接”。
第二部分,魯迅未收錄,但劉咸炘認為是傳奇作品的,有張說《梁四公記》《鄴侯外傳》,裴铏《鄭德璘傳》。今人朱一玄等編著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就將它們列為傳奇小說,于《梁四公記》言:“全書故事雖然零散,卻能用問答鋪陳的漢大賦結構形式加以連綴……,在文字上將叢殘小語與駢儷文字共熔一爐”,而《鄴侯外傳》寫李泌奇行,敘述詳盡,《鄭德璘傳》多用詩文,情節曲折巧合,這些作品都非常符合劉咸炘的唐傳奇定義。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即作品并不是單篇,而明人叢書多將其列為單篇的情況,這些作品魯迅亦未收入,但劉咸炘也認為是傳奇,包括有蘇鶚《同昌公主傳》、沈既濟《陶峴傳》、陳鴻《睦仁倩傳》、鄭還古《杜子春傳》、楊巨源《紅線傳》、顧飛熊《妙女傳》、許棠《吳保安傳》、宋若昭《牛應貞傳》、于鄴《揚州夢記》、馮延巳《昆侖奴傳》、羅鄴《蔣子文傳》、李景亮《人虎傳》、孫頠《申宗傳》《神女傳》、顧敻《顏氏傳》、孫恂《獵狐記》、蔡偉《魏夫人傳》、于義房《黑心符》。這些作品,除了《神女傳》《顏氏傳》《魏夫人傳》《黑心符》《睦仁倩傳》《蔣子文傳》有爭議外,其他作品基本上都被今人看作傳奇小說。
其次,叢錄方面。叢錄之書,魯迅《唐宋傳奇集》并未收錄,但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此類作品有牛僧孺《玄怪錄》、李復言《續玄怪錄》、張讀《宣室志》、蘇鶚《杜陽雜編》、高彥休《唐闕史》、康駢《劇談錄》、孫棨《北里志》、范攄《云溪友議》、裴铏《傳奇》,又言“武功人蘇鶚有《杜陽雜編》,記唐世故事,而多夸遠方珍異,參寥子高彥休有《唐闕史》,雖間有實錄,而亦言見夢升仙,故皆傳奇,但稍遷變。至于康駢《劇談錄》之漸多世務,孫棨《北里志》之專敘狹邪,范攄《云溪友議》之特重歌詠,雖若彌近人情,遠于靈怪,然選事則新穎,行文則逶迤,固仍以傳奇為骨者也”。
在魯迅看來,唐傳奇的選擇標準有兩個,一是題材屬于志怪類,二是即使不是志怪類,但只要是選事新穎,行文逶迤,也可以算作唐傳奇。但劉咸炘的唐傳奇選擇標準更為狹窄,他說:“記夢、記仙,取材新穎,不必即為小說,惟行文逶迤,乃真傳奇之體。”即只有行文逶迤才能算得上唐傳奇,而內容方面不能作為唐傳奇的選取標準。所謂“行文逶迤”,就是指“描寫纖委而文詞艷麗,凡敘事纖則必增,麗則必飾,煒曄揚厲”。唐傳奇與志怪小說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有意為小說”,但是如何看出作者是否“有意為小說”,則要探求小說文本。文詞艷麗、敘事詳盡、煒曄揚厲的小說即可看出作者有明顯的虛構成分,即作者“有意為小說”。
如志怪小說《搜神記》中的《宋定伯捉鬼》,這則故事雖然內容新穎,情節曲折,但是作者只是如實記錄當時的情形,幾乎沒有描寫的成分,整篇文章如新聞報道一般,很難看出作者有意虛構。而唐傳奇則不然,雖然有些作者也說自己的作品是聽他人敘述,但這類作品仍可看出作者“有意為小說”,如《鶯鶯傳》,這篇作品以細致的外貌、心理、語言、動作等描寫來展示人物性格,文中夾雜詩賦,文辭優美,抒情色彩濃郁,因此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彰顯自己的文才,存在著虛構的故意。
而唐代也有不屬于傳奇而屬志怪一類的作品,如張讀《宣室志》中的一則:
大歷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后且有禍。”尋為官得罪,謫為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為珠可貴,即命人采之,或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誅死。
這則短文雖然是記述靈驗之事,在內容上和唐傳奇相近,但整篇作品平鋪直敘,沒有對事件或人物作細致地描寫和渲染,看不出作者是有意虛構,而是讓人覺得作者將這個故事作為一則新聞來記錄下來,因此這類作品當屬志怪一類。據此,劉咸炘認為:“牛僧孺、李復言、裴铏之作,純為傳奇,張讀與鄭還古《博異記》已有小分,簡略率直,蘇、高、康、范與何光遠《鑒戒錄》則略率更居大半,止小分為傳奇體。”
綜上所述,劉咸炘對魯迅的唐傳奇觀做了更深入的辨析,他認為唐傳奇是有別于志怪一類的一種新興文體,并從辨體角度提出唐傳奇與志怪小說的主要別在于是否“行文逶迤”,即表明如何看出作者有意虛構的方法,然后以此為基礎,從單篇、叢錄兩個方面對唐傳奇的作品收錄進行辨析。這些觀點為今后唐傳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
參考文獻:
[1]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110.
[2]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丁輯[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
[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1.
[4]趙彥衛.云麓漫鈔[M].北京:中華書局,1996:135.
[5]林辰.神怪小說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12.
[6]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7] 張讀著,張永欽,侯志明點校.宣室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