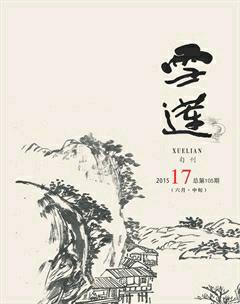“輕”與“重”——《所羅門之歌》中黑人的精神困境
劉華青
【摘 ?要】《所羅門之歌》本是舊約中的一章,是一部歌頌愛的篇章。莫里森將它用作自己小說的名字,描繪了在愛的缺失和扭曲之下黑人的精神困境:內心“輕”“重”失衡,困惑、迷惘,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走出困境。小說借《所羅門之歌》,表達了對黑人出路的思考:只有博愛才能解決內心的“輕”“重”失衡,將其從痛苦中解放出來。
【關鍵詞】《所羅門之歌》;“輕”;“重”;困境
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昆德拉對生命之輕重做了深刻思考: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變得比空氣還輕……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在昆看來,沒有責任意識的生命會“輕”得讓人難以承受,人應該承受生命之“重”。莫里森在《所羅門之歌》中也表述了自己對生命之輕重的看法。和昆德拉一樣,莫里森認為沒有責任、沒有愛的人生會過于“輕”。但是,莫里森看來,生命也不能過于沉重。如果在責任和愛的偽裝之下去做狹隘之事,會讓生命“重”得難以承受。而只有學會正確地愛和承擔,才能獲得心靈的“輕”“重”協調,才能走出痛苦。
一、愛的缺失之下的生命難以承受之“輕”
小說中,梅肯·戴德和兒子奶娃都生活在愛的缺失中。他們就像《不》中的托馬斯,沒有責任意識,過著一種極“輕”的、沒有意義的生活。
在梅肯·戴德眼里,生活就是為了“擁有”。對物質的過分狂熱,讓他將親情、愛情和人情都置之度外。為了金子,他將唯一的親人派拉特看作敵人。他對兒女毫無關心,經常對他們亂發脾氣。他將婚姻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娶露絲是為了她父親的財產和地位。他絲毫不近人情,將交不起房租的黑人同胞趕出房屋;在同胞要跳樓自殺時,他考慮的僅僅是自己的租金。表面上看他似乎成功了,成了最富有的黑人。但是,他活得沒有任何價值可言。作為黑人,即使再富有也不被白人所接受;對同胞的掠奪讓他在黑人中也無法立足,成了黑白之間的“夾縫人”。另外,對家人冷漠的他也難以體會家的溫暖,妻子兒女并不真正尊重他。利欲熏心的他沒有承擔對家人和同胞的責任,過著極“輕”的生活。他“感覺像是局外人”,“孤獨”,那么難以承受。
奶娃雖極力要和父親不同,但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不滿父親的唯利是圖,卻揮金如土,喜歡高檔奢侈品;不滿父親對待家人的方式,但對身邊人極度冷漠。父母的矛盾在奶娃看來和自己沒有任何關系,不僅沒有絲毫關心,反而覺得“似乎一些他不應得的負擔加到了自己身上”。冷漠讓他喪失愛的能力,變得孤立,除了吉他,沒有一個朋友,根本體會不到親情、愛情和友情的溫暖,沒有任何寄托。他感覺迷茫,“就像站在他不該站的角落里,努力想要下定決心要往前還是退后”。這種空虛無聊讓他逐漸難以承受,想要逃離。于是,奶娃南下開始新的旅程,雖沒有找到期待的金子,但找到了更為重要的東西:他找到了自我,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喚醒了對世界和他人的愛。
二、愛的極端之下的生命難以承受之“重”
“七日”是極端之愛的典型代表,他們以愛同胞的名義殺害無辜的白人,但極端的暴力殺戮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內心的平靜,反而讓他們備受煎熬,生命“重”得難以承受。
史密斯是“七日”社團的一員,秘密殺害白人為黑人報仇。同時他還是白人保險公司的代理,通過榨取黑人來為白人謀取利益。關愛自己黑人同胞還是向他們掠奪?代表白人公司利益還是極端向他們復仇?他一直活在矛盾之中,不敢正視自己的同胞:“幾乎全部的時間里,他都將目光集中在客戶的腳上”。這種將對黑人的愛等同于對所有白人的恨的極端做法讓他最終難以承受,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莫里森曾說,“在愛的名義或者偽裝下,人們做著各種各樣的事。暴力也許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的一種扭曲”。“七日”另兩個成員波特和吉他也以愛為名在暴力中苦苦掙扎。波特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對黑人的責任和愛。但這種扭曲的愛讓他很迷茫,為愛而殺戮的邏輯讓他不知何去何從。醉酒后,他企圖像史密斯一樣跳樓自殺。自殺之前,他將自己的痛苦全部釋放,大聲咆哮:“上帝啊,我承擔不了更多的愛啦!我受不了啦!就像史密斯一樣。他承擔不了,因為愛太沉重”。在極端復仇的壓力之下,波特企圖用自殺結束自己的不可承受之“重”。吉他是“七日”最堅定的成員。他曾向奶娃解釋自己的殺戮,“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白人的憎恨,是對我們自己的愛,對你的愛。我的生活充滿了愛”。在他看來自己的初衷是“愛”。奶娃指出,殺戮會成為一種習慣:如果吉他能“殺任何他不喜歡的人,那么有一天也會殺了我”。雖然吉他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會殺黑人,但奶娃的擔心還是應驗了。最后,吉他為了金子一路追殺奶娃,將自己標榜的“愛”和友情全部拋之腦后。在“愛”的名義下,吉他從對白人的盲目仇恨轉移到對同胞乃至對朋友的瘋狂報復,最終將槍口指向了他口口聲聲“深愛”的兄弟。
這種極端的報復方式讓黑人變得瘋狂。莫里森對他們的刻畫表明,借助極端暴力并不能幫助黑人通向自由平等,反而使黑人的生活“重”得難以承受;不僅不能解決種族問題,還會造成種族內部的隔膜。
三、博愛之下的“輕”與“重”之協調
弗洛姆認為:“博愛有利于人類的團結并構成一體,這是基于一種我們都是一個大家庭的這樣一種經驗”。小說中的派拉特算得上是“莫里森所有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中最出色的”,是小說中唯一一位滿懷博愛之心,沒有受到精神煎熬的人物。通過這一形象,莫里森表達了對黑人博愛的期望。在派拉特引導下,奶娃逐漸開始思索人生,喚醒自己心中對他人和世界的愛,“輕”“重”失衡的靈魂找到了歸宿。
派拉特是位善良博愛的黑人女性,她愛他人,愛自然中的一切事物,愛本民族的文化。在她看來,生命是寶貴的。她用愛去化解一切紛爭和仇恨,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用自己對他人的尊重來贏取尊重。她愛家人,露絲懷孕后她極力保護嫂子和奶娃不受梅肯的傷害;即使是敵人,派拉特對他們也充滿憐憫和愛護。小時候和哥哥躲在山洞里,梅肯為了金子殺死白人老頭,但派拉特堅持不同意哥哥帶走不屬于他們的金子,并將這位白人的尸骨隨身攜帶以表歉疚。女兒麗巴受男友傷害,她本可以好好教訓這個男人,但博愛之心讓她選擇了寬恕:“當有人不喜歡自己的孩子,媽媽們會緊張,會受傷……我不想對你多做什么,因為怕你媽媽像我現在一樣傷心”。她熱愛自然,“眷戀曠野,愛嚼松針,愛打光腳,愛在農場和樹林享受無拘束的自由生活”。派拉特過的是一種極其自然原始的生活,不注重物質而是內心的充盈。她深愛本族文化,她將父親當年抄寫自己名字的小紙條放進耳墜里隨身攜帶;時刻謹記父親教會,愛護每一個人的生命;一生都在歌唱代表黑人歷史的所羅門之歌,用愛的實際行動感染同胞。盡管吉他最后將槍打向了派拉特,她依然沒有怨言和憎恨,而是后悔自己沒有去愛更多的人。正是因為她的博愛,派拉特的生命不像梅肯那樣“輕”得毫無意義,又不像“七日”那樣“重”得難以承受,只有她,在愛中實現了飛翔。
在派拉特影響下,奶娃意識到自己人生的毫無意義,開始轉變極“輕”的生活方式。第一次見派拉特,奶娃感受到這位獨立自信的黑人女性的魅力,并在派拉特充滿愛的家里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暖。通過派拉特的講述,他了解了自己的爺爺,意識到家族身份。看到姑姑不顧自己偷金子的荒誕,還想方設法救自己,他開始感到羞愧。派拉特的博愛,讓奶娃開始思考人生,決定離開。南下過程中,奶娃變得越來越有派拉特的影子。他一改往日冷漠,開始和陌生人交流甚至幫助他們;開始像派拉特一樣變得獨立堅定,不再被外界所左右,思索除去外在的物質的東西,自己作為一個最原始存在的價值;在狩獵過程中,他意識到自然萬物的可愛,在語言出現之前的遠古時代,人已經學會了與萬物交流。隨著對家族史了解的逐漸深入,他在為自己身份自豪的同時,意識到根的重要:根是家人共享的東西,可以讓大家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正是因為對過去的了解,他開始理解父母。正是對民族之根的追尋,他像派拉特一樣學會了愛他人,意識到自己對哈格爾所犯下的錯誤。學會愛他人、愛自然和愛民族文化的奶娃 ,“輕”“重”失衡的心靈終于找到了歸宿,靈魂得到凈化和提升。
四、總結
小說中,莫里森描述了掙扎中的黑人的生活狀態,他們或由于愛的缺失,生活得極“輕”,或因愛的扭曲生活得極“重”,而只有博愛的精神——愛他人,愛自然乃至愛整個世界,并且愛自己本族文化,才能將黑人從痛苦中解放出來,找到靈魂的歸宿。莫里森關注的不僅僅是黑人群體,她的作品向人們展示,整個人類只有懷著博愛的精神,才能實現與自己、與他人乃至整個世界的和諧。
參考文獻:
[1]Fromm, Erich. The Art of Loving[M].Ed. Ruth Nanda Anshe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6.
[2]Morrison, Toni. Song of Solomon [M].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2006.
[3]Taylor-Guthrie, Danille.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M]. Jae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4]侯靜華.莫里森黑人女性文學特質及其主體性建構[J].求索,2013(9).
[5]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