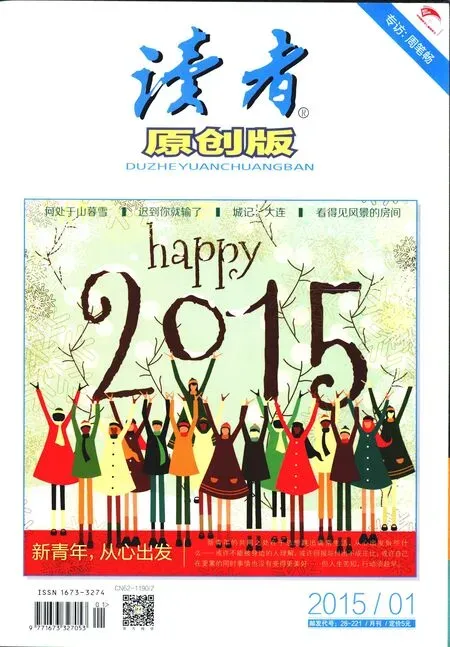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文_任盈盈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文_任盈盈
任盈盈,曾用筆名一盈,出版小說《玉泡泡》《櫻桃錯》《25歲清醒的沉淪》,曾經從事記者、編輯工作,現居加拿大首都渥太華。

渥村不是一個村子,而是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因為人口只有北京市朝陽區人口的一半,故而被中國移民嘲笑為“渥村”。出發之前,我告訴媽媽,在渥村,吃菜需要去自家后院里摘,窗簾需要自己去市場買布,然后踩縫紉機做。超市沒有活魚,實在嘴饞怎么辦?那就劃條船去河里釣吧。
媽媽驚訝:“我好不容易走出農村,怎么你現在又千辛萬苦回農村了?”
在渥太華,老移民總是說:“買房子,如果沒有看到三百套以上,千萬不要做決定。”可是我在看到第三套房時,便已經心動了。
那是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們如約去看房子,遠遠便看到兩棵大楓樹像士兵一樣佇立著,一棵深紅,一棵明黃。前院建了花園,花園內有好幾棵一人高的丁香樹,樹前種著稍矮的松果菊和玫瑰,再矮一點兒的是白色雛菊,貼地遮蓋土壤的則是開著星星點點小藍花的歐石楠。
渥太華有將近半年的冰雪天,也許是因為對春光的無限珍惜,本地人狂愛園藝。看多了私家小花園,我這個“花草盲”漸漸也看出點兒門道,原來種花可不是隨隨便便想種就種,一個合格的花圃要講究視覺層次的組織規劃,還要講究花草在不同月份顏色的搭配,保證一年四季都有鮮花盛開。
眼前這個花園當然不算卓越,但起碼經過精心設計。我已經開始暢想夏天的傍晚,端著冰酒半躺在花園的藤椅上看書的圖景了。當然,沒有想到的是夏天渥太華如同轟炸機般的蚊子,還有冰酒因為甜度太高,在本地可不算討人喜歡。
一
中介Carlo在房間里等著,房主則已經避開。一進門,我們便被花香、音樂以及繪畫作品擁抱了,抬眼便看到幾扇落地大窗,令后花園的風光撲面而來:芍藥濃艷,草皮新綠,藍綠色的雪杉佇立在角落。恰好墻壁被刷成暗紅色,襯托得窗外風景如同上帝的油畫,姹紫嫣紅,自然天成。
我突然想起那部電影—《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壁爐是舊的,屋頂是舊的,地毯爛了一個洞。”朋友看我有些愣怔,趕緊潑冷水讓我清醒,“這幾項加起來起碼得刨去三四萬塊。”
可是,對于剛剛逃離北京霧霾的我來說,多少錢也比不上綠葉一捧。我充耳不聞,只是心若撞鹿地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繼續看。這幢獨立的三層小樓,到處都是極富設計感的窗戶,窗外皆是風景,就連地下室的三個半窗,一扇窗外種著爬行的常春藤,另外兩扇窗外種著薰衣草。
Carlo是個聰明人,她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微笑著說:“Rose說,她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自己的花園。”
Rose就是現任房主了,她是來自英國的一位老藝術家,這滿墻的畫都是她的作品。因為要搬回英國和女兒同住,所以不得不賣掉這幢房子。想到這里,我居然有點難過,這滿園的芳菲,她怎么舍得放下?
二
愛屋及烏,我開始不停地想象Rose。美麗的、優雅的,還是像《塔莎奶奶的美好生活》中的塔莎奶奶,畫畫、做園藝、烤餅干,穿著中世紀的古董衣服?
按照本地慣例,買賣雙方只有簽好合同才有可能見面,很多可能永遠不會見面,畢竟一切由中介、銀行與律師代辦,確實也不需要見面。但合同還沒簽好,我便催著Carlo要求安排見面,理由是“學習如何照料花園”。Carlo說Rose興奮極了,連連表示:“太好了!”
見面那天,Rose穿了一件有精致刺繡的白色襯衫,藍色褲子,雪白的頭發挽成發髻盤在腦后。本以為見面時會有一個熱情的擁抱,但一觸到她冷峻的眼神,我不由得后退幾步,態度也變得矜持起來。
Rose絕少像本地人那樣輕松微笑,表情幾乎稱得上嚴肅,薄薄的嘴唇緊緊抿著。她60多歲,但動作仍然稱得上敏捷有力,微駝的后背倨傲挺直,令我不由得想起伊麗莎白女王,那一模一樣的冷峻表情,還有永遠屹立不倒的姿態。
她當然和女王沒有半點兒關系,盡管房間里掛滿英國王室的照片。她只是一個不算出名的畫家,為了生計,把地下室布置成教室教學生畫畫。她還是一位單身母親,很多年前離了婚,獨自一人供養房子,撫養女兒。如今女兒長大成人,也成為藝術家,供職于英國一家博物館。
“你怎么做到這一切的?”我驚訝地問。
如果說做單身媽媽需要勇氣,那么生活在加拿大,單身媽媽更需要無比強悍的勇氣與能力。即便解決了經濟困難,還要應對惡劣的天氣與繁重的勞動……不說別的,光是冬天鏟雪、夏天割草就足以撂倒一個大男人。更何況,Rose還是一位老人。
她云淡風輕地說:“這沒什么,我只是去建材超市買來工具與材料,換了燈,刷了墻,換了衛生間的水槽與柜子,還用砂紙和油漆調整了樓梯與壁爐的顏色。”
連螺絲釘都不會擰的我只能誠心誠意地贊美:“真了不起。不過雖說別墅居住舒適,但工作量太大,難怪很多老年人選擇住老年公寓,省得維護麻煩。”
沒想到這句話傷害了她。“我還沒有老到那個程度。”她有些慍怒地說,然后大步流星地走進花園。此時正值傍晚,前院花開正好,正午有些耷拉的花朵又精神抖擻地綻放了。蚊子不要命地橫沖直撞,砸得人臉生疼。
我不敢往園子里站,但Rose早已經習慣了蚊蟲,隨手摘下一片樹葉為我示范如何趕蚊子,同時指著水源、各種花草一一講解。這里本是一處接近荒廢的院子,但熱愛園藝的她用手把草拔掉,再用鐵鍬翻地晾曬土壤,然后把牛糞羊糞等有機肥混入土壤中,再開車去園藝店買來堅硬的石頭,按照英國園林風格修建出小花園。
經過數年的精心打理,今日的花園已經草木芳菲。丁香、玫瑰、芍藥、菊花、薰衣草、香草、薄荷……除了觀賞,更多是為了生活需要:薄荷不僅可以驅蚊,還是每日早茶的必要食材;香草除了做蛋糕,泡澡的時候丟進浴缸里,香味比玫瑰還持久;薰衣草風干之后插入花瓶中,是她繪畫時經常描摹的對象;至于香蔥就更不用說了,每次做沙拉時,她多半連鞋子都來不及穿,赤腳跑到花園里摘幾根,因為極其干凈,都不用洗便直接丟進沙拉中……
這便是夢想中的田園生活,表面有多詩意,背后的工作就有多繁重。
“你在英國的新家有花園嗎?”我問她。
“沒有。”她搖頭。
“那你會不會想念這個花園,以及這幢房子的一切?”
她笑了,神情有些黯然:“當然會。但這就是生活,我們總要面對,不是嗎?”
“不一定,”我輕輕說,“我知道你會在英國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還會來渥太華做客,不用住旅館,記得聯系我,你還可以住在這里—你的房子里。”
她有些不相信地望著我,我微笑著向她點頭。我看到淚水漸漸溢出她的眼眶,她張開雙臂擁抱我:“謝謝你,從來沒有一個人這么對我說過。”
三
我并非客套。在我的理解中,房子不僅是港灣,還是橋梁,把所有相同的人漸漸連接起來。但Rose顯然不這么想,或許她認為,房子是一座城堡,你不要進來,我也不會出去,我們各自燦爛。
我給她寫過兩封郵件,均沒有收到回復。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只是聽鄰居說,這位老太太在很短的時間內幾乎賣光全部家當,把繪畫作品、鋼琴以及幾件精致的收藏品打包,漂洋過海帶回英國,開始新的生活。他們說,那是一個很有個性的老太太。
收房那天,人去樓空,整幢房子因為舊人的離去顯得悲哀。廚房的吧臺上擺著一個廣口玻璃花瓶,里面用清水養著一朵從花園摘來的丁香花,下面附著一張用她的繪畫作品印制而成的卡片。“這是一個美麗的家園,我在這里生活了好多年,相信你們也會收獲幸福和健康的未來。”她寫道。
還是那樣的矜持、克制,有著顯而易見的距離。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她的擁抱,還有那一瞬間奔涌出來的眼淚。
Rose的故事已經過去,如今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窗外的風景每天都在變化,唯愿時光與風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