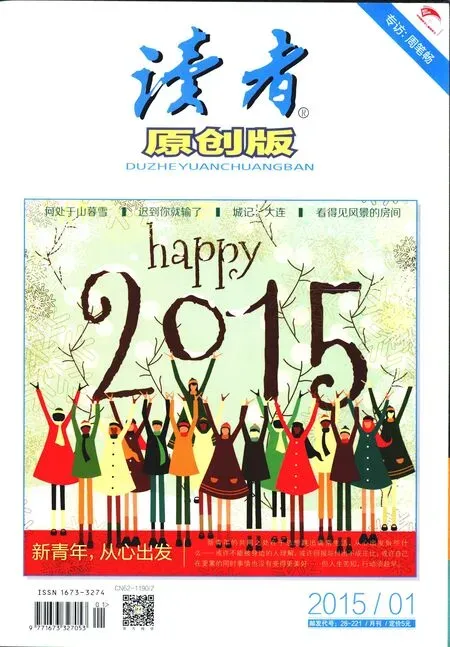木心: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
文_路 明
木心: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
文_路 明
木心,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大師、畫家,出版多部著作。木心先生的畫作曾被大英博物館收藏,他創(chuàng)作的散文與福克納、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國文學(xué)史教程》。一批當(dāng)代著名的畫家、文學(xué)家深受其影響。他的學(xué)生陳丹青說:“木心先生自身的氣質(zhì)、稟賦,在任何時(shí)代都會(huì)出類拔萃。”
一
木心,本名孫璞,號(hào)牧心,筆名木心,出生于烏鎮(zhèn)東柵財(cái)神灣。1937年年末,烏鎮(zhèn)淪陷。當(dāng)時(shí)木心10歲,“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dòng)是不上日本憲兵隊(duì)控制的學(xué)校,家里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xué)齡子弟都來上課”。
木心和茅盾是遠(yuǎn)親,孫家花園和茅盾故居在一條街道的兩端。茅盾到上海做事,在烏鎮(zhèn)留下一屋子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年少的木心手不釋卷,如饑似渴地閱讀,像“得了‘文學(xué)胃炎癥’”。
書讀多了,便開始嘗試著創(chuàng)作。起初是模仿古人的風(fēng)格,“神閑氣定,儼然居高不下”。姐姐和姐夫看了他的詩,兩人商討:“弟弟年紀(jì)這樣輕,寫得這樣素凈,不知好不好?”木心寫道:“我知道他們的憂慮。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凈是不祥之兆,是出家做和尚的。”
他跟一個(gè)女孩子通信,鴻雁傳書三年多,彼此有愛慕之意。三年“柏拉圖之戀”,一見面,一塌糊涂。兩人勉強(qiáng)吃了頓飯,散了回步,“勉強(qiáng)有個(gè)月亮照著”,后來就不再來往。
我忍俊不禁,原來木心年少時(shí)也做過這等事,跟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網(wǎng)戀”“見光死”沒什么區(qū)別嘛。
19歲時(shí),他借口養(yǎng)病,獨(dú)自上莫干山,雇人挑了兩大箱書,其中有他鐘愛的福樓拜和尼采的作品,一個(gè)人住在家族廢棄的大房子里,專心讀書、寫文章。白晝一窗天光,入夜燃白禮氏礦燭一支。有個(gè)鄉(xiāng)下姑娘定時(shí)來送飯,一開始頓頓有米粉蒸肉,頗得少年歡心,到了后來,肉塊變?nèi)馄馄儽。敝敛灰姟D拘恼{(diào)侃,由散文成了五言絕句。
我去過冬天的莫干山,山風(fēng)刺骨,景致荒涼。少年木心的手背起了凍瘡,披一床被子,埋頭寫作不止。從夏初一直寫到第二年雪化時(shí),交出三大篇論文—《哈姆雷特泛論》《伊卡洛斯詮注》《奧菲斯精義》,不為發(fā)表,不求成名。
19歲的美少年,甘心拋下溫柔富貴,跑到山上做一個(gè)苦行僧。我不知道他如何耐得住寂寞,只知他的床頭貼著福樓拜的話:“藝術(shù)廣大已極,足可占有一個(gè)人。”
他去杭州讀藝專,后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回望在美專的那兩年時(shí)光,應(yīng)是木心一生中的黃金時(shí)代—少年翩翩登場(chǎng),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鵝絨西服、白手套的“比亞萊茲”式的裝扮,今日又著黃色套裝作“少年維特”狀。如同一顆10萬光年外的恒星,或許早已湮滅,卻在我們的視野里度著它最好的時(shí)光。
二
1947年,一腔熱血的木心參加了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的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他走上街頭,演講,發(fā)傳單,從大卡車上跳上跳下。“白天鬧革命,晚上點(diǎn)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1948年,木心短暫投奔新四軍,后因此事被當(dāng)時(shí)的上海市市長(zhǎng)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xué)籍,又被國民黨通緝。木心避走臺(tái)灣,直到1949年才返回大陸。后來,他在部隊(duì)中做宣傳工作,因從小患肺結(jié)核,一邊咳血,一邊扭秧歌、打腰鼓。他自嘲是“跑革命的龍?zhí)住保艿煤芷饎拧?/p>
“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在本單位被監(jiān)督勞動(dòng),掃地,掃廁所。他的家被查抄三次,挖地三尺,數(shù)箱畫作、藏書被抄走。紅衛(wèi)兵、造反派輪番搜查,墻壁鑿破,地板撬開,瓦片翻身,連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來用筷子撥拉。全家人被日夜監(jiān)視,姐姐遭批斗身亡,姐夫被關(guān)在學(xué)校的“牛棚”里。木心被囚禁18個(gè)月,折斷三根手指。某夜,木心趁看守不備,從木柵欄里鉆出,逃出后四顧茫然,發(fā)現(xiàn)竟沒有可以去的地方,只得又從剛鉆出的木柵欄里鉆回。
他在白色的紙上畫出黑色的琴鍵,夜夜在這無聲的鍵盤上彈奏莫扎特和肖邦的音樂。“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他在煙紙背后寫,在寫交代材料的紙上寫,夜里沒有燈,就盲寫,前后寫下65萬字,層層疊疊的蠅頭小楷幾乎無法辨認(rèn),藏在破棉絮里帶出來。這65萬字里,沒有聲嘶力竭,沒有血淚控訴,有的只是他對(duì)美學(xué)和哲學(xué)的思考,以及斷斷續(xù)續(xù)寫下的詩。晚年,他說“誠覺世事盡可原諒”,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但不知去原諒誰”。
他曾絕望投海,被追兵撈起后投進(jìn)監(jiān)獄。自殺過一次后,他想通了:“平常日子我會(huì)想自殺,‘文化大革命’以來,絕不死,回家把自己養(yǎng)得好好的。我尊重阿赫瑪托娃,強(qiáng)者尊重強(qiáng)者。”
是藝術(shù)讓他熬過最艱難的歲月。平時(shí)只知藝術(shù)使人柔情似水,浩劫臨頭,才知道藝術(shù)也使人有金剛不壞之心。他說,文學(xué)是他的信仰,這信仰佑他渡過劫難,“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三
1982年,木心旅居美國。在紐約的一幢小公寓里,他以寫絕筆的心情日日寫作,“燃燒,獨(dú)對(duì)雕像,夜夜文藝復(fù)興”,寫出大量的論文、隨筆、小說和詩歌。
20世紀(jì)80年代末,他為一群旅美的中國藝術(shù)家開講“世界文學(xué)史”,從而開始了一場(chǎng)長(zhǎng)達(dá)5年的“文學(xué)遠(yuǎn)征”—從1989年1月15日開課,到1994年1月9日完成最后一講。聽課的人輪流提供自家客廳,一節(jié)課每人收費(fèi)20美元(夫婦算一人)。沒有教室,沒有課本,沒有考試與證書,更沒有贊助與課題費(fèi),不過是在紐約市皇后區(qū)、曼哈頓區(qū)、布魯克林區(qū)的不同寓所中,年輕的藝術(shù)家們圍攏來,聽木心神聊。
“風(fēng)雪夜,聽我說書者五六人;陰雨,七八人;風(fēng)和日麗,十人。我讀,眾人聽,都高興,別無他想。”

他以為今日所有偽君子身上,仍然活著孔丘;他引嵇康為兄弟,推崇屈原是中國文學(xué)的“塔尖”,而陶淵明是“塔外人”;他將杜甫晚年的詩作與貝多芬的交響樂作比較;他評(píng)價(jià)中國古典文學(xué),“兒女情長(zhǎng),長(zhǎng)到結(jié)婚為止;英雄氣短,短到大團(tuán)圓,不再犧牲了”;他說魯迅的幽默其實(shí)黑多紅少,是紫色幽默……
尤其令我感動(dòng)的是木心說起與故交李夢(mèng)熊先生的交往。彼時(shí),“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不久,兩人在徐家匯散步,吃小館子。大雪紛飛,滿目公共車輪,集散蕓蕓眾生,“這時(shí)中國大概只有這么一個(gè)畫家、一個(gè)歌唱家在感嘆曹雪芹沒當(dāng)上宰相,退而寫《紅樓夢(mèng)》”。
這是這個(gè)孤傲了一輩子的人,飄零海外時(shí),偶爾回憶起的溫暖。
后來,陳丹青整理了那5年的聽課筆記,共85講,逾40萬字。這不是一本純粹的文學(xué)史,而是木心個(gè)人的文學(xué)記憶。這是木心留給世界的禮物,也是文學(xué)的福音書。
四
木心對(duì)美有著近乎偏執(zhí)的追求。院子里來了好看的松鼠,他去喂食;不好看,“去去去”。
他一生自詡為哈姆雷特和伊卡洛斯,都是早逝的美少年形象。陳丹青有一次去紐約的寓所看望木心,走進(jìn)廚房,水槽里堆滿幾天沒洗的盤子。陳丹青要洗,木心斷然拒絕,幽然笑道:“哪兒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喬伊斯說:“流亡是我的美學(xué)。”木心自稱不如喬伊斯闊氣,只敢說:“美學(xué)是我的流亡。”
那個(gè)烏鎮(zhèn)的翩翩少年,向世界出發(fā),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晚年終于回到故鄉(xiāng)。
2006年,在孫家花園的廢墟上新建起一座二層小樓,香樟、榆樹環(huán)繞,名曰“晚晴小筑”,那是木心晚年隱居之所。此時(shí),他在烏鎮(zhèn)已無一個(gè)親人。“少小離家老大回”,面目全非的故鄉(xiāng),迎來了雙鬢染白的游子。
貝聿銘的弟子去烏鎮(zhèn),與木心商議如何設(shè)計(jì)他的美術(shù)館。木心笑言:“貝先生一生的各個(gè)階段都是對(duì)的,我一生的各個(gè)階段全是錯(cuò)的。”
少年時(shí)的富家子弟,青年時(shí)的熱血男兒,壯年時(shí)的飽經(jīng)磨難,中年時(shí)的顛沛流離。“我愛兵法,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斷子絕孫。愛情上,柳暗花明,卻無一村。說來說去,全靠藝術(shù)活下來。”一輩子的不合時(shí)宜,一輩子的干凈清醒。
2011年12月21日3時(shí),烏鎮(zhèn)。那個(gè)黑暗中走過大雪紛飛的人,歸去了。
五
木心說,在北京的小酒館里活著零零碎碎的墨子。我也在上海的弄堂里見過零零碎碎的木心。可是木心不再有,他的身世、遭遇、學(xué)識(shí)、見地、對(duì)美的偏執(zhí)、對(duì)藝術(shù)的熱情……這一切,決定了木心的不可復(fù)制。
木心的價(jià)值在于“守”。時(shí)代變革的滔天巨浪中,“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年輕的他也隨波逐流過,當(dāng)意識(shí)到時(shí)代的荒謬和個(gè)人的無力后,“守”便成了他唯一的選擇—拒絕被灌輸,拒絕被裹脅,時(shí)刻把握住自己的舵,“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gè)時(shí)代”。外界如何暴風(fēng)驟雨,內(nèi)心深處始終有一方田園,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那個(gè)年代里,失守的人太多,所以木心彌足珍貴。錯(cuò)過木心,是文學(xué)的不幸;不知木心,是我們的悲哀。
進(jìn)則為魯迅,退則為木心,寫作者當(dāng)如是。
有多少屬于那個(gè)時(shí)代的豪言壯語和海誓山盟,褪色了,被遺忘了,或淪為笑談。到頭來,打動(dòng)人的是這樣的詩句:
清早上火車站
長(zhǎng)街黑暗無行人
賣豆?jié){的小店冒著熱氣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gè)人
圖/劉程民

用微信掃描二維碼,看陳丹青如何回憶他與木心的“文學(xué)遠(yuǎn)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