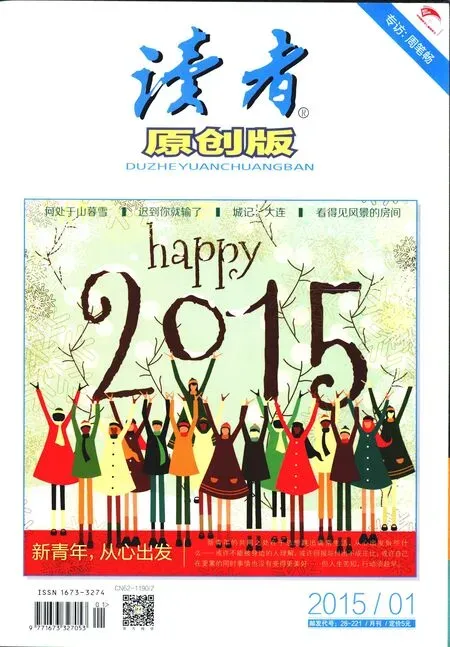打雜者的甜區(qū)
文_草上飛鴻
打雜者的甜區(qū)
文_草上飛鴻

有不少人好奇農(nóng)民工的現(xiàn)狀,他們問(wèn)我們的生活,問(wèn)我們的想法,問(wèn)農(nóng)民工到底是一個(gè)什么樣的群體。整體來(lái)說(shuō),與問(wèn)這些問(wèn)題的人相比,我們的生活和想法也許要簡(jiǎn)單一些,一些陋習(xí)也顯得更加突出,娛樂(lè)生活以及各方面的條件都差很多。但大家都在同一片天空下吃灰塵,我們的現(xiàn)狀也無(wú)非就是生存和利益。
這些有想法的愛心人士,甚至覺得“農(nóng)民工”這個(gè)稱呼不友好,要用個(gè)更好的名詞以示尊重。他們?cè)诟伊奶鞎r(shí)就不停地問(wèn),介不介意他們用“農(nóng)民工”稱呼我。
有人要尊重我,想了解我,要給我所在的龐大群體一個(gè)喜人的標(biāo)簽,我當(dāng)然不介意。
叫我“農(nóng)民工”也好,叫我“不失足”也不錯(cuò)。
—王二屎《不失足》
“80后”王本松竟然給自己起了一個(gè)可能讓有些人不舒服的筆名“王二屎”,“二”就是傻的意思,“屎”就不用解釋了。
這個(gè)名字也許跟王本松賴以謀生的工作有關(guān),他是個(gè)一天到晚在工地上打雜的人:刷墻、搬磚、提水、攪拌混凝土……他一度看不到翻身的希望,因?yàn)椴还茏鍪裁矗娴闹鲬?zhàn)場(chǎng)似乎永遠(yuǎn)在工地上,只不過(guò)一陣兒在長(zhǎng)沙,一陣兒在張家界。人隨著項(xiàng)目走,等建筑物拔地而起,自己好像又矮了一點(diǎn)兒,被流浪的大風(fēng)吹往另一個(gè)工地。
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工友們喜歡隨地吐痰,喉嚨里有痰時(shí)吐,沒痰時(shí)也吐,高興時(shí)吐,不高興時(shí)也吐;吃飯時(shí)大聲說(shuō)話,說(shuō)著說(shuō)著甚至?xí)叵饋?lái);大菜盆里放著“公筷”,但是沒有人用,每個(gè)人到盆里夾菜,用的還是自己的筷子……他們舍得流汗流血,舍得被蚊蟲叮咬,舍得用嬉笑和臟話掩藏內(nèi)心的孤獨(dú)寂寞,卻舍不得吃喝穿戴,舍不得坐公交車,舍不得在口干舌燥的時(shí)候買一瓶礦泉水。年輕的王本松曾經(jīng)問(wèn)工友們留著錢干嗎,他們說(shuō)要回家蓋房子。白領(lǐng)里有“房奴”,農(nóng)民工里也有,而且更加令人唏噓。
王本松和工友們相互嫌棄、戒備,可是這樣的工地又讓他們變得毫無(wú)差別。也許只有離開工地,改變農(nóng)民工的身份,才能成為另一個(gè)自己,但是誰(shuí)敢說(shuō)離開工地就能活得更好?工地上永遠(yuǎn)不可能花團(tuán)錦簇、鳥語(yǔ)花香,有時(shí)候連一點(diǎn)兒綠意都見不到。從沮喪到苦悶,王本松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jīng)有些老態(tài)龍鐘了。他有些絕望地說(shuō):“我找不到比這里更適合自己的地方。”他甚至苦澀地愛上了工地,不管它讓人變得多么模糊、符號(hào)化和原子化。他的理由竟然是:“(工地)多骯臟啊,但是多自由啊;工友們多愚昧啊,但是多真實(shí)啊!”
在這里,王本松交不到朋友,他想說(shuō)的話只能統(tǒng)統(tǒng)咽回肚子里。靦腆的他也很難得到愛情。他曾經(jīng)和他愛慕的姑娘坐在電影院里,人家在看電影,他卻在痛苦地嗅著自己身上的氣味,那件衣裳已足夠干凈,但是他總覺得它散發(fā)著水泥味,他始終認(rèn)為自己還待在工地上。
歇工的時(shí)候是王本松最無(wú)聊的時(shí)候。他慢慢地看起了小說(shuō),不是武俠,也不是言情,甚至不是時(shí)髦的穿越、玄幻,而是王小波、韓寒、卡夫卡、馬爾克斯等人的作品。做包工頭的姐夫大概從王本松身上看出了一些書呆子相,說(shuō)他不務(wù)正業(yè)、沒出息,還嘲笑他是異想天開的傻子—這樣看書能娶上老婆嗎?他沒有爭(zhēng)辯,還有什么誤解、歧視和委屈不能忍受呢?在外面,他無(wú)法活得跟其他工友不一樣,但是他想由著自己的性子在內(nèi)心里活出一點(diǎn)兒是一點(diǎn)兒,不讓生活單調(diào)得只有水泥色。他想讓自己的內(nèi)心泛出微微綠意,品味出人生的絲絲甜意,也許只有書籍能夠幫助他,甚至幫他多出一些反抗的力氣。
書看得多了,不知不覺地,王本松從內(nèi)心深處涌出了表達(dá)自我的沖動(dòng)。他想寫作,靠一個(gè)一個(gè)漢字將憋在生命里的血腥味吐出來(lái),血腥味里面還有他滄桑的青春和孤苦的夢(mèng)。當(dāng)姐夫看到王本松開始用手機(jī)寫小說(shuō)時(shí),嘲笑變得更加露骨了。王本松忽然明白姐夫一直在試圖“控制”他的人生,他默默地反抗著,用最深沉的行動(dòng)進(jìn)行“反控制”。他說(shuō):“我沒想通過(guò)寫作改變什么,只是,如果可以干點(diǎn)兒搬磚以外的有意思的事,我為什么不能干呢?”
他終于將寫作變成一種生活習(xí)慣,每天下班后會(huì)先洗個(gè)澡,然后躺在床上,用手機(jī)寫一兩個(gè)小時(shí)。很多時(shí)候,周圍太吵鬧,他煩得一個(gè)字都寫不出來(lái),但是他還是愿意忍耐著,盡量多寫一點(diǎn)兒。實(shí)在不能寫,他就到外邊跑上10公里,等工地安靜下來(lái),再回來(lái)舉著手機(jī)寫自己的小說(shuō)。生活就是這樣,有憎惡得恨不得逃離的地方,也有值得回歸和堅(jiān)守的地方。
王本松在《你好美呀,請(qǐng)等一等》中寫道:“但命運(yùn)安排我在另一個(gè)地方服刑。沒有女人,沒有一切,那兒只有一群停止干活和賺錢就會(huì)虛弱地死去的精神病和一堆停止運(yùn)轉(zhuǎn)就會(huì)很快冷卻的機(jī)器。”
事情的轉(zhuǎn)機(jī)是王本松用手機(jī)下載了韓寒的電子雜志,當(dāng)然,他不會(huì)僅僅滿足于當(dāng)一個(gè)忠實(shí)的讀者,他已經(jīng)多少有些信心向它投稿了。韓寒是王本松的偶像,成為偶像創(chuàng)辦的電子雜志的作者會(huì)讓他很快樂(lè)。他的第一篇小說(shuō)《天仙配》是在長(zhǎng)沙一間潮濕悶熱的工棚里寫出來(lái)的,也是在一股股腳臭味和煙味中寫出來(lái)的。躺在床上,舉著手機(jī),2000多字的處女作,他花了兩個(gè)晚上。小說(shuō)寫成后還沒有題目,有個(gè)工友打牌時(shí)和了,大喊一聲:“天仙配嘞!”對(duì)方的煙灰抖落在王本松的腳指頭上,他嘿嘿一笑,就這樣有了小說(shuō)的題目。這篇小說(shuō)用自嘲的口吻,像一把小刀那樣刻畫了農(nóng)民工真實(shí)又殘酷的青春,文章發(fā)表后,韓寒給王本松寄了稿酬。王本松拿著錢,在最熟悉的外貿(mào)店門口來(lái)來(lái)回回走了20多趟,最終卻沒有進(jìn)去,他不敢隨便地花掉它。幾個(gè)小時(shí)后,他喝醉了,癱軟在工地附近的河邊。后來(lái),他回憶說(shuō):“生活跟夢(mèng)境一樣。”
這篇小說(shuō)難道不是從工地的水泥里生長(zhǎng)出來(lái)的一株植物嗎?它嘗起來(lái)肯定是苦澀冷硬的,但是畢竟還有一點(diǎn)點(diǎn)甜美—再殘酷的文學(xué),其中也必有隱秘的甜美,那也許叫作“希望”,有人把“服刑”般的青春寫出來(lái),這本身就是一種希望。只是不知道水泥中長(zhǎng)出的植物叫不叫“甘蔗”—它多少甜了作者自己,我們就叫它甘蔗也沒有什么。
后來(lái),王本松又陸續(xù)發(fā)表了幾篇文章……他突然意識(shí)到自己成長(zhǎng)了,成長(zhǎng)的含義是他對(duì)自己產(chǎn)生了滿意感,體現(xiàn)在寫作上,滿意的標(biāo)準(zhǔn)是“得跟別人寫得不一樣”。哪怕只有這為數(shù)不多的幾篇小說(shuō),我也認(rèn)為王本松已經(jīng)活得跟其他的農(nóng)民工不一樣,跟其他的年輕人不一樣。至于他能不能成長(zhǎng)為不一樣的“綠巨人”,我還不知道,但至少知道他終于找到了自己內(nèi)在的“甜區(qū)”,在水泥里種出了幾根甘蔗,這是他獻(xiàn)給青春和整個(gè)世界的綠意以及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