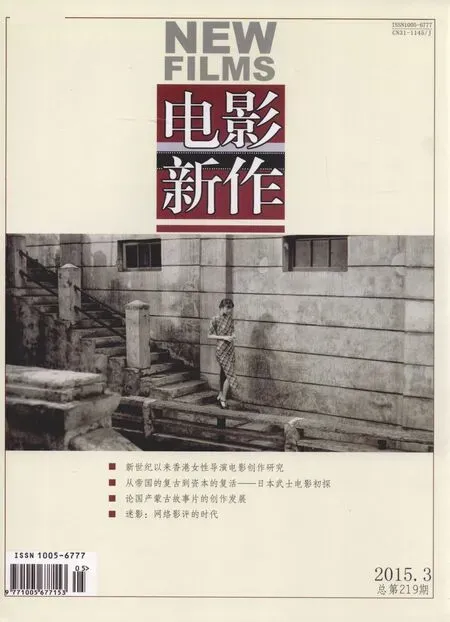如何“女性”,怎樣“中國”?——新世紀以來香港女性導演電影創作研究
聶 偉
一、引言
新世紀以來,中國內地一批女性導演的電影創作令人矚目。李玉、徐靜蕾、趙薇等青年導演的作品均在內地市場取得較好的票房,海外影展獲獎屢有進項①,而李少紅、胡玫、彭小蓮等成名已久的導演亦偶有佳作面世。她們著力描寫都市化進程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存狀態,有的則將都市白領的職場婚戀與商戰故事描寫得時尚而趣味橫生。無論將鏡頭聚焦于何處,上述導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還原當下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冰山一角。
相比之下,曾經歷盡輝煌的香港女性導演創作近年來大都相對沉寂。她們攜帶自己的作品一路北上,其作品往往被淹沒在同期開畫的其他影片中,回聲參差,幾近慘淡(參見表一數據)。
是她們一直以來標榜的女性身份成為束縛自由表達的絆腳石,還是她們致力發掘的影像美學與內地觀眾市場的接受存在先天的差異?本文選取新世紀以來最具代表性的五位香港女性導演——許鞍華、黃真真、區雪兒、黎妙雪、麥曦茵,著重分析其創作風格嬗變。

表1.香港女性導演部分代表性作品網絡評分情況②
上述五位導演近年來在內地院線都有新作上畫,其中許鞍華是“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之后繼續在新世紀進行旺盛創作的代表;黎妙雪入行已久(1989年),但在新世紀(2001年)才正式執導第一部劇情長片《玻璃,少女》;黃真真和區雪兒身為后輩,都有留學紐約學習電影制作的海外背景,接受了先進電影制作理念的熏陶,學生時代作品受認可后回到香港投身創作;而長期與彭浩翔合作的麥曦茵,以其畢業習作《他·她》獲得第12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公開組金獎,此后執導《九降風》的香港版本《烈日當空》,成為香港歷史上執導長篇電影中年齡最小的導演,亦為新生代香港女導演群體的佼佼者。
二、如何“女性”?
既然將研究限定在新世紀的時間維度和香港的空間場域內,CPEA的簽署及其后續影響就成為了首當其沖的話題。CPEA對于整個香港地區電影創作與發行的影響,勢必會波及到女性導演的創作,而她們的創作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后發生的變化與否便是一個有趣的切入點。而另一方面,欲分析女性導演的作品特質,自然會將它們擺在與之相對的“男性”之對立面作研究。在世界范圍內,電影導演的性別比例相當懸殊,這就注定了女性導演在進行創作時帶有某種先天的特殊性,尤其當這五位女導演的作品是在中華文化圈的整體影響之下時。因此,關于這些影片的風格解讀,都繞不開與女性特質相關的話題。
一般來說,女性影像敘事會以兩種方式呈現:一是刻意標榜自身的女性身份,打破原有兩性關系的陳舊觀念,彰顯其獨有特征,將女性置于平等對立的一方;二是直接填平男女性別的鴻溝,徹底消解“男性與女性”這一組對立的關系,從而捍衛女權意識。下文將以導演個案作為切入點,探討其女性影像創作的講述方式。

圖1.許鞍華電影代表作打分情況柱形圖
由上圖可見,許鞍華的創作一直以來維持在比較高的水準。有趣的是,《玉觀音》應該可以算作CPEA簽署后許鞍華北上創作的第一部作,面對新的市場訴求,加之有電視劇版的珠玉在前,影片并不成功。在性影像呈現方面,許鞍華遵循了某種近似于“無性”的創作觀念——她從不刻意強調女性身份以博取眼球,從“新浪潮”時期的作品《投奔怒海》(1982年)起,陽剛硬氣的美學風格一直延續至今,也沒有隨著周遭市場環境的改變而調整。表現在劇情設置方面,兩性關系并不主動被構設為二元對立結構,男性常常以菲勒斯缺席的方式反證女性的成長。典型代表如《得閑炒飯》(2010年),其核心議題聚焦在周慧敏和吳君如扮演的一對女同身上,男性則置身鏡頭后景處,成為女性敘事的背景和陪襯;《桃姐》(2012年)重在講述著名制片人對家中年長保姆的呵護和關懷,相比劉德華飾演的旁敘人,飽經風霜、風韻不存的桃姐反而成為第一主角;及至《黃金時代》(2014年),儼然新世紀華語影壇不可多得的女性主義純自傳式敘述電影。

《桃姐》劇照
黎妙雪的創作與此相仿,《戀之風景》(2003年)講述一位失去男友的女性重獲生存信念的故事,在這部較早在內地獲得放映資格的影片中,代表過去的另一半(香港演員鄭伊健飾演)和代表現在的另一半(內地演員劉燁飾演)共同扮演了這位女性個人成長引路者的角色。他們存在的意義,似乎僅僅止于幫助林嘉欣飾演的曼兒找回女性主體意識。而懸疑片《情謎》(2012年)中,真正的主角也非戲臺上一唱一和的一對戲夢男女,而是由舒淇一人分飾兩角的惠香、惠寶“兩生花”。余文樂飾演的男友穿梭在兩位女性中間,出場伊始就被扁平化為一個“兩邊倒”的“搖擺人”,其存在對女性并不構成任何本質意義上的威脅。
許鞍華和黎妙雪對女性電影的理解,在此固定的視角上已漸成敘事套路。她們似乎獨立于市場的激烈競爭之外,于閑庭信步間安然地完成了自己的創作,波瀾不驚地重復著固定的母題。這種固守看似淡然,卻需要相當的執著。

圖2.黃真真電影代表作打分情況柱形圖
相比之下,黃真真對女性意識的關注與表達在其創作的初始階段中展露得淋漓盡致,其后又經歷了微妙的轉折。如圖二所示,相比許鞍華,她的作品大概緣于內容和形式的雙重特殊性,其觀眾接受度要更低一些。研究其創作歷程,即便暫時擱置圍繞影片的內容爭議,僅就結構而言,可以發現導演一直試圖擺脫傳統電影的固有秩序——我們也許可以將這種秩序看做一直以來統治電影創作的男權制度的某種表征。具體來看,經典電影一般都是以情節推動敘事,尊重線性的故事發展邏輯。而黃真真自成名作《女人那話兒》(2000年)開始,就在竭力摒棄這種常規。這部主要由訪談拼接而成的“偽紀錄片”(其中也穿插了部分搬演的虛構場景),非但很難在傳統劇情片的范疇找到解讀入口,即便用紀錄片的常態模式來比照,也很難在導演隨性而為的鏡頭組接中,找到任何可資借鑒的先例。而在內容上,《女人那話兒》及其續作《男人那話兒》,均毫無遮攔地挑釁著傳統的兩性關系認知。導演敏銳地捕捉到香港多元的文化生態,將形形色色的邊緣人物編織入她的香港文化拼圖里。言談中,被訪者對港島居民的家庭倫理以及性服務場所的描述,將觀眾針對香港社會生態的思考直接置于“性文化”的大語境中。在這個過程里,通過對談,將原本“男人/女人”與“獵人/獵物”的對位關系徹底反向逆轉。她將拍攝團隊的成員全部統一為女性,為的是引導女受訪者(其中包括從過氣艷星到女電影導演,從閨中密友到性工作者的各個階層)肆無忌憚地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談論話題尺度之大,用語之無下限,令觀眾瞠目結舌,由此這兩部作品在香港直接被歸為三級片。
在黃真真此后的商業劇情片嘗試中,雖然大多數時間她依舊不甘于“安守本分”地地講述一個標準套路的愛情故事,但面對大眾市場,導演的創作姿態已經大為軟化,其強烈的女性意識在博弈與妥協中被逐步稀釋。典型案例如《傾城之淚》(2011年)這樣典型的“北上”試水內地市場的“純愛電影”。一方面,作為原來反傳統敘事結構的延續,《分手說愛你》(2010年)和《傾城之淚》都開辟出多元化的敘事空間:前者將導演本人拍攝的故事和銀幕空間內部情侶的情感鬧劇,依靠網絡與電影創作雜糅在一起,以互文本的方式在銀幕內外不斷碰撞火花;后者雖有粗制濫造之嫌,卻也嘗試以割裂的三段式敘事結構,破壞傳統的敘事體驗。而另一方面,與此前在影片中公然挑戰男性社會規則相比,這種三段式的嘗試和碎片化的敘述嘗試,都顯得過于平庸,缺乏銳氣。再看與《分手說愛你》風格極為相似的《完美嫁衣》(港版名為《抱抱俏佳人》,2010年),兩位女主演都不是傳統的“花瓶”:二人都擁有較高的學歷③,身兼影星、歌手兩棲身份,外形都談不上精致,也鮮有可供男性窺視的曲線身材。片中不乏女主角掌摑男演員或男演員自殘的鏡頭以彰顯女權,且女主角完全脫離了先前經典影片中那種被動的從屬地位,游走于幾位優秀的男性中間,掌握著選擇愛情的權力。然而這些流于表面的女權敘事,漸漸淪為市場營銷的噱頭,以扭捏之態迎合了大眾市場對夫權主導的核心家庭倫理敘事的觀影需求。

《分手說愛你》劇照
再看區雪兒的創作,目前其主要擔綱的兩部作品《明明》(2007年)《東成西就2011》④(2011年)都在內地獲得了公映機會,對于僅有這“一部半”作品的導演來說,在作品中顯示出其音樂方面的造詣。早先拍攝上百部MV的經驗讓其作品的影像幾乎成為了音樂的物像性外現符號,其故事情節的敘事推動力常常基于女性感性化的跳躍式思維。《東成西就2011》里大量經典音樂的“破壞性”使用,極具顛覆性,將影片的非理性推向極致。如果說結構上的創造力顯示出年輕導演的美學創新,那么其敘事內容對女性話題的指涉,則進一步彰顯了影片饒有趣味的女權文化特質。在區雪兒擔任音樂導演的《東成西就2011》中,雖然有一眾主流女影星加盟,也但導演的出發點顯然在于戲謔而非窺探,直接隔絕了勞拉·穆爾維所指稱的“視覺快感”:一方面其內地公映版本通篇使用四川話對白;一方面女性明星的銀幕形象頗為邋遢骯臟,具有明顯的去性化色彩。
無論堅守還是妥協,無論激進還是溫婉,上述女性導演的女性敘事遵循著各自不同的軌跡,呈現了香港地區女性導演創作之冰山一角,其他女性導演同樣以各自的方式昭示女權,而正是這種多樣性,構建了香港女性電影五彩斑斕的風景線。
三、怎樣“中國”?
以銀幕形象呈現中國故事,基于不同的地域社會文化土壤,內地導演與香港導演的敘事視角自然會存在相應的差異性,由此形成關于中國故事的對照閱讀。如果說,李玉、徐靜蕾等青年導演的成功都在于以女性視角呈現了一種立足內地想象中國的銀幕敘事,那么,這些香港導演也不可避免地攜帶獨特的地域文化記憶來編織中國故事。如同一枚萬花筒,不同的觀察視角折射出迥然不同卻五光十色的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與精神生態。有趣的是,這批香港女性導演鏡頭中的中國故事,大都聚焦于東部地區(見圖三),對中西部地區幾無涉獵,由此呈現的“中國意象”具有奇特的限定性。

圖3.香港女導演鏡頭中的故事發生地
《戀之風景》中,黎妙雪嘗試用一條尋找記憶的線索將兩地勾連,這是合拍片在啟動階段相對比較保險的做法。《戀之風景》屬于CEPA規則制定后較早完成的合拍片,與那些僅有演職人員參與合作、情節卻互不相關的合拍片(如許鞍華緊隨其后的作品《玉觀音》)不同,影片講述來自香港的女孩到青島找尋已故男友記憶的故事。影片可以視為香港女導演初窺內地的一個暗喻:在現存有限的文化記憶資源下(曼兒男友的日記),對并不了解的內地社會歷史(男友長大的地方)進行一次執著的尋根。于是,一方面,影片呈現出和諧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世界,一方面,淳樸的民風為這雙初次審視內地的眼睛鍍上了一層柔光,仿佛一切都是建立在單純女孩的視野與想象之中。我們注意到,片中多次出現漫畫家幾米風格的動畫和實景,整個故事都浸潤在漫畫式的幻境里,將曼兒的經歷凝結成一種東方式的哀婉情節劇,節奏舒緩,意境憂郁。在此過程中,尋找的目的已不再重要,尋找的過程才是實質。這種想象也許呈現了某一特定地區中國小鎮特殊的文化風景線(包括現下已幾乎不復存在的“登瀛梨雪”),但終究與中國內地更加多元立體的全貌擦身而過。
如果說黎妙雪的想象僅僅是一個純粹夢境的話,那么如同此前的寫實主義題材一樣,許鞍華的創作則更加深邃地指向中國的社會現實,只不過這一次是把攝影機從地理空間狹促的香港半島搬到了廣袤的神州大地。在《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中,她直接割舍了香港的牽絆,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對內地的描繪。細看影片囊括的敘事空間,連貫了典型中國南方都市上海和典型的中國東北地區老工業重鎮鞍山。在這里,許鞍華嘗試用笑中帶淚的方式,執行內地“第六代”導演擅長的敘事——“后新時期”處于急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稍有不同的是,許鞍華選擇的視點不是社會邊緣地帶的小偷,也不是四處閑蕩的無業游民,而是一位有著神秘歷史的滑稽角色——姨媽葉如棠。片中,代表老舊知識分子形象的姨媽與五光十色的現代生活對撞,在一次又一次的希冀中重重地被現實撞醒,內中的各種不適折射出轉型時期中國階層的陣痛。然而,如果我們深究其中關于講述“中國”的方法,會發現許鞍華能夠較好地駕馭這個故事的原因之一在于,作為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城市,鞍山本身太具有符號性,其歷史沿革和地理特征很容易借助影像經營出來。鞍山在整個故事中發揮的作用,不過是承載姨媽歷史記憶的“原鄉”而已,此間與上海的都市繁華產生了巨大的美學落差與心理距離,很容易令人信服。
相比之下,黃真真的《傾城之淚》,撇開其海報創意和故事內容上對權宗冠導演的韓國電影《悲傷電影》(2005年)的“借鑒”不談,影片本身呈現出的“中國”想象早也已被全球化語境下同質化的都市景觀席卷而空。《傾城之淚》所“傾”之“城”,可以是當下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任何一座城。影片中的“東方巴黎”若不是被抓取了些許外灘夜景的鏡頭,在普通觀眾看來,已與真正的巴黎無異。
再看麥曦茵的創作。此前與彭浩翔的合作中,麥曦茵幾乎成為了他的“影子寫手”,作為《春嬌與志明》的編劇,將彭氏喜劇的精髓納入自己的寫作風格中,通篇充斥著辛辣的言語和機智的橋段,但也兼有女性作者心思的纖細和敏銳。這種“女版彭浩翔”的寫作方式與她在2008年推出的影片《烈日當空》(被譽為香港版本的《九降風》)異曲同工。作為一名極為年輕的女性導演,她嫻熟地掌控了一出專屬男性青春的群戲,捕捉到一群青春叛逆期在讀中學生的成長轉折與心理陣痛,將青春的荷爾蒙化作“男性化”敘事的利器,如入無人之境般挑戰著青春片的底線。相比之下,進入內地市場后,《前度》(2010年)與《華麗之后》(2012年)無不別扭地完成了從叛逆女青年作家到資深情感女作家的蛻變。這兩部影片更多地回歸到一般女性導演所擅長的情感糾葛,著力刻畫女性之間的嫉妒與爭風、女性在男性周遭的游蕩與尋覓,以及注定無果的情感追逐等,幾乎都是都市白領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情感命題。遺憾的是,這些典型的女性題材雖能頻頻觸碰到當下都市白領的精神世界,但與早期狂放而略帶野性的講述風格相比,終究是中規中矩的中成本制作,反響平平。顯然,對于麥曦茵的創作來說,拓展內地市場的“北上”之渴望稀釋了原先的女性張揚特質,最終令其作品難寫其心。
無論試圖在香港和內地之間設置連線,還是斜線貫穿內地地區,我們看到,香港的女性導演們實際上始終游蕩在中國版圖的東部海岸線,就像《戀之風景》中的曼兒期待著了解內地背景的前男友身世一樣,她們渴望叩開內地市場之門,擁抱內地消費力強大的主流觀眾,然而其講述的對象卻始終在兩個物理空間的夾縫中徘徊。這些對象要么與香港存在類似地理上或文化上的相似點,要么本身只是一個想象式的符號。

《華麗之后》劇照
先看許鞍華,從《女人四十》(1995年)《男人四十》(2002年),到《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年)《桃姐》,導演一直試圖在傳統的東方倫理和中國哲學中尋找解決香港當下問題的方式。《女人四十》記錄了年過四十的家庭主婦在處理生活中接踵而來的不大不小的麻煩時的沉穩與淡然,女主角孫太阿娥在孝文化的感召下,不得不照料突然變為癡呆老人的公公,并主動擔負起整個家庭的重擔。而《天水圍的日與夜》與《桃姐》一樣,許鞍華嘗試運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代替了法律或者社區制度上的責任,將老一代城市居民的生存困境問題溫情地安頓下來。無論是《天水圍》中的阿貴,還是《桃姐》里的桃姐皆為女性,她們都本應是香港飛速運轉的現代機器代謝出的“冗余物”,但卻又是確鑿實在的肉身組成部分,她們的生存信念,是周遭生活賦予她們的樂觀。在沒有西方式的制度保障下,他們依然可以作為獨立的女性,如前一樣欣欣然地過活。由此可見,許鞍華電影中的香港,是對中華文化的某種傳承與擁抱。
這種東方式的傳承也可以在區雪兒的《東成西就2011》中找到聯系。影片提及的困境來自當代人對愛情的恐慌和不知所措,而導演用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方式,將這種迷局構架為天神之間的沖突和爭奪導致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奇形怪狀的天神們絕非西方宗教世界中的基督,而是典型的東方神——天龍八部,包含一天眾、二龍眾、三夜叉、四乾達婆、五阿修羅、六迦樓羅、七緊那羅、八摩呼羅迦。于是一個原本世俗的故事升華為東方諸神的幾世輪回,其答案也出現在影片結尾時頗具禪意的頓悟里。更有趣的是,在傳統的設定里,阿修羅本應是男性極丑陋,女性非常美麗,但片中導演將演員莫文蔚刻意地扮丑,而正是由她,作為一個看似癡情懵懂的普通“少女”,完成了對迷途的夜叉的拯救,儼然一次女性地位的反轉。
肉體上意欲進入內地而不得,轉而返回香港,在精神上尋找東方式的敘事通道,組成了當下香港女性導演創作的普遍選擇。而各類合拍片的日漸興盛,保證了這些嘗試無功而返的概率會隨著合作模式的逐步成熟而緩緩降低。與此同時,在內地與香港之間去去來來的過程里,女性導演的經驗也在不斷地積累,相信將來會出現一幅具有更多面向,散點更均勻的中華文化地形圖。
與內地的主流女性導演相比,香港的女性導演的生存處境更加艱難,她們大多與浮躁的媒體絕緣,鮮見于炒作的風口浪尖,其中又以許鞍華為最。她們著力拍攝可以承載個人藝術追求的作品,并注入個人對于新世紀中國的想象。無論是固守東方倫理,還是借鑒西方思潮,她們的作品中都散發著迷人的女性魅力。也許在商業上暫時難以突圍(《桃姐》是唯一的例外),但對日漸衰微的華語女性電影來說,卻是一條自我拯救的出路——畢竟她們從未放棄努力描述她們對于當下中國乃至華語世界的想象。
【注釋】
①《蘋果》獲得2007年第五十七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提名,2007年第六屆紐約翠貝卡電影節劇本榮譽獎等;《觀音山》獲得第二十三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麒麟獎提名,以及最佳女主角獎、最佳藝術貢獻獎等。
②該評分數據截至搜集于2015年4月30日。
③楊千嬅畢業于香港理工大學,薛凱琪則畢業于香港城市大學。
④影片導演是劉鎮偉,區雪兒在其中擔當音樂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