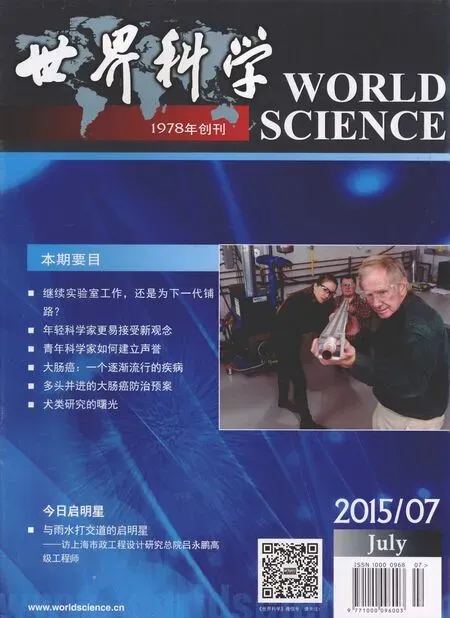當我最后一次望見群星
姚人杰/編譯
當我最后一次望見群星
姚人杰/編譯

●《當我最后一次望見群星》通過奶奶與孫女之間的一場對話,講述了一則發人深省的故事。莫非真的要等到喪失后才會懂得珍惜?相信讀者在讀完之后定會有今晚好好看下夜空的打算。
“我有條其他人都不曉得的消息,”我告訴奶奶,“我答應過會頭一個告訴奶奶你。”
“好嘞,小海倫。你一直是奶奶的乖孫女。”奶奶說道。父母稱呼奶奶為“大海倫”,因為在我小時候,奶奶比我高很多。現在的我長得與奶奶過去一樣高,可是奶奶如今卻蔫巴了,虛弱得站不長久。
“記得月球再過去的地方那臺新造的太空望遠鏡嗎?它龐大強勁,能看見其他恒星旁邊的行星。我用它見到了一些新東西。”那面30米口徑的鏡片能觀察到遠處的紅外線波段景象,地球這樣的星球會在紅外線波段下因自身的熱度而發光。我以前告訴過奶奶,但奶奶104歲了,記不清楚細節。
“你以前就告訴過我這些事。小海倫,當我最后一次望見群星時,你還只是個小女孩。”
我那時沒那么小。我那時候有12歲了,到緬因州鄉村的避暑木屋里探望奶奶和爺爺。我們很晚都沒睡,關掉所有電燈,到了屋子后面的開闊場地。我們躺在舊的鋁質休閑椅里,見到整個宇宙攤在深邃的黑色夜空中。爺爺指出了銀河,還把他那只大大的雙筒望遠鏡遞給我,讓我仔細看。當我調好雙筒望遠鏡的焦距,那片朦朧的夜空變成了越來越多的星星,那一刻的我陶醉入迷。
“星星美極了,”我告訴奶奶,“我仍然記得那一幕。它讓我想要當天文學家。”我記起那是多么久以前的事,不由感激起醫學的奇跡,是醫學奇跡使得奶奶比她的祖父母多活了二十年。
“小海倫,你記得我那時告訴了你什么嗎?”
“關于銀河的話?”
“不,不,”她說,“是說我們永遠沒法再像那樣看星星了。全球第一項地理工程學工程是在天空中擴散霧霾,從而降低地面氣溫。你沒注意到,但我們那時早已能在夜空里看見散射光,仿佛城市的光線已經照到了我們的鄉村木屋那兒。”
“我們從太空望遠鏡能更清楚地望見星星,比從地面看更加清楚。”我告訴奶奶,“那兒沒有空氣擋道。”
“我想要抬起頭看見滿天空的星星,小海倫,”奶奶說,“我這么多年沒見過星星了;到處都有霧霾和光線。”
“奶奶,我們需要這種地理工程氣霧劑,”我說,“它們是我們控制氣候的唯一辦法,能讓氣候不會變得太過暖和,避免南極洲和格陵蘭島剩下的冰山融化。”
“我們可以停止燒煤,”奶奶說,“我記得政府那時候討論停止溫室氣體的排放,不再整夜開著道路、高速公路和室外的燈光。我們稱其為保護政策。”
奶奶和爺爺告訴過我,他們是怎么努力控制污染的。當他們告訴我未來會帶來什么時,還嚇到了我。“奶奶,室外燈光有好處,”我說,“讓我們晚上出門時能看見周遭一切。它能防止犯罪,支撐了人類如今24小時不停歇的生活方式。”
“小海倫,如今光照太多,污染太多,”奶奶說,“但我不想和你爭辯了。你說有事要告訴我。我想要聽聽你帶來的消息。”
我笑了笑。這才是我的奶奶,總是避免家庭內的爭吵。“奶奶,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這件,新的望遠鏡工作得很好,我們能望見其他恒星周圍的行星盤,那些行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我們發現其中一顆行星的空氣里有氧氣,還有其他屬于生命和文明標記的氣體。我們發現了同樣的硝酸鹽,也就是我們噴撒到平流層里讓地球氣溫不再上升的物質。我們認為那顆行星上也許有文明。”它僅有30光年的距離,我尋思著為何我們從未收到過他們發來的信號。
但我不想對奶奶抱怨說別人都不關心其他的智慧生命,不贊同我的計劃,不愿向那顆行星發出信號。
“小海倫,聽到這條消息真不錯。我從未想過我們會能夠看見這么遠以外的行星。但是,我想見到的是播撒在黑色夜空中的群星,還有宇宙里的壯麗銀河。”
“我有照片,”我說,“能展示給你看。”
“我不想看小小的照片。你除非看到群星散布在整個夜空里,否則是不會懂得宇宙是怎樣的。”奶奶說道,“在我年輕時,我抬起頭看著綴滿星星的夜空,告訴你爺爺,總有一天咱們的孫子女的孫子女會去探訪他們在夜空里看見的那些星星。可是,假如你的孫子女的孫子女看不見夜空里散布的群星了,看不見宇宙了,他們永遠不會去嘗試探索宇宙。”
我打了個寒顫,記起當我在大峽谷的谷底里佇立過之后,那些大峽谷主題的明信片顯得多么的渺小。我轉過了身,這樣奶奶不會見到我哭泣。
[資料來源:Nature][責任編輯:彥隱]
本文作者杰夫·赫克特(Jeff Hecht),生于1947年,《新科學家》雜志駐波士頓記者,《激光世界》雜志的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