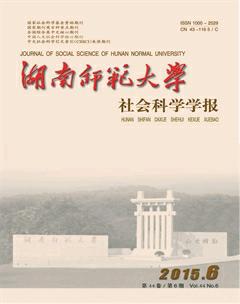試析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分歧和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因素對(duì)中蘇論戰(zhàn)的影響
李明斌
摘 要:中蘇論戰(zhàn)是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史上的重大事件,對(duì)中國和蘇聯(lián)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是一場“雙輸”的歷史悲劇。導(dǎo)致中蘇論戰(zhàn)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分歧和兩國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因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蘇共不認(rèn)同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面紅旗”并提出批評(píng),中國共產(chǎn)黨認(rèn)為赫魯曉夫的“物質(zhì)刺激”是修正主義,這種分歧和所謂爭奪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問題交織在一起,增加了問題的復(fù)雜性。中蘇兩國都是權(quán)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因素對(duì)兩黨兩國關(guān)系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毛澤東認(rèn)為赫魯曉夫與自己不是一個(gè)層次的領(lǐng)導(dǎo)人,赫魯曉夫把毛澤東看作是對(duì)其國際共運(yùn)領(lǐng)袖地位的威脅,兩個(gè)人的文化素質(zhì)、個(gè)性、風(fēng)格和思維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因素都對(duì)中蘇關(guān)系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guān)鍵詞:中蘇論戰(zhàn);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領(lǐng)導(dǎo)人;分歧
中蘇論戰(zhàn)的是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史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史上的重大事件,對(duì)中國和蘇聯(lián)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是一場“雙輸”的歷史悲劇。導(dǎo)致中蘇論戰(zhàn)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歷史積怨、意識(shí)形態(tài)分歧、對(duì)外戰(zhàn)略的沖突、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等方面,其中,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分歧和兩國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因素是導(dǎo)致中蘇論戰(zhàn)的重要原因。今天,正確分析中蘇兩黨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的分歧和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因素對(duì)中蘇論戰(zhàn)的影響,對(duì)我們?nèi)婵陀^地評(píng)價(jià)中蘇論戰(zhàn)、總結(jié)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對(duì)正確分析和評(píng)價(jià)第一代領(lǐng)導(dǎo)集體對(duì)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的探索,對(duì)正確認(rèn)識(shí)改革開放前后兩個(gè)三十年的關(guān)系,從而堅(jiān)定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中蘇兩國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的分歧對(duì)中蘇論戰(zhàn)的影響
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開始,中蘇兩黨開始在斯大林的評(píng)價(jià)、如何認(rèn)識(shí)世界形勢、如何認(rèn)識(shí)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道路等一系列問題上出現(xiàn)分歧。1958年中蘇之間還出現(xiàn)了長波電臺(tái)和聯(lián)合艦隊(duì)事件,中國共產(chǎn)黨認(rèn)為蘇聯(lián)想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為此而進(jìn)行的爭吵使雙方產(chǎn)生了明顯的裂痕。從1958年底開始,中蘇兩黨在國內(nèi)建設(shè)道路與方法上也出現(xiàn)了嚴(yán)重分歧,這種分歧和所謂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問題交織在一起,增加了問題的復(fù)雜性,并促使論戰(zhàn)的發(fā)展和激化。
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國內(nèi)實(shí)行了越來越激進(jìn)的“左”傾路線,集中的表現(xiàn)就是在農(nóng)村搞人民公社,在全國搞“大躍進(jìn)”,搞“三面紅旗”。“大躍進(jìn)”和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dòng)涉及到如何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如何實(shí)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問題,而這正是整個(gè)社會(huì)主義陣營都十分關(guān)注的大問題,不可能不在社會(huì)主義陣營乃至國際共運(yùn)中激起波瀾。對(duì)此,毛澤東也承認(rèn)。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內(nèi)部談話中說:“我們的大躍進(jìn)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1}
赫魯曉夫?qū)χ袊摹按筌S進(jìn)”一開始是贊同的,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觀察之后,他逐步認(rèn)識(shí)到中國“左”的做法存在的問題,這正是所謂“旁觀者清”。赫魯曉夫?qū)γ珴蓶|的看法也發(fā)生了變化,越來越瞧不起毛澤東。同時(shí),赫魯曉夫還害怕中國式的平均主義會(huì)影響到蘇聯(lián),他對(duì)他的同事們說:“中國人的這些改革的口號(hào)是非常誘人的,如果認(rèn)為這些想法的種子不會(huì)在我國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錯(cuò)了。”{2}
1958年12月1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同美國參議員漢弗萊談話時(shí),開始指責(zé)中國的內(nèi)政。其后不久,赫魯曉夫在公開場合談?wù)撓蚬伯a(chǎn)主義過渡問題時(shí),含沙射影地批評(píng)了中國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bào)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擊中國內(nèi)政,表示不同意中國發(fā)生的“大躍進(jìn)”。他在報(bào)告中說,“社會(huì)不能不經(jīng)過社會(huì)主義發(fā)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共產(chǎn)主義”,“平均主義并不意味著向共產(chǎn)主義過渡,而是在破壞共產(chǎn)主義的聲譽(yù)”。他還說,“必須注意到,按目前的發(fā)展水平來說,財(cái)富還不足以充分滿足一切人的需要。那種‘平均共產(chǎn)主義只能使積累起來的資金都被耗盡,并使得經(jīng)濟(jì)進(jìn)一步順利發(fā)展和擴(kuò)大再生產(chǎn)成為不可能。”“認(rèn)為共產(chǎn)主義會(huì)突然出現(xiàn)是不正確的、錯(cuò)誤的。”{3}今天看來,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
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注意到赫魯曉夫的影射攻擊,在毛澤東看來,剛剛因?yàn)殚L波電臺(tái)和聯(lián)合艦隊(duì)等主權(quán)問題而同蘇聯(lián)人發(fā)生過摩擦,對(duì)方卻公然否定我們的創(chuàng)造,焉知不是報(bào)復(fù)抑或心懷叵測?不過,當(dāng)時(shí)毛澤東和黨中央把主要精力用于國內(nèi)問題,主要是糾正“大躍進(jìn)”和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dòng)中發(fā)生的“左”的傾向,所以,毛澤東還是強(qiáng)調(diào)以團(tuán)結(jié)為重。他提出,對(duì)赫魯曉夫的影射,我們可以暫不理會(huì),看看以后再說{4}。
赫魯曉夫并不罷休,1959年7月21日,他又在波蘭的一個(gè)群眾合作社的大會(huì)上發(fā)表講話,認(rèn)為通過公社來走上社會(huì)主義道路是錯(cuò)誤的。正是這個(gè)講話激怒了在廬山的毛澤東,因?yàn)檫@時(shí)毛澤東還面臨著彭德懷的批評(píng)。8月1日,毛澤東在給王稼祥的一個(gè)批件中寫到:“一個(gè)百花齊放,一個(gè)人民公社,一個(gè)大躍進(jìn),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duì)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zhàn),包括黨內(nèi)大批反對(duì)派和懷疑派。”{5}1959年12月1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huì)上又對(duì)中國黨進(jìn)行影射攻擊,并且公然提出社會(huì)主義各國要“對(duì)對(duì)表”,即要求社會(huì)主義各國同蘇聯(lián)保持一致{6}。對(duì)此,毛澤東認(rèn)為“對(duì)表論是錯(cuò)誤的”。
毛澤東把“三面紅旗”視為他一生中的偉大創(chuàng)造,可以說是情有獨(dú)鐘。這時(shí),毛澤東卻要面對(duì)赫魯曉夫的批評(píng)甚至是攻擊,當(dāng)然十分惱火。1959年10月赫魯曉夫第三次訪問北京,中蘇兩黨會(huì)談時(shí),盡管爭論主要是圍繞對(duì)外政策進(jìn)行的,但毛澤東頭腦中考慮的還是“大躍進(jìn)”和人民公社問題,以至10月4日在東郊機(jī)場為赫魯曉夫送行時(shí),毛澤東仍然大講特講“大躍進(jìn)”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人民群眾如何創(chuàng)造了“人民公社”,與蘇聯(lián)歷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有哪些優(yōu)越性,等等{7},而赫魯曉夫卻很不以為然。
赫魯曉夫一方面對(duì)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提出了批評(píng),同時(shí)自己也在犯超越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的錯(cuò)誤。1958年前后,赫魯曉夫本人關(guān)于向共產(chǎn)主義過渡的調(diào)子唱得也很高,15年內(nèi)趕上美國就是他在1957年莫斯科會(huì)議上首先提出來的,毛澤東受他的影響和感染才提出了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hào){8},“超英趕美”只不過是頭腦熱得發(fā)昏之后又向前邁了一步而已。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公開宣布蘇聯(lián)進(jìn)入“全面開展共產(chǎn)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也比毛澤東清醒不了多少。中國有個(gè)徐水縣,蘇聯(lián)有個(gè)梁贊州,在搞浮夸、放“衛(wèi)星”方面,蘇聯(lián)絲毫也不比中國遜色。到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的冒進(jìn)思想已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公開宣布,蘇聯(lián)要在20年內(nèi)建成共產(chǎn)主義。這種超越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的思想,給蘇聯(lián)及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其他社會(huì)主義國家的建設(shè)事業(yè)都帶來了有害的影響。
赫魯曉夫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左”的口號(hào),一方面又對(duì)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進(jìn)行改革。毛澤東對(duì)赫魯曉夫的經(jīng)濟(jì)改革也不滿意。他反對(duì)蘇聯(lián)通過加強(qiáng)利潤的刺激作用讓企業(yè)接受計(jì)劃任務(wù),也反對(duì)國家和企業(yè)的關(guān)系建立在利潤分配的基礎(chǔ)上,認(rèn)為強(qiáng)調(diào)利潤是搞“物質(zhì)刺激”,利潤掛帥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辦法,是修正主義。
毛澤東的獨(dú)立探索也是為了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少用蘇聯(lián)的“拐杖”。在1962年初召開的擴(kuò)大的中央工作會(huì)議上,毛澤東曾經(jīng)說:建國后的頭八年,“因?yàn)槲覀儧]有經(jīng)驗(yàn),在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方面我們只得照搬照抄蘇聯(lián),特別是重工業(yè)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lián),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很少。……從1958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9}但毛澤東走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的道路,采用的是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辦法,用“政治掛帥”、“思想領(lǐng)先”作為調(diào)動(dòng)群眾積極性的原動(dòng)力和維系這種群眾運(yùn)動(dòng)的向心力。實(shí)踐已經(jīng)證明,這條道路和這種辦法忽視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是行不通的。而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推行的改革,毛澤東認(rèn)為走的是與帝國主義陣營“和平競賽”的道路,是運(yùn)用“利潤掛帥”、“物質(zhì)刺激”等經(jīng)濟(jì)手段提高社會(huì)的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這樣,兩條道路、兩種方法之間就有了一道鴻溝。
今天看來,毛澤東中國式的對(duì)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的探索與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推行的改革,其動(dòng)機(jī)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探索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和改革的道路、證明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中蘇兩黨的兩條道路本來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互不染指,也就相安無事了。而赫魯曉夫等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不但對(duì)中國共產(chǎn)黨的獨(dú)立探索橫加指責(zé),而且看作是對(duì)蘇聯(lián)的挑戰(zhàn),甚至當(dāng)作爭奪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這就增加了問題的復(fù)雜性和敏感性。事實(shí)上,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國際共運(yùn)中的第二大黨,也一直想在國際共運(yùn)舞臺(tái)上擁有較多的發(fā)言權(quán)。斯大林逝世后,特別是蘇共二十大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毛澤東和中國共產(chǎn)黨在心理上確實(shí)出現(xiàn)了某種優(yōu)越感,認(rèn)為赫魯曉夫作為這么一個(gè)大黨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是不成熟的,自然對(duì)他領(lǐng)導(dǎo)世界社會(huì)主義運(yùn)動(dòng)的能力持懷疑態(tài)度。毛澤東曾說,我們不能說我們自己要怎樣影響國際,要曉得,蘇聯(lián)自己開香腸鋪,但不愿中國也開香腸鋪,他要推銷他的香腸。毛澤東不允許蘇聯(lián)捆住中國人的手腳,中國也要影響國際,引起蘇共領(lǐng)導(dǎo)人的警惕。
毛澤東提高國際影響力的具體行動(dòng)就是發(fā)動(dòng)了以“超英趕美”為目標(biāo)的“大躍進(jìn)”運(yùn)動(dòng),毛澤東的初衷是,想把我們中國搞得好一點(diǎn),發(fā)展得快一點(diǎn),他認(rèn)為,國內(nèi)工作決定我們?cè)趪H上的發(fā)言權(quán){10}。所以,毛澤東的目標(biāo)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要證明社會(huì)主義陣營優(yōu)越于西方陣營,“東風(fēng)壓倒西風(fēng)”;另一方面,也要證明中國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優(yōu)越于蘇聯(lián)的建設(shè)道路,“學(xué)生超過先生”,“后來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魯曉夫的不滿。對(duì)赫魯曉夫來說,正當(dāng)雙方因長波電臺(tái)和聯(lián)合艦隊(duì)之事而相互耿耿于懷的時(shí)候,中國提出要“提前進(jìn)入共產(chǎn)主義”,是對(duì)蘇聯(lián)“老大哥”地位的挑戰(zhàn)。蘇共還把中國的“大躍進(jìn)”看作是中國領(lǐng)導(dǎo)人民族主義、霸權(quán)主義野心的表現(xiàn),是為其在社會(huì)主義大家庭和世界解放運(yùn)動(dòng)中攫取主導(dǎo)地位這一大國主義野心制造根據(jù)的嘗試{11}。俄羅斯學(xué)者也指出,中國方面宣布要比蘇聯(lián)提前進(jìn)入共產(chǎn)主義這件事,曾經(jīng)把赫魯曉夫激怒過{12}。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蘇聯(lián)的支持與援助,他不能容忍更不相信中國能夠在沒有蘇聯(lián)的援助下,會(huì)走上獨(dú)立發(fā)展的道路。
二、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不和諧的私人關(guān)系對(duì)中蘇論戰(zhàn)的影響
歷史唯物論從來都強(qiáng)調(diào)要正確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個(gè)人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一般認(rèn)為,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之間關(guān)系的好壞對(duì)國家關(guān)系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國際交往中,領(lǐng)導(dǎo)人的個(gè)性、風(fēng)格、思想等,對(duì)一國的外交活動(dòng)及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蘇兩國都是在決策過程中權(quán)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因素往往對(duì)兩黨兩國關(guān)系產(chǎn)生重大影響。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兩位領(lǐng)袖沒能建立良好的個(gè)人關(guān)系,都直接領(lǐng)導(dǎo)、部署并參與了兩黨的論戰(zhàn),赫魯曉夫甚至一直站在論戰(zhàn)的第一線,并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線人員進(jìn)行了面對(duì)面地交鋒。在中蘇關(guān)系惡化的過程中,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個(gè)人因素和兩位領(lǐng)導(dǎo)人之間的私人關(guān)系,成為影響中蘇論戰(zhàn)的一個(gè)重要方面。
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才逐步打敗自己的對(duì)手而成為蘇聯(lián)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的,他既沒有在蘇俄革命和建設(shè)時(shí)期擁有巨大建樹,也沒有多高的理論水平,有時(shí)甚至還很淺薄、很魯莽,與具有很高理論水平和崇高威望、有著詩人氣質(zhì)的毛澤東不是一個(gè)層次的人物。赫魯曉夫盡管生理年齡與毛澤東幾乎相同,并且加入共產(chǎn)黨比毛澤東還早3年,但是,當(dāng)1935年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事實(shí)上的領(lǐng)袖的時(shí)候,赫魯曉夫剛開始領(lǐng)導(dǎo)莫斯科市和州的黨組織;當(dāng)1949年毛澤東成為新中國的開國領(lǐng)袖時(shí),赫魯曉夫仍然只是莫斯科州委的領(lǐng)導(dǎo)人。比較起來,毛澤東與斯大林是一代人,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相比無疑存在政治上的“代溝”。1958年之前,在對(duì)待赫魯曉夫和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tuán)主席(即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的態(tài)度上,毛澤東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不同,因?yàn)樵诿珴蓶|看來,伏羅希洛夫是與斯大林同時(shí)代的老資格的領(lǐng)導(dǎo)人,威望比赫魯曉夫高,能夠真正代表蘇共和蘇聯(lián)的崇高形象,也才有資格受到中國老資格的領(lǐng)導(dǎo)人,尤其是毛澤東等人的尊重。所以,1957年春天伏羅希洛夫訪華時(shí),毛澤東稱他為“伏老”,視他為“長者”,兩人在一起表現(xiàn)出既尊重、又親切和諧的氣氛。伏羅希洛夫還受赫魯曉夫的委托,讓他說服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毛澤東答應(yīng)了,而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時(shí)就向毛澤東發(fā)出過訪蘇邀請(qǐng),但毛澤東未置可否{13}。這似乎表明,赫魯曉夫沒有伏羅希洛夫的面子大。
兩個(gè)人的文化素質(zhì)差別很大,個(gè)性、風(fēng)格和思維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要建立良好的個(gè)人關(guān)系比較困難。特別是赫魯曉夫在黨內(nèi)的地位鞏固之后,他繼承了斯大林在黨的關(guān)系上的“老子黨”做法和在對(duì)外政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fēng),毛澤東對(duì)此堅(jiān)決反對(duì)并極力抵制。作為大俄羅斯民族的一員,赫魯曉夫潛意識(shí)中的大國主義不斷顯露,他自己卻渾然不覺,而作為新獨(dú)立國家的領(lǐng)導(dǎo)人,毛澤東把中國的獨(dú)立和主權(quán)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這種差異不能不影響到兩個(gè)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而影響兩國的關(guān)系。與此同時(shí),由于雙方的探索和改革都出現(xiàn)了失誤,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副作用,雙方領(lǐng)導(dǎo)人都在懷疑對(duì)方的領(lǐng)導(dǎo)能力和領(lǐng)導(dǎo)水平,甚至進(jìn)行影射攻擊,嚴(yán)重惡化了雙方的關(guān)系。這種影射式的攻擊促使論戰(zhàn)的范圍不斷擴(kuò)大,并使論戰(zhàn)帶有極強(qiáng)烈的個(gè)人色彩。其主要表現(xiàn)有兩個(gè)方面:
其一,赫魯曉夫把毛澤東看作是對(duì)其國際共運(yùn)領(lǐng)袖地位的威脅。
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別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中,確實(shí)出現(xiàn)了誰聽誰的,即誰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領(lǐng)袖的問題。斯大林的逝世,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領(lǐng)導(dǎo)人的心理。斯大林在世的時(shí)候,中蘇之間如果發(fā)生爭執(zhí),只要斯大林介入并支持蘇方的意見,從中蘇團(tuán)結(jié)的大局和尊重斯大林的意見出發(fā),中方通常總是作出讓步。中蘇結(jié)盟談判時(shí),毛澤東之所以在那個(gè)后來被他稱之為“搞了東北和新疆兩個(gè)勢力范圍”的“秘密協(xié)定”上簽字,主要與斯大林的堅(jiān)持和“壓力”有關(guān){14}。斯大林逝世后這一情況不復(fù)存在,環(huán)顧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中的領(lǐng)袖們,只有毛澤東享有較高的威望。
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斯大林對(duì)秘密訪問蘇聯(lián)的劉少奇說,中國馬克思主義成熟了,蘇聯(lián)人和歐洲人要向中國人學(xué)習(xí),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轉(zhuǎn)移到了東方,現(xiàn)在又轉(zhuǎn)移到了中國和東亞{15}。斯大林還說,馬克思主義誕生于西歐,卻在東方的蘇聯(lián)取得了勝利,將來就會(huì)在中國發(fā)展,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澤東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領(lǐng)袖{16}。據(jù)當(dāng)年為蘇中兩國領(lǐng)導(dǎo)人擔(dān)任過翻譯的一位俄國人回憶,還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國共產(chǎn)黨共領(lǐng)導(dǎo)人就曾明確講過:斯大林去世后,國際革命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袖就屬毛澤東了{(lán)17}。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準(zhǔn)確,1956年蘇共二十大斯大林問題暴露后,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心理上確實(shí)出現(xiàn)了某種優(yōu)越感。他們明顯地認(rèn)為,自己在許多方面,比如理論聯(lián)系實(shí)際、黨的領(lǐng)導(dǎo)體制、黨群關(guān)系以及對(duì)肅反問題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蘇聯(lián)好。毛澤東對(duì)赫魯曉夫的秘密報(bào)告抱有一種十分復(fù)雜的心態(tài),他不滿意報(bào)告打倒一切的調(diào)子,卻不止一次地高度評(píng)價(jià)赫魯曉夫的做法,說赫魯曉夫勇敢地揭開了蓋子,從而解放了思想。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問題的揭露至少證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yàn)并不都那么令人羨慕。而赫魯曉夫?qū)λ勾罅謫栴}不顧后果的并且是明顯偏激的做法,更讓毛澤東懷疑蘇共新一代領(lǐng)導(dǎo)人的政治能力。
從19世紀(jì)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及其領(lǐng)導(dǎo)人的威望在社會(huì)主義陣營和亞非國家中不斷提高,引起了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的重視,實(shí)際上也播下了蘇聯(lián)不滿的種子。中國在萬隆會(huì)議上支持亞非利益,這已使蘇聯(lián)認(rèn)為中國是蘇聯(lián)在這些國家中擴(kuò)大影響的潛在威脅。面對(duì)在各國共產(chǎn)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澤東,面對(duì)在世界事務(wù)、特別在亞洲事務(wù)中發(fā)揮著日益顯著作用的中國和有效地協(xié)助蘇聯(lián)平息波匈事件后威信大為提高的中國共產(chǎn)黨,蘇聯(lián)無疑擔(dān)心自己在國際共運(yùn)中影響的縮小將削弱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權(quán)力。
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huì)議看,盡管蘇共和蘇聯(lián)是會(huì)議的東道主,與會(huì)者也大致贊成“以蘇為首”的提法,但實(shí)際上在會(huì)上唱主角的似乎不是赫魯曉夫等蘇共領(lǐng)導(dǎo)人,而是毛澤東。第一次莫斯科會(huì)議是社會(huì)主義陣營形成之后全世界共產(chǎn)黨人的第一次大聚會(huì),這次毛澤東訪問蘇聯(lián),與1949年訪問蘇聯(lián)時(shí)的情況已大不相同,赫魯曉夫?qū)γ珴蓶|也格外客氣。1949年新中國剛剛建立,斯大林還健在。1957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jīng)完成了社會(huì)主義改造,經(jīng)濟(jì)欣欣向榮,第一個(gè)五年計(jì)劃提前和超額完成。同時(shí),中國共產(chǎn)黨成功召開八大,開展了1957年整風(fēng)反右斗爭,政治上是穩(wěn)定的,在國際舞臺(tái)上嶄露頭角,威望正迅速上升。特別是因?yàn)?956年蘇共二十大時(shí)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引起全世界的反蘇反共浪潮,接著又爆發(fā)了蘇波糾紛和匈牙利事件。在這股浪潮中,中國黨儼然中流砥柱,在各國共產(chǎn)黨人中越來越引人注目。
第一次莫斯科會(huì)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在會(huì)議期間,毛澤東顯得非常輕松,不時(shí)會(huì)見各國黨的領(lǐng)導(dǎo)人,繼續(xù)調(diào)和波蘭黨和蘇共的關(guān)系,目的是維護(hù)社會(huì)主義陣營的團(tuán)結(jié)。在準(zhǔn)備會(huì)議的文件、提出一系列重要觀點(diǎn)、提出會(huì)議的方向和促進(jìn)會(huì)議的成功等方面,毛澤東及其率領(lǐng)的代表團(tuán)所起的作用也似乎比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更突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毛澤東成了這次莫斯科會(huì)議上最引人注目的領(lǐng)導(dǎo)人。這表明,在斯大林逝世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毛澤東在國際共運(yùn)中的威望確實(shí)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與蘇共的關(guān)系上,和斯大林時(shí)期相比,毛澤東也感覺到有一種平等的氣氛了{(lán)18}。
據(jù)蘇共中央負(fù)責(zé)中國事務(wù)的庫利克后來回憶,1958年以后在莫斯科流傳著這樣的話: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中只有一個(gè)理論家、哲學(xué)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gè)實(shí)干家,是一個(gè)種玉米的實(shí)干家。還有許多人認(rèn)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chǎn)主義的道路,而赫魯曉夫沒有找到這條道路。赫魯曉夫聽了這些話以后非常生氣{19}。在赫魯曉夫看來,“要在這么短的時(shí)間內(nèi)趕超最先進(jìn)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荒謬可笑的”。赫魯曉夫甚至認(rèn)為:毛澤東的目的很明顯,“他想如果他能夠在5年內(nèi)與英國并駕齊驅(qū)并且開始趕上美國,那他就能夠把列寧的黨遠(yuǎn)遠(yuǎn)拋在后面并且超過蘇聯(lián)人民自十月革命以來所取得的全部進(jìn)展。”{20}
其二,中蘇開始面對(duì)面的爭吵之后,一方領(lǐng)導(dǎo)人對(duì)另一方領(lǐng)導(dǎo)人的人身攻擊所造成的感情上的傷害,對(duì)中蘇關(guān)系產(chǎn)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中蘇分歧擴(kuò)大后,到19世紀(jì)50年代末,赫魯曉夫?qū)χ袊I(lǐng)導(dǎo)人的謾罵給毛澤東以嚴(yán)重的精神創(chuàng)傷。毛澤東曾講過:“赫魯曉夫這個(gè)人是很蠢的。中蘇論戰(zhàn)開始以后,我曾向他打過招呼,叫他退居二線,做幕后指揮,不要赤膊上陣與我們對(duì)著罵,以后也有個(gè)轉(zhuǎn)彎的余地,他不聽!”“為了討好美國,罵我毛澤東是好斗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是草(母)雞!”{21}1960年2月,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的宴會(huì)上,赫魯曉夫又大罵毛澤東,稱毛澤東是“破套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rèn)為,赫魯曉夫的行為已嚴(yán)重違背中蘇同盟的原則。為了挽救赫魯曉夫,挽救中蘇關(guān)系,阻止赫魯曉夫進(jìn)一步滑向修正主義,從1960年起,毛澤東決定從理論上對(duì)赫魯曉夫及其錯(cuò)誤路線進(jìn)行批判,并使批判具有理論性和系統(tǒng)性。
盡管如此,毛澤東一開始的目的并不是要大批赫魯曉夫,而是要“幫助”他、“挽救”他。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huì)議上,蘇共代表團(tuán)對(duì)中國共產(chǎn)黨進(jìn)行了公開批評(píng)。面對(duì)蘇共的突然襲擊,中共中央明確要求代表團(tuán)在堅(jiān)持對(duì)赫魯曉夫嚴(yán)正批評(píng)之后,要適可而止,要留有余地,要有理有利有節(jié){22}。之后不久,毛澤東對(duì)前來勸和的胡志明說,我們對(duì)赫魯曉夫也并不使用國內(nèi)對(duì)待右派的辦法來對(duì)待他,而是用團(tuán)結(jié)——批評(píng)——團(tuán)結(jié)的方法,今年不靈,明年再討論、再批評(píng)。明年不靈,后年再來。總會(huì)有結(jié)果。現(xiàn)在甚至還不到公開批評(píng)赫魯曉夫的地步{23}。
但是,隨著分歧的不斷增多和論戰(zhàn)的逐步加劇,中蘇雙方都改變了正面說理的態(tài)度,開始互相攻訐,甚至互相對(duì)罵。俄國學(xué)者在回顧19世紀(jì)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情況時(shí)指出,本來中蘇分歧是完全可以協(xié)調(diào),可以解決的。可是后來雙方爭吵起來,罵起來了,這就無法挽救了。雙方在互相爭吵、互相罵的時(shí)候,中國方面罵蘇聯(lián)可以,罵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可以,就是別罵赫魯曉夫本人,罵他本人就完了,就無法挽救了{(lán)24}。“九評(píng)”的發(fā)表表明,毛澤東已作好了與赫魯曉夫決裂的準(zhǔn)備,不再有什么忌諱了。這樣,自視為國際共運(yùn)領(lǐng)袖的蘇共領(lǐng)導(dǎo)人處處咄咄逼人,從來不買外國人賬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常常寸步不讓,尖銳的沖突不可避免,并最后造成了國際共運(yùn)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組和大動(dòng)蕩,留下了慘痛的教訓(xùn)。
總之,中蘇論戰(zhàn)是國際共運(yùn)史上的一段插曲,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代領(lǐng)導(dǎo)集體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時(shí)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給國際共運(yùn)和中蘇兩黨帶來較大的消極影響,給中國共產(chǎn)黨留下了慘痛的教訓(xùn)。在以反修防修為主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代領(lǐng)導(dǎo)集體總結(jié)中蘇論戰(zhàn)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不斷恢復(fù)和改善與兄弟黨之間的關(guān)系,繼續(xù)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道路,并提出“決不當(dāng)頭”和“韜光養(yǎng)晦”國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形成的過程中,在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中,雖然沒有對(duì)中蘇論戰(zhàn)進(jìn)行系統(tǒng)總結(jié),但可以較多地看到對(duì)中蘇論戰(zhàn)進(jìn)行反思的影子。應(yīng)該說,中蘇論戰(zhàn)導(dǎo)致中蘇兩黨關(guān)系破裂,中國還走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誤區(qū),但是,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作為一支獨(dú)立的政治力量走向國際政治舞臺(tái),終于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并產(chǎn)生道路自信。這也是中蘇論戰(zhàn)的積極影響。
注 釋:
{1}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jīng)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111-112頁。
{2}《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674-675頁。
{3}《赫魯曉夫言論集》(第11集),北京:世界知出版社,1965年,第114-121頁。
{4}{10}{22}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中蘇關(guān)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9年,第192頁,第314頁,第299頁。
{5}{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cè)),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3年,第391頁,第301頁。
{6}《赫魯曉夫言論集》(第13集),北京:世界知出版社,1966年,第452頁。
{7}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jīng)濟(jì)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93頁。
{8}{14}《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1994年,第296頁,第323頁。
{11}(蘇)奧·鮑·鮑里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蘇中關(guān)系》(1945-1980),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第129頁。
{12}{19}{24}丁明:《回顧和思考——與中蘇關(guān)系親歷者的對(duì)話》,《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3}《新中國外交風(fēng)云》(第2輯),北京: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1991年,第10-11頁。
{15}于洪君:《豐碑與警示——20世紀(jì)的社會(huì)主義》,北京:當(dāng)代世界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第353頁。
{16}伍修權(quán):《六十年代國際共運(yùn)大論戰(zhàn)的臺(tái)前幕后》,《炎黃春秋》1993年第11期。
{17}(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諾夫:《毛澤東同斯大林、赫魯曉夫的關(guān)系》,《黨的文獻(xiàn)》1993年第5期。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cè)),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2年,第628頁。
{20}《最后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xù)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419頁。
{21}鄭新、海光、恒煉編:《中外名人談毛澤東》,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623-624頁、633頁。
{23}毛澤東與胡志明主席談話記錄(1960年8月10日)。
On the Influences of Divergenc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Top LeadersPersonal Factors upon Sino-Soviet Debate from 1956 to 1966
LI Ming-bin
Abstract:The Sino-Soviet Debate from 1956 to 1966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t also ha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both Chinas and Soviet Unions socialist construction,and is regarded as a“doubleloss”historical tragedy. Among the various causes of the debate,there are two noticeable aspects:divergences i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nd personal facto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p leaders. On the one hand,Soviet Communist Party didnt agree with CPCs Three Red Banners(the General Line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on the other hand,CPC considered Nikita Khrushchevs “material incentive”to be revisionism. These divergences and the so-called battle for the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ere intertwined,which made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even more complicated. Moreover,in both China and Soviet Union,power was highly centralized so that personal facto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p leader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Chairman Mao personally didnt lik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Nikita Khrushchev and Mao himself,meanwhile the latter considered Chairman Mao to be his rival in the position of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ctually,Chairman Mao and Nikita Khrushchev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such as cultural accomplishments,personality,ways of leadership, thinking patterns etc.. Those factors brought very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Key words:the Sino-Soviet Debate;Socialism Constructing Road;leaders;divergences
(責(zé)任編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