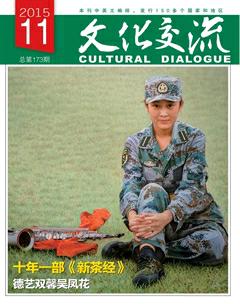夏衍:錢塘之子,革命文人
李月紅
從杭州市江干區新塘路東轉,沿嚴家弄前行100米,矗立著一座江南風格建筑,夏衍舊居便在此:嚴家弄50號。
1900年,革命藝術家夏衍在這里出生。1920年,他從這里走出去,投入到左翼文壇,抗戰時期高擎文藝救亡的火炬。夏衍為我國藝術事業奉獻終身。1995年,遵其遺愿骨灰撒入錢塘江,魂歸故里。
今年,是夏衍逝世二十周年。如今,在杭州市和江干區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夏衍舊居得到恢復擴建,夏衍研究會得以成立,占地4.29萬平方米的夏衍文化街區最近正式進入規劃批復階段。
錢塘之子:留學東瀛時期的探索,開啟了他的藝術人生
十月初,秋陽桂香,筆者走進夏衍舊居,恍若走進他的自傳體小說《懶尋舊夢錄》里的八詠堂、蠶房、臥室。夏衍正是在這里寫下這部長篇回憶錄小說。舊居負責人關佳晶告訴我,舊居正是按照這部小說進行復原的。
如今,這里多了一個展廳,中央豎立著夏衍半身塑像,廳內展示著夏衍一生為我國文藝事業作出的成績和貢獻。陳列柜中,放著他的劇本、生前衣物、紀念徽章等舊物。
舊時嚴家弄,原離城三里。本是沈家祖上下鄉祭祖時的臨時公館“八詠堂”,到了夏衍祖父這一代,因家道中落,才由城內舉家遷此居住。1993年,經夏衍首肯,舊居開始復建。
然而看似體面的“沈家”,在夏衍的青少年記憶里,卻一直為貧窮所困擾。三歲時,父親中風去世,母親夜以繼日攬活貼補家用。在回憶錄里,他寫道,“窮還是緊緊地纏著我,杭州多雨水,特別是黃梅天,可是直到二十歲畢業,我始終買不起一雙‘釘鞋……直到老年,每逢傷風感冒,或者別的毛病發高燒的時候,我總是反復地做同一個夢,就是穿著濕透了的鞋子在泥濘里走路。”
1915年春,他的人生開始出現轉折:他被保送到浙江甲種工業學校讀書。這期間,他遇到了終生難忘的“最好的老師謝遒績”,以及隨后的“五四運動”,他的愛國思想和組織才能得到了極大的鍛煉。1920年9月,學校決定派他去日本留學,培養他為“工業人才”。
得益于在“甲工”打下的基礎,他有更多的時間學習外語,英語、德語都達到了相當的水平,他對世界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癡迷于易卜生、契訶夫的劇本;大膽將自己翻譯的《戲曲論》寄給從未謀面的田漢,請其代為介紹出版。他沉浸在世界文學名著的世界里,歡呼“我愛歌德,我愛華茲華斯,我更愛斯蒂文生”。
在人的一生中,青春歲月是一個詩的時代。1922年,身在櫻花之國的夏衍寫下《殘櫻》一詩,“一片片的殘櫻/蝶兒般地向春泥去/被時光逼走的么/還是伊自己不愿長存/我問。”
“明治歲月”與世界文藝的邂逅,開啟了夏衍的藝術人生。
左聯運動:他是左聯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為抗戰民族統一戰線鼓與呼
1927年,夏衍回國。很快,他加入共產黨,搞工運,跑紗廠。兩年后,地下黨組織讓他較多地進入文化教育界展開活動,籌備“左聯”。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正式召開。那天夏衍穿著西裝,經代表們舉手表決,魯迅、夏衍和錢杏邨三人組成主席團,在隨后的“左聯”常委選舉中,夏衍再次當選,且得票最多。對于這一年上海的三月,夏衍這樣描述,“三月來了!充滿了歡喜和希望,我們擁到街頭去吧……她,已經沖破了長時間重壓著的灰色的地殼,已經接觸著料峭的春風。”
1935年到1937年夏衍全身心地投入左聯運動,特別是左聯電影工作。這段時間他在創作上也取得豐碩成果兩個獨幕劇,一個歷史劇《秋瑾》和著名報告文學《包身工》。
時間來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華民族烽火四起,37歲的夏衍高擎文藝救亡的火炬東奔西走。
那一年,在上海石庫門一幢房子二樓,夏衍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周恩來第一句話就說:“還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周恩來親切地詢問了夏衍各方面的情況,很自然地對夏衍提出:“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很快結束的,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你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做宣傳工作、統戰工作。”
這是夏衍藝術生涯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會面。也正是在這一年,夏衍寫出自己的第一部話劇代表作《上海屋檐下》。此劇1980年在上海被改編成電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已成為無可爭議的中國現代戲劇經典。
1942年,重慶的話劇活動異常繁榮。在重慶北碚區一間倚山臨江的小屋,一個多月后,《法西斯細菌》就誕生在這里。從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與《上海屋檐下》、“七七事變”與《保衛盧溝橋》、“提高抗戰必勝信心、抨擊悲觀主義”與《一年間》、“反對投降傾向”與《心防》、“跳出個人小圈子”與《愁城記》以及反法西斯戰爭與《法西斯細菌》,一直到1945年抗戰接近尾聲與《芳草天涯》,這些作品與這場戰爭,不僅是緊密聯系,而且是同步進行著,為中國的救亡事業爭取更多民心與力量。
辦報生涯:為辦一張有特色的抗戰報紙《救亡日報》而輾轉奔走
在淞滬抗戰的炮火中,1937年8月24日,由國共兩黨聯辦的《救亡日報》在上海正式創刊。郭沫若任社長,國共雙方各派一名總編輯,共產黨方面派的總編輯便是夏衍。這個日子,記載著夏衍開始新聞工作的新起點。
三個月后,夏衍寫出《上海失去了太陽的都市》,這是抗戰新聞史上的一篇名作,雖是嚴謹寫實的新聞報道,但視點的捕捉、敘述節奏的把握將“上海淪陷了,但是人心不死,人們將在鐵與火與血中不屈抗戰”的激情斗志完美地表達出來。夏衍的《始信人間有鐵軍》《悲劇中的悲劇》等力作發表后傳播甚廣。
田漢曾這樣評價夏衍,“在上海《救亡日報》時代,他已經表現非常卓越的記者才能。他對于處理事務是那樣的精神勇敢,對于觀察事務是那樣的敏銳深刻,善能把握要點。”
1937年11月21日,上海淪陷。《救亡日報》當日宣布暫時撤離上海,編輯部遷至廣州。1938年1月1日,《救亡日報》在廣州復刊。夏衍仍擔任總編。10月1日,廣州淪陷。當天凌晨6點,《救亡日報》主要辦報人員在夏衍的率領下徒步離開廣州。次年元月,《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此時的夏衍,掌握了新聞工作的“十八般武藝”,連排字和拼版都學會了。
對于一份報紙來說,言論能直接表明報紙傾向,引導公眾輿論。從1938年9月起,夏衍每天寫一篇評論,每篇千字左右,直至報紙停刊,共計寫了450余萬字。他后來回憶道,“那時真是苦極了。每天深夜還得趕社論……真沒有一時一刻好好地休息。但也感謝這樣使我更能和這偉大的時代同呼吸,對于國際國內每一事變能比較敏銳地看到它的癥結和動向,而不致十分錯誤。”
除了撰寫評論,夏衍還盡可能擠出時間到戰地采訪。1938年除夕,他來到粵北重鎮韶關,感受前線將士的士氣。采訪歸來,寫出《粵北的春天》這篇有名的通訊。
從一份面向知識分子的報紙,到連普通市民都能接受的新聞讀物,到1939年底,《救亡日報》的發行量已增至六千份,成為在粵、桂以至南洋一帶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報紙。這很大程度上在于夏衍對版面不斷加以革新,努力適應更多階層讀者的口味,“救亡木刻”、“青年政治”、“舞臺畫”、“十字街”等新欄目層出不窮。
夏衍在回憶《救亡日報》的文章中說,“從這時開始,我才覺得新聞記者的筆,是最有效為人民服務的武器。”
電影事業:他與電影人一起,
探索中國電影之路
多年來,中國電影界從業者對夏衍尊稱為“夏公”。對他的尊敬和愛戴,不僅因為他是中國進步電影事業的先驅者、開拓者和領導者,更因為他始終和電影人在一起,尋求和探索中國電影之路。
1932年,是中國電影大轉變、大革新的一年。電影當時在中國已成為一門嶄新的藝術。彼時,夏衍已動手翻譯普多夫金的《導演論》,在上海《晨報》“每日電影”副刊連載,署名“黃子布”。
他注意學習電影的藝術特點和拍攝技巧,努力掌握電影特殊的藝術規律。他撰寫的第一個電影劇本《狂流》,揭開了左翼電影的帷幕。1933年3月,《狂流》首映轟動了整個中國電影界,輿論界認為該片是“中國電影界有史以來的最光明的開展”。左翼進步電影的局面很快打開了。
1933年春,《狂流》激起的余波尚未散去,夏衍已把全部精力投向《春蠶》的改編。這部電影的拍攝是中國電影與“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次結緣。茅盾回憶說,“記得夏衍還陪我去明星影片公司攝影場參觀了影片的拍攝。此后,夏衍就成了我家的常客。”這部電影開始了兩人數十年的友誼,并為日后《林家鋪子》的攝制伏下了契機。
1958年,夏衍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主管藝術和電影兩個部門,工作繁忙。這個時期,他一直在考慮的是如何在新中國的電影中,把人民是歷史創造者這個主題鮮明地表現出來。其時,他問北影廠廠長汪洋,“茅盾的《林家鋪子》你們敢拍嗎?給我一個月的假,我交給你們一個劇本。”后來,他真的準時將劇本交給了汪洋。
影片《林家鋪子》的問世,標志著夏衍的電影改編藝術發展到了更高的境界。夏衍告訴飾演林老板的演員謝添說:“對于林老板這個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他的反派的性格、狡猾性,以及損人利己的行為,并不是外露在表面上的。表面看來他很客氣,做人很巴結,對于老婆孩子,他還是很好的,但一有機會欺騙別人,他的手段也還是毒辣的。”在當時能夠自如把握這種復雜性格的,大約只有夏衍這樣既有高度政治洞察力又諳熟文藝特質的藝術家了。
上世紀50年代末,夏衍先后將魯迅小說《祝福》、茅盾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改編成電影劇本。后來,主管電影工作的夏衍,雖然已身居高位,仍經常親手為他人修改劇本。鄧小平曾贊他為“電影醫生”。電影《早春二月》,經夏衍精心批改的鏡頭達到143個,而這部電影的分鏡頭總共才474個,他差不多改了三分之一;劇本《十二朵金花》報到文化部后,夏衍看了劇本聽了匯報后,改成《五朵金花》,電影《五朵金花》創下了當時中國電影在國外發行的最高紀錄。
1994年10月30日,夏衍的九五華誕。這一天,夏衍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并號召年輕一代學習夏衍的奉獻精神和敬業精神。這是繼錢學森之后,國家將第二頂“國家有杰出貢獻的”桂冠授予一位文化名人。直到2015年,“國家有杰出貢獻的”專家仍然只有這兩位。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都是浙江杭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