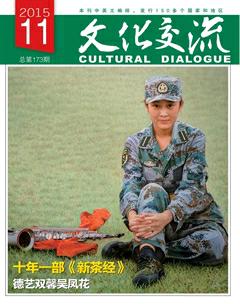樓適夷的故鄉情
陳偉權
1984年7月,樓適夷重回故鄉。那年由丁玲特邀,他到廈門參加丁玲作品研討會,繞道來到故鄉余姚。故園已經沒有他的直系親屬,卻到處有他的親人。當年筆者有幸拜見這位文壇名宿,至今其音容笑貌宛在,他的殷殷鄉情更是記憶猶深。
新文化運動的驍將
樓適夷與魯迅、郭沫若、老舍、茅盾、郁達夫、胡愈之、楊賢江、阿英、林談秋、應修人、馮雪峰等人關系密切。1933年9月,樓適夷在上海被追蹤的特務逮捕,是魯迅第一個寫信通過相關人士使黨組織知道。信中說:“適兄忽患大病,頗危,不能寫信了。”他被捕后在何處無人知道,當魯迅從張天翼處得知樓適夷已押解南京,又立即寫信告訴樓適夷在余姚的親人。在編選一批當時有才華青年作家選集時,魯迅積極推薦樓適夷寫的小說《鹽場》。
在抗日戰爭時期,樓適夷在香港等地協助茅盾編輯《文藝陣地》,五卷本上還署名“茅盾、適夷主編”。1945年8月,郁達夫在印尼被日本憲兵槍殺,最早表達對郁達夫命運關切的是樓適夷《憶達夫》一文,發表在1946年3月20日延安《解放日報》上。
柔石、殷夫等“左聯”五烈士犧牲后,樓適夷遭逮捕入獄,被判處無期徒刑。在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被釋放。他在獄中翻譯蘇聯高爾基作品《在人間》《文學的修養》,以及日本、法國等多部作品。從訪問樓適夷之子及相關資料獲悉,樓適夷還是胡風、梅志的大媒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共派樓適夷去日本、與日本共產黨聯絡,一路皆由胡風暗中照顧。后來胡風回國擔任“左聯”黨組書記,樓適夷在“左聯”與胡風同事。1933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參加“左聯”的梅志為入獄難友尋求援助,來到“左聯”,初見胡風和樓適夷在一起,從此胡風和梅志“產生好感”,樓適夷從中牽線,以致發展成婚姻。梅志晚年寫有回憶錄《胡風和我共同的朋友樓適夷同志》,文中記述:“到了80年代,我們和樓適夷重逢時,他曾開玩笑地對我說:我還是你們的紅娘。你們該請我吃酒呢。”
全面記述樓適夷生平的有《我談我自己》,此文的存世有段曲折。1984年樓適夷到上海住了段時間,包子衍等和他多次交談的內容,根據錄音,整理成3萬余字,題為《樓適夷談生平》,《新文學史料》季刊準備發表,文稿到了樓適夷手上即被“沒收”,鎖入抽屜,禁閉了多年。后來他在此文的引言中說,包子衍“不幸中年謝世,我心痛如割,整理舊作見此稿,拿在手里是一團火。《新文學史料》主編牛漢又多方設法要稿,想到整理者辛苦勞作,豈能白費,話句句是我說的。”“他們實事求是,一句沒空話。”于是,樓適夷最后自己重加整理,改題為《我談我自己》。
樓適夷自謙是“大時代小人物,人家叫我老作家,我感到慚愧,老倒是老,只能算個文學工作者”。
樓適夷逝世后,一批著名人士所寫的回憶樓適夷的文章,匯成32萬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樓適夷同志紀念文集》。
四明山上的文化抗日
樓適夷五歲啟蒙,在余姚念德小學讀完初小、高小共八年,隨后到上海錢莊學生意,受到“五四運動”的積極影響,參加革命活動。1927年入黨后,回家鄉傳播革命火種,建立第一個中共余姚支部,樓適夷任書記,以他家為活動據點,樓適夷來往于上海和余姚之間,聯絡許多革命志士。
抗日戰爭后期,樓適夷奔走于余姚實獲中學、上海儲能中學之間,以教育工作為掩護,從事抗日斗爭。其時,黃源已在四明山上,黃源通過賣柴山民進城帶信給樓適夷,請他上四明山。樓適夷到四明山根據地,見到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后在浙東行政公署文教處和浙東魯迅學院工作。
浙東魯迅學院從創辦到北撤,時間不長,但發展迅速,以靈活多樣方式,培養了800余名干部、戰士,如喬石夫人郁文等。在戰爭環境中,浙東魯迅學院所存史料不多。樓適夷作為當事人,在香港出版《四明山雜記》一書有記載,后來在《我談我自己》中也有回憶:
“新四軍浙東游擊隊的根據地已有三年的歷史,我去的時候是抗戰最后的時期了,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力量已相當強大,中心地在梁弄,是四明山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大鎮。從城區到山區中間有敵偽的崗哨,我是通過水道繞道上虞縣境進去的。”“熟人邦靜唐是司令部秘書長,黃源是浙東魯迅學院副院長,院長是譚啟龍。不久,舉行了一個浙東地區的參議會,成立了政府,這個政府叫浙東行政公署,黃源是文教處長,我當個副的,擔任文教工作。”
樓適夷還寫道:“文化方面,報紙屬于黨的區委宣傳部直接領導,搞刊物沒有條件,我們就搞了地方戲劇,地方戲劇就是越劇,民間叫‘的篤班,影響很大。一個社教隊,招了民間藝人演傳統戲,自編抗日新戲。文學還談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這么件事:那時小學教科書不能用漢奸編的,我們就自己動手編,招刻字匠刻板,我主持了這工作。”
樓適夷在《四明山雜記》里寫道,他們辦了一個報,叫《解放周報》,還做群眾工作,鼓勵群眾生產,支援前線。
1994年《余姚市志》編纂工作完成。樓適夷年屆九旬,為之欣喜,并執筆作序。序言所記:“余姚浙東大邑”,“這也是自己度過黃金時代的最親愛的土地,久背鄉井老而不歸”。
年屆八十故鄉行
新中國建立后,樓適夷全力投入文化工作,但依然情懷故土。他曾說:“文藝工作上,我的職業是后勤服務,得首先盡我的本分。”1957年他和魏金枝同去天臺時,回過家鄉一次。1984年夏重訪余姚,這是1949年以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時隔27年,更是鄉情滿懷。
當時許多人景仰樓適夷,只是沒有機會拜見。此時我在余姚從事新聞報道,也同樣難以聽取這位名人的聆教。好在接待樓適夷的姜枝先老人,對后輩厚愛有加。那年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觀察》上發表《迷人的楊梅王國》報告文學,有些影響。姜枝先為獎掖后人,把我引見給樓適夷。
樓適夷下榻在政府第一招待所,1984年7月5日下午6時半,我當按時赴約,提前抵達,在門外等候了四五分鐘。我所見到的樓適夷,臉龐方正,頭發稀疏,理的平頂頭,穿著上下一色的素色紡綢衣衫,一見面,就覺得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者,十分和藹,完全是平等式的聊天。我們講到浙江日報發表的他的紀實散文《夸我的故鄉》,題材信手拈來,寫得親切感人,也談到余姚是中國楊梅之鄉。我請樓適夷前輩參加家鄉的業余文學愛好者座談會,他欣然答應。后因他參觀河姆渡遺址歸來患感冒,行程安排又緊,座談會未開成。后來他還給我寫過長信,鼓勵業余作者學習寫作,持之以恒,必有所獲。
請樓適夷參觀河姆渡遺址那天,老人興致盎然,深為河姆渡后人而自豪。在和陪同人員的談笑風生中,他又打開隨身所帶的折扇,請大家一一簽名留念。
城中有山十分難得,余姚城中有座龍泉山。《適夷詩存》一書首篇為作于1923年的《龍山放歌》,寫出了年輕作者獻身革命的激情,其中一節為:“啊,我的鮮紅的血液/已如海潮一樣狂奔/我的蓬勃的心兒/已如火山一樣爆噴。”當年他十八歲。1984年返鄉,樓老八十歲,他在龍泉山上梨洲文獻館,看了王陽明寫給其父親的手書,又看了日本人送來的朱舜水先生生前所刻的雕像,以及出土的越窯青瓷,還訪問了龍泉山麓的余姚瓷廠。他在瓷廠題詞:“龍山靄靄,舜水泱泱,人文齊秀,美哉我鄉……”
四明山是樓適夷戰斗過的地方,到了余姚,自然得去。馳車到梁弄,在獅子山上有高聳的烈士紀念碑,徒步登山有數百石階,對八旬老人來說上山談何容易!陪同者勸樓適夷在山下紀念館看看,心意到了就好。樓適夷堅持徒步登山,在紀念碑前低頭默哀,祭掃烈士。回憶1964年他在北京得知建造四明山紀念館,詩興大發,為之題詩:“銳氣英姿迥不同,擎天立地懸奇峰。千巖屏障挺秀竹,萬壑云雷傲古松。石骨嶙峋見勁節,泉流浩蕩發東風。當年冰雪枝頭赤,今日山花爛漫紅。”如今在烈士碑前,樓適夷緬懷先烈,扶今憶昔,以致熱淚盈眶。下獅子山后,他說“這才了卻我心愿”。
樓適夷還去橫坎頭,參觀浙東區黨委舊址、浙東魯迅學院遺址,并當場吟詩:“四十年前橫坎頭,故園今日又重游。當年戰友音容在,豪氣英風萬古流。”
1984年的那次回鄉探訪,樓老非常感慨家鄉余姚已成“現代化工商都市,陌不相識了。為之借唐人賀之章之句,竊易數字,以寄感慨:‘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故園相見不相識,自問我從何處來”。
念德橋畔適夷亭
發源于四明山的姚江,由西向東橫貫余姚城中,經寧波入海。姚江人文薈萃,孕育了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等歷史名人。樓適夷的舊居,是余姚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的遺址,又是名人出生之地,曾開設為紀念館。后因城市擴建道路需要,將館中文物移至余姚名人紀念館和博物館,在城中姚江岸邊的念德橋畔,建造了適夷亭。亭中碑文由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民政府落款。全文如下:
樓適夷(1905—2001)
樓適夷,原名錫春,余姚人,著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出版家。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受黨組織派遣由滬返余姚,成立中共余姚支部,任書記。支部主要活動地點就在樓家。歷任新四軍浙東根據地浙東行政公署文教處副處長,《新華日報》編委,東北軍區后勤政治部宣傳部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顧問,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
樓適夷熱愛家鄉,雖長期在外工作,多次回鄉。一九八七年又把舊居房產饋贈給國家。在其散文《夸我的故鄉》中說:“正如生為中國人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故鄉,也是我一生的夸耀。”而余姚人民則為有他這樣的赤子引以為榮。今特在其故居舊址東南姚江之濱建此亭,作為紀念。
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民政府
二零一零年春立
念德橋橫架于姚江之上,適夷亭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讀著適夷亭內碑文,舉目江橋,佇立遐思,樓適夷文以載道,品格崇高。姚江之水,長流不息地訴述著樓適夷的故鄉情結,也傾注著故鄉人民對他的崇敬、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