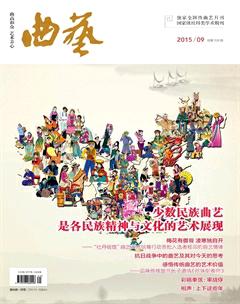第一槍
1931年9月18日晚10點20分,奉天城突然響起了震耳欲聾的炮聲和接連不斷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向我東北軍北大營駐地發起了攻擊,震驚中外的“9·18”事變爆發了。
當時駐守北大營的是國民東北軍第七旅,總兵力八千多人,裝備精良,戰斗力強,而進攻北大營的日軍呢,其實不過六七百人。咱們軍隊的人數比他們多十倍還富裕呢,明顯的敵弱我強啊,打他們應該不費什么事。可東北軍第七旅卻傷亡慘重,狼狽撤出,將沈陽城拱手交給了日軍,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他們接到了上司的指令:不準抵抗,違者嚴懲。此時,在日本特務機關辦公室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接到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的電話,報告東北軍潰敗撤出,日軍戰況順利,美得他是一個勁兒地搖晃那豬頭一般的腦袋:“幺西,幺西,這么發展下去,奉天今天就是我們的了,東北明天也是我們的了,中國用不了多久就全都是我們的了!”他隨即命令關東軍乘勝進發,將奉天城全面拿下。撂下電話,土肥原賢二和幾個部下啟開了幾罐啤酒,擺上了豬頭肉,喝上了。幾個豬頭一樣的腦袋,嘴里嚼著豬頭肉,得意地哼哼上了日本小調。
日本軍沒遭到任何抵抗,占領了北大營之后,便大搖大擺地向奉天城里進發了。可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平靜的夜空里突然響起了一聲清脆的槍聲。第一槍響過,緊接著就是一陣猛烈的射擊。隨著槍聲,打頭里倒下十幾個鬼子,這讓日軍的進城隊伍是瞬間大亂。先頭部隊領頭的是個少佐,趕緊下令:“后撤!先弄清打槍的什么人的干活。”是呀,日本軍也糊涂了,他們掌握的確切情報是中國軍隊奉命不抵抗正在一路后撤,讓出了奉天城。這都已經是空城了,那這打槍的是哪門子部隊呀?不一會兒,前邊刺探情報的回來了:“報告,前邊打槍的不是中國軍隊,是中國警察的干活。”“警察?不會吧?”那少佐把腦袋搖得跟撥浪鼓似的,“警察哪有什么戰斗力呀?敢和我大日本皇軍叫板?我的不信!”“報告少佐,確實是警察。”“不可能,剛才分明有機關槍在掃射,警察哪兒來的機關槍啊?”
你別說,這少佐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警察,各國如此,都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沒有打仗的任務。即使有槍,也都是小手槍,近戰防身用的,哪有配備重武器的?何況中國的正規軍對日軍的進攻都沒敢還手,調頭就跑,你小小的警察敢向日軍開火?是膽兒肥了還是吃錯藥了?
那么向日軍開火的究竟是什么人?你別說,還真是警察。但這支警察隊伍和別的警察隊伍可不一樣,那背景可是不一般哪——他們的局長,那是大名鼎鼎的黃顯聲。
黃顯聲是誰?那是國民黨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少帥張學良的鐵哥們兒。原本是東北軍二十旅的旅長,一年前,被張學良委派,擔任了遼寧省警務處長兼沈陽市公安局的局長。大家還記得小說《紅巖》里那位在渣滓洞監獄里給小蘿卜頭當老師的黃以聲將軍嗎?原型就是黃顯聲將軍。黃將軍在后來的抗戰中更是屢立戰功,聲名顯赫,官至東北軍五十三軍的副軍長。西安事變后,受張學良的牽連得罪了蔣介石,被捕后被關進了渣滓洞。但是,面對這位赫赫有名的抗戰英雄,國民黨高層對他也得高看一眼,不敢怠慢。所以黃將軍在監獄里的待遇還比較好,一個人住單間,伙食也不錯,還給他訂了報紙,自由度比其他的囚犯大多了。黃將軍在獄中還通過牢房墻壁的縫隙,將報紙傳遞給隔壁牢房里被關押的共產黨獄友,有力地支持了監獄黨組織的地下斗爭,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名特別黨員。
話說回來,“9·18”事變發生前,黃顯聲將軍就憑著敏銳的觀察和縝密的分析,對形勢做出了極為正確的判斷。他完全摸透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也完全掌握了上邊的不抵抗意圖。但是他絕不甘心就這么把奉天城交給日本人,心想:你們正規軍不敢違抗軍令,但我作為公安局長,和你們還是有所區別的。我不能看著日本人耀武揚威地在中國土地上橫晃,必須讓他們吃點苦頭,叫他們知道中國人是不甘心做亡國奴的。于是黃將軍早就做好了準備,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因為他在軍內還有職務,搞到重武器是沒有問題的。他秘密派人,搞來重武器,裝備了他的警察隊伍,做好了抵抗日軍的戰斗準備。所以,那日軍少佐弄不明白了,警察怎么還會有機關槍啊?別忘了,這是黃將軍統領的警察隊伍,別說機關槍啊,要機關炮還有呢。
日軍先頭部隊遭到了迎頭痛擊,撂下幾具尸體暫時退了回去,并不敢貿然推進。那少佐趕緊向上司報告:情況不妙,請求增援。
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剛剛還和土肥原賢二報告,關東軍順利地拿下北大營,正向奉天城里大踏步地前進呢,怎么說話功夫就被送回老家好幾個了?怎么中國的警察還敢跟大日本的皇軍梗梗?他趕緊下令,集中隊伍,分兵多路,從不同路線向城里進發。他尋思,你在這條道上阻擊我,我就從別的道繞過去。我還不信了,東北軍的兵營我都進去了,還能在你奉天警察的地盤上掉鏈子?可是,不大會兒工夫,各路紛紛傳來讓他懊惱的消息;“報告,小西門方向部隊遭到阻擊。”“報告,大東方向遇到頑強抵抗。”“報告,皇姑屯方向過不去,都死了六個了……嗯……說話這工夫,又死了一個瘸了兩個。”
本莊繁這個氣呀,怎么哪條道上都有抵抗啊?他忘了,公安局下面都有分局呀。黃將軍一聲令下:日本軍過來就給我往死了打,哪個分局敢不聽他的呀?所以,哪條道上日本軍都沒占到什么便宜。
本莊繁一琢磨,這黑燈瞎火的,也不知道城里的部署到底是怎么回事,這么打下去恐怕不是個事。趕緊發話:暫停進攻,原地休整,明天再說。
各路日本軍得令,先撤下去了。
奉天城里的夜晚,暫時平靜下來。
公安局里,黃顯聲將軍正在召開緊急會議。
黃將軍,大高個,身材挺拔,眉宇軒昂,用今天的話說,那是標準的帥哥,或者說顏值很高。他雖然是一個武將,但從小飽學博覽,學識淵博,后投筆從戎,所以他和一般魯莽的武將有很大的不同,那是英武而不失儒雅,思維縝密,頭腦清楚,從不莽撞胡來,是一個難得的文武雙全的人才。要不,少帥張學良也不能和他的關系那么鐵。
黃將軍看了一下部下,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諸位,黃某感謝大家!今天,我們用自己的行動給了日本人一點顏色瞧瞧。不過,雖然暫時阻止了日軍的腳步,但我們必須清楚,日本人是兇惡的,殘忍的,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而我們警察隊伍,以前從來就沒打過仗,戰斗力畢竟有限。今天我們是突然襲擊,打了日本人一個措手不及,可一旦他們緩過勁兒來,就會積蓄力量,對我們發動更猛烈的攻擊。我們和他們硬拼,是不明智的。所以我要根據具體情況,做好準備,盡量多堅持些時間,爭取多打死一些鬼子,然后,我們按計劃撤出沈陽,到新民和錦州待命。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只要我們保存好火種,燒死日本鬼子,那是早晚的事。”接著,黃將軍如此這般地作了部署,部下們便分頭下去執行。
第二天白天,沒什么動靜。日本人受到驚嚇,也得緩口氣呀,晚上折騰夠強,白天還得補覺不是?
到了夜里,日本軍隊出動了。這回,他們不敢大意,把坦克派上來了。這邊,黃將軍搞的機關炮也派上了用場。雙方叮咣噼啪火力都相當猛,戰斗是異常激烈。幾個回合過去,死傷都很多。本莊繁見久攻不下,下令把坦克集中起來,從一個城門突擊。這一招還真見效,畢竟那鋼鐵大家伙抗打,你干掉一個它第二個又上來了。警察隊伍遵照黃將軍的指令,邊打邊撤。他們熟悉地形啊,游刃有余。鬼子也不敢掉以輕心,慢慢推進,謹慎前行。最后,日本軍終于推進到了城里,包圍了公安局的總部,只見那大門緊緊地關閉著。日本軍用坦克連續撞擊,打開了大門,沖到了院內。此刻,院子里已是空無一人,整個大樓里也是漆黑一片,鴉雀無聲。人呢?剛才火力還那么猛,怎么蔫吧悄地都沒了?在這兒跟我玩兒失蹤啊?嘿嘿,真叫他說著了,此時,黃將軍的隊伍已經按計劃順利地撤出了奉天城。
就這樣,一支原本沒有戰斗力的警察隊伍,在黃顯聲將軍的指揮下,打響了“9·18”事變后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第一槍。他們堅持了四十多個小時,對日軍實行了重創。最后,為保存實力,撤出奉天,來到了錦州,和已經先期到達那里的省政府行署和東北邊防軍司令部行署匯合。
雖然黃顯聲將軍率隊伍對日軍進行了抵抗,但張學良卻并未對此予以追究。因為黃顯聲將軍指揮的畢竟是警察隊伍,不屬于正規軍,你拿軍令懲處,顯然并不合適。再說,你怎么知道張學良心里頭到底是怎么想的?這打的是日本人哪,他能不高興?不說民族大義吧,他老爹是怎么死的他不清楚嗎?這也等于給他報了仇是不是?因此,黃顯聲將軍到了錦州后,少帥張學良不僅沒責怪他,反而將主持錦州兩個行署工作的大任交給了他,命他設法保住錦州。錦州是關內外咽喉要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得失,直接關系到熱河、平津的安全。
黃將軍深知肩上的責任重大,他也知道因為有不抵抗的軍令,正規軍是不能出戰的,那日本人打過來,光靠警察隊伍,總不是長久之計。如果阻擋不了日軍,那保衛錦州豈不成為一句空話了?怎么辦?經過深思熟慮,他計上心來。當即決定以警察隊伍為基礎,發動民間武裝,動員社會力量,全民奮起,保家衛國。
于是,在黃將軍的發動下,一支特殊的抗日隊伍——東北義勇軍正式成立了。從此,在東北的大地上,在白山黑水之間,義勇軍這支特殊的隊伍,承擔起了抗日救國的重任。他們英勇戰斗,前赴后繼,不懼流血,甘愿犧牲,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中華民族新的長城。這才有了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那首《義勇軍進行曲》。唱著這首歌,中華兒女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舊體制,建立了新中國。這首歌,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這正是:危難之時挺脊梁,豈容惡魔逞兇狂。血肉之軀筑長城,義勇美名萬世揚。
點評:
讀了崔立君先生的評書《第一槍》,眼前一亮,這是一篇飽含滿滿正能量的佳作。
據立君先生說,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遼寧省曲藝家協會組織創作力量為田連元先生打造了系列評書《鐵馬冰河丹心譜》,立君先生參加了創作,《第一槍》就是其中的一篇。
我們通常說的八年抗戰,是指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范圍內掀起的全面抗戰。其實,從1931年“9.18事變”之夜,黃顯聲將軍率警察隊伍在奉天城打響第一槍后,東北人民就一天也沒有停止對日軍的抵抗。對東北人民來說,是十四年抗戰。關于抗戰的作品,我們早已不陌生。有悲壯感人的,有弘揚民族大義的,甚至也有近年來某些胡搞的所謂“抗戰神劇”。但能做到既還原史實,又給人帶來藝術享受的佳作并不是很多,《第一槍》 是一次有益的嘗試。這篇作品充分尊重史實,沒有胡編亂造,時間、地點、事件及主要人物都有據可查。同時,作者沒有讓史實束縛了手腳,在紀實的基礎上,大膽展開藝術構思,發揮合理想象,豐富了很多生動的藝術細節,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受。曲藝畢竟是讓人開心的藝術形式,整個作品,張弛有度,描述自然,緊張曲折,又透著輕松幽默,而且不乏“包袱”,讓人在領略英雄壯舉的同時,又時時發出會心的笑聲,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在情節的設計上,自然流暢,故事性強。在語言的使用上,準確精煉,干凈利索,絲毫不拖泥帶水,沒有多余的話。尤其是充滿了詼諧爽朗的“東北味”語言特色,給作品打上了鮮明的烙印,也緊緊把握了田連元先生的表演風格。
對敵人的描寫,貶損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貶損得恰到好處又是極難的。這一方面該作品在尺度的把握上做得也比較恰當。
立君先生曾說過,他一向追求“嚴肅認真地創作,輕松幽默地完成”,這話很值得我們搞曲藝的人琢磨。
如果說還有什么令人不滿足的,大概就是在黃將軍個人形象的塑造上,可能受節目時長的限制,并未充分施展。如果再多一些對人物性格和動作的描述,藝術感染力勢必更加強烈。
立君先生是一位勤奮的曲藝作家,多年來,他不僅堅持在曲藝創作領域不懈耕耘,而且在曲藝教學中也頗有成就,帶出了很多優秀弟子,其中不乏來到深圳打拼的佼佼者,他們已經成為深圳曲藝事業的骨干力量,在此,我也一并向他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