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平衡的政治藝術
文/阮帆
弗朗西斯·福山:平衡的政治藝術
文/阮帆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ViVi攝影)
1989年初,對自由民主制充滿信心的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在文中,福山斷言,民主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隨著幾個月后冷戰結束,柏林墻轟然倒塌,他的斷言猶如一個變現的寓言,在西方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1992年,他在原文章的基礎上擴充,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其核心論點——“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制,而布爾喬亞是最后之人”穿越世紀,歷經了熱烈的擁抱和不一而足的批評。
去年9月,福山出版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在接受英國時政周刊《新政治家》采訪時,福山承認“使自由民主制度奏效是何其艱難”。在書中,他表達了對美國政治現狀的失望,認為即便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成熟民主國家,也可能經歷政治衰落過程。過去二十多年對世界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使福山意識到了西方民主自由制也是講條件的,在下結論時也考慮得更加全面而謹慎。不過,他并無意推翻之前的結論,而是在肯定自由民主制的前提下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自由民主的前提是國家能力,除此之外,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必須在法治下運行。
4月中旬,弗朗西斯·福山來到清華大學,與青年學子們交流了他的政治思想。此外,在國家外國專家局,福山與中外專家學者們就如何推進中國的依法治國和社會治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作為外國專家為中國的政治治理和發展建言獻策。對于他的政治思想,我們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

希臘危機是官僚主義的衍生品,圖為希臘民眾示威抗議政府財政緊縮政策
自由民主制仍然是政治的不二歸宿
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福山開篇就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歷史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構成“歷史的終結”。換言之,以前的統治形態有最后不得不崩潰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而自由民主也許沒有這種基本的內在矛盾。因此,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經不能再改良了。
這一結論剛剛面世,就受到了批評家的各種質疑:其意圖動機是什么?命題是否有點太狂妄了?批評家們紛紛用“民主國家的亂象”,“威權國家的韌性”來批駁福山的核心論點,舉出柏林墻的瓦解、伊拉克侵虐科威特來證明歷史還在“持續”。
面對這些質疑,福山并沒有感到困擾,相反,他認為不管是從經濟發展的方面考量,還是從黑格爾對于人們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認”的論述來看,這種社會形態都將使歷史終結成為必然。
然而,在去年9月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里,人們發覺福山的學術思想似乎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曾經那個對于自由民主制度自信滿滿的擁護者卻在這本書里花了很大篇幅論述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自由民主制國家的種種弊端,警示“政治衰敗”的可能。
“一種制度曾經很成功、穩定不等于它永遠會如此”,福山在書里寫道。他認為,美國已經出現了“過度民主”的危險,“否決民主制”導致政府被民主和法治逼到“已經無法做出艱難抉擇的處境”。
為了說明美國的司法機構如何削弱其行政機構,福山用美國森林局來作比方。成立于1905年的美國森林局曾經是美國高質量官僚機構的典范,但如今它的每一項使命都對應于不同的外部利益集團:木材商、環保主義者、森林居民。到底是要砍伐木材,放任森林野火還是保護樹木,森林局卻不能自主決定,因為它“受到國會和法院的多層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命令”。
一些媒體開始評論,福山的學術思想有了重大轉折,他已經開始承認,相較于民主和法治而言,國家能
力對繁榮更加重要。
對此,福山認為這顯然是對他觀點的誤讀。在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采訪時,他解釋道:“我的論點是,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必須讓國家能力與民主和法治相平衡。”
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里,福山概括說,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政府、法治和民主——相互補充。雖然這三個要素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比如民主要求控制政府而政府又要求自主,又比如法律的嚴格運作限制了行政的酌情決定權。但不管它們之間的摩擦有多大,福山認為,自由民主制承認每個公民的尊嚴和價值,這是自由民主制的道德基礎。這種道德基礎,從根本上將人和動物區分開來,創造了一個環境讓人們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它是捍衛尊嚴的自由民主社會的源動力。
在最后一章里,福山總結說,“盡管民主在21世紀初出現了挫折,但民主的前景在全球意義上仍然保持良好”,“雖然高質量的民主政府時而供不應求,但對它的要求卻與日俱增……這意味著政治發展過程具有一種清晰的方向性,意味著承認公民之平等尊嚴的可問責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因而,“自由民主制沒有真正的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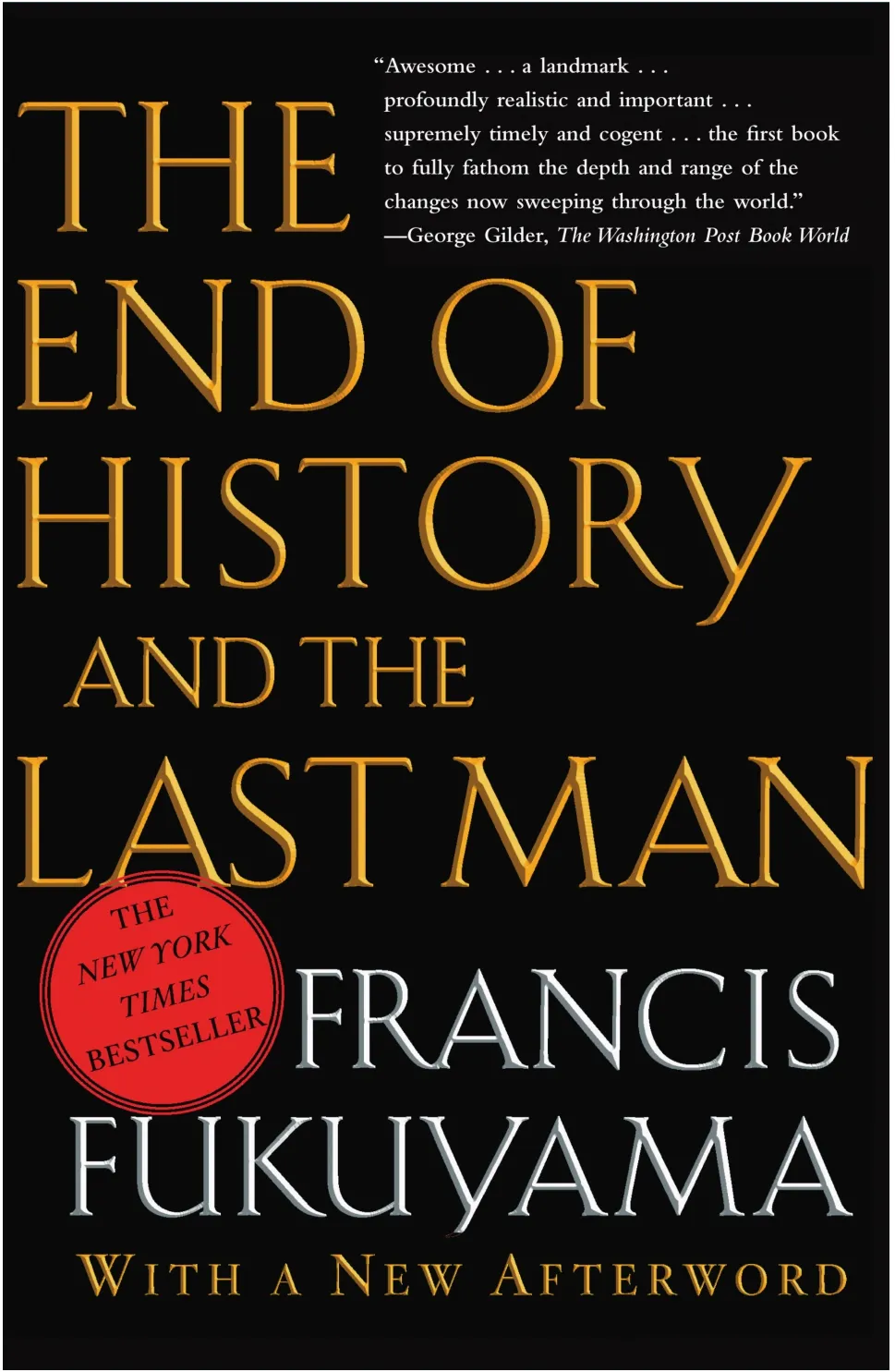
福山最具代表性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此書出版后引起巨大轟動,被先后譯為20余種文字
沒有國家能力的民主不是好民主
既然自由民主制是社會的終極形態,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都獲得了不同形式的肯定:自由國家和共產主義社會,那么,民主是否真能在全世界推廣開來,以不變應萬變?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國家大量出現,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也逐漸高漲。然而,良好政治秩序的建設卻并非易事,它取決于許多條件和偶然因素,但關鍵無非在于強政府、民主和問責制。三者往往不可兼得,彼此之間也常常難以達到平衡,但是缺少任何一方,制度就很難運行好。于是,制度要素的發展順序至關重要。
在福山看來,理想的順序是先建立強國家,繼而發展法治,最后走向民主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丹麥。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的前言,福山寫道:“丹麥是一個理想化的社會,它繁榮、民主、安全,國家治理得當,腐敗率很低;在那里,有執行力的政府、強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從世襲制轉型為現代國家,丹麥依靠的就是順序鋪墊的這三大基石。
舉兩個反例可以說明這個論點。比如希臘,希臘在沒有充分完成國家建設的條件下“過早地”進入了民主化階段,在19世紀希臘的普選權實踐中,政治精英在選舉中收買民眾,以提供公職就業機會等方式交換選票。結果在19世紀70年代,希臘的人均公務員數量是英國的7倍。政治精英為獲得短期政治利益而導致官僚膨脹化的傳統在希臘一直殘存,1970年之后的40年間,希臘公職人員的數量增長了5倍。
又比如印度。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目前,這個國家卻飽受普遍的裙帶關系和腐敗困擾。在法治、民主問責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印度滿足了兩個,卻離大功告成差之千里,問題就出在這個順序上。也許正是出于此種覺悟,2014年,印度果斷地轉向人民黨領袖納倫德拉·莫迪,希望他能提供堅決的領導,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取代過去10年來無能腐敗的國大黨領導的聯盟。
希臘和印度二者共同面臨的問題,是精英利用特
權和資源向較為弱勢者提供保護和利益、換取支持和服務,即政治學家所稱的“庇護主義”。庇護主義常常是弱國民主的常見病,它不僅是腐敗的溫床,也導致了低效政府,加劇了社會不公。先行于國家與法治建設的民主化進程可能造成脆弱的政治秩序,這不同程度地出現在晚近“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轉型之中。
“在我對發展中國家所做的研究當中,我發現一些地區的國家會愈發貧窮,主要是國家能力不足導致的負面效應。它比政治發展中其他任何成分的缺乏所造成的影響都更嚴重。”福山在一次采訪中說。
他說自己同許多生活在發達國家中的人一樣,有時候會把國家能力看作理所當然的事,但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觀察當中,他意識到如何發展國家能力卻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制度建設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言:“一個政體在限制權力之前,首先必須行使權力。”
現代國家的起源和中國模式
福山認為,如果要追溯歷史終結的政治思想從何而來,就不得不從古代中國說起,因為古代中國是整個現代國家制度的起源,是研究世界政治歷史不能繞過的一環。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福山花了很長一章專門寫古代中國。他提出,要談一個擁有官僚體制的、中央集權的、選賢任能的、秉公持正的馬克思·韋伯式的現代國家,我們應該把眼光聚焦到中國的漢代——它那現代國家意義上的政治制度比歐洲早出現了1800年。
漢代的國家是圍繞官僚體系和教育體系建立起來的,一方面,福山認為,這是戰國時代各國相互競爭共存狀態的產物,因為如果要打勝仗,政治上就必須選賢任能,而不能依靠家族傳承。另一方面,他認為這表明中國古人懷有一種抱負,認為政府是把公民當公民看的,而不是以家族裙帶關系或地方豪族。正是這種對于世襲主義的克服,給中國的政治種下了優良的基因。
他在書中寫到,當今的中國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歷朝歷代的一種延續。尤其是清王朝后期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這漫長而巨大的苦難讓人們產生了一個共識——國家必須強大,才能使人民得到保護和教化。不過,同時讓他覺得遺憾的是中國沒有發展出一套制度,比如法治或西方的選舉責任制,來制衡國家。
在他歸納的“向上負責制”和“向下負責制”兩種政治負責制中,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屬于后者。其潛在危險是否決政治,體制可能被分離聯盟俘獲并固化,走向政治衰敗。而前者常見于一些一黨專政的國家,這種負責制很可能存在腐敗、濫用權力等一系列問題。
“向上負責制的風險在于,你首先得有個好的領導人。這種制度的優勢在于它能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解決信息問題,如果管理得當,權力下放能加快政府的反應速度,更有效地滿足公眾利益。”福山說。他認為,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因為自鄧小平開始,中國的領導人都很好,所以中國體制能夠在1978年以后比民主國家更快速地改變經濟體制的基礎。但他認為,仍然有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怎么確保永遠都能遇上好的領導人?
福山在外國專家建言座談會上介紹說,要將向上負責制的風險降到最低,就必須依賴法治。“中國有以法律為基礎的決策體制,但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現有的趨勢,最終走向真正的法治。”他說。對于中國的現狀,他認為如何將法律應用的范圍擴大,將法律的決策制度做得更加透明公正乃是中國的領導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所有的決策和決斷都應當是公開的、正式的、開放的,每個人都能夠看到,這就能夠限制自由裁量權,在低級別的政治當中尤為重要。”福山說,“因為很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沒有這種限制,不限制行政權力的話,對于自己的政治體系非常危險。”
談及中國自十八大以來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反腐運動,福山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提道,希望能夠比較快地建立一個程序或者規則,不然的話,一開始對于反腐行動的支持,很可能到后來就成為過度個人意志決定的東西了。
拋開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與自由民主到底相差還有多遠,福山認為,“中國模式”乃是現在唯一看上去可以與自由民主相競爭的體制。“最好的官僚機構能夠自主地運用判斷力做出決定,去冒險和創新。而最糟糕的官僚機構執行他人制定的詳盡規則”。
回首二十多年前做出的歷史終結的判斷,福山最新的兩本力作似乎在試圖闡釋歷史走向這一終點的復雜而崎嶇的路徑。而我們得到的啟示是:也許只要方向是對的,我們就該意識到制度和程序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