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哲三者并重方為大家
他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科普作家、教育家,中國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在身體癱瘓的情況下,他克服了巨大的病痛和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寫下數百萬字的科普作品,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就是高士其,天空中有一顆星以他為名。因為引導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走上科學道路,他還被親切地稱為“高士其爺爺”。
201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誕辰110周年紀念日,在2015年江蘇省全國科普日活動期間,高士其誕辰110周年科普展作為一項重要活動向公眾開放。為了弘揚高士其精神,我們特約高士其之子高志其先生撰寫文章,為我們講述“高士其爺爺”的故事。——編者
在2005年高士其百年誕辰之際,媒體和社會輿論就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高士其現象是怎樣產生的?他的成就又是如何取得的?時間再回溯到1999年,《人民日報》刊載的一篇文章的標題這樣寫道:高士其的傳人在哪里?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今天的時代無法產生高士其這樣的科普大家?
這個問題迄今未有答案,因而在今天,我們有必要追溯一下高士其的成長道路。
文化、科學與哲學三位一體
高士其是怎樣成長的呢?我們可以理解為文化的高士其、科學的高士其和哲學的高士其。
因為在任何一個領域,大家的成長必須是文、理、哲三者并重,如果以一棵大樹來比喻的話,那么文化就是大樹的樹根,哲學則是大樹的升華。由此可見文化作為基礎的重要性。
高士其在3歲時,就讀了《三字經》《幼學須知》《千字文》《百家姓》等書,而做人的基本道理也盡在這些簡單的經典之中了。4歲時,他又讀了《大學》《中庸》,一篇八百字的《大學》他整整背誦了八百遍,倒背如流。每逢家里來客人時,祖父就把高士其叫出來,讓他當眾背誦。高士其則搖頭晃腦、吐字清晰地背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幼小的高士其雖然不懂這些古文的明確意涵,但卻充滿了莫名的喜悅和興奮。他隱約地感到在這些語言文字后面,是一扇精神世界的大門。
隨著歲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幼時所背誦的經典字義,都一一地被理解、消化和吸收了。文化的原理、傳承的精神、歷史的使命感也隨之建立起來,當然,這與當時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備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壓和凌辱密切相關。
在小學時期,高士其幾乎閱讀了所有的中國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紅樓夢》《封神演義》《包公案》《儒林外史》《說岳全傳》《七俠五義》等,還有一些翻譯過來的西方文學,如《福爾摩斯探案集》《黑奴吁天錄》等。同時,高士其白天在福州明倫小學上學,晚上祖父繼續教他四書五經。這些都為高士其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六七歲時,高士其開始接觸自然科學,他的一位叔叔給他講了細菌、病毒和微生物的知識,激發了他對微觀世界的好奇與探索。此后,在明倫小學和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里,高士其正式接受了自然科學的教育。在對自然科學的學習中,他全面發展而又重點突出,他熱愛化學,每次做化學實驗時都十分準確。因此,他懷抱化學救國的遠大理想。同時,他也喜歡數學。由于興趣廣泛,他獲得了“博物學獎章”。赴美留學后,他在自然科學方面又得到進一步深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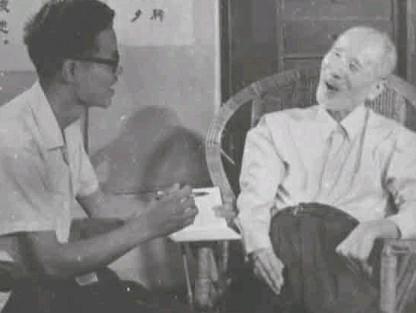
高士其精通英文、德文和法文,廣泛涉獵西方文學,在美國留學期間,他經常到美國國家圖書館去看書。他在回憶錄里曾這樣寫道:“在美國國家圖書館,我幾乎閱遍了世界上的所有名著。”旅歐期間,他在萊茵河畔歌德故居的小書攤上流連忘返,最終買到了一本德文版的歌德名著《浮士德》,滿意而歸。與此同時,他還喜歡藝術,熱愛音樂和攝影。他還參加音樂會,學習小提琴,購買了唱機和唱片,聆聽貝多芬的交響樂;他攜著照相機踏遍了美國的東西兩岸,拍攝了許多風光旖旎的照片,這些照片至今還保存在他的影集中。
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讀書時,高士其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堂哲學課,從而使他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歸國后,他與哲學家艾思奇結為朋友,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習,這就奠定了他的哲學思想基礎。1937年,高士其到達延安后,不但從事自然科學的普及工作,發起了國防科學社、邊區醫學座談會、細菌學討論會,同時還與周揚、艾思奇、成仿吾、郭化若等人發起并組織了“新哲學會”“自然辯證法座談會”。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徐特立、陳唯實、范文瀾、于光遠等四十幾位同志相繼成為會員,參加座談,研究討論哲學與方法論。
高士其是當時我國僅有的幾位微生物學家、細菌學家之一,因此,他帶來了世界上先進的科學知識與思想。這些知識、思想對當時閉塞的延安地區來講,仿佛打開了一扇通往現代世界的窗戶,充實了延安干部群眾學習哲學、自然辯證法的科學內容。為此,毛澤東在窯洞中與他探討了古典自然辯證法。
綜上所述,高士其在文化、科學、哲學三方面都進行了很好的學習與研究。實際上,高士其的成長及其作品是由文化所奠定的、科學所孕育的、哲學所指導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文、理、哲三者并重,方為大家也,方為社會與民族的大家,世界與人類的大家。
從高士其的回憶錄看他的作品由來
要走近高士其、要理解高士其,就必須閱讀高士其的回憶錄。那是因為我們要想理解高士其的作品,弄清他為什么要這么寫,這么寫的緣由與淵源在哪里,也就是古人所講的出典在哪里,在回憶錄中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確的答案。通過回憶錄,我們看到的高士其不再是一個理性的、概括的形象,而是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歡樂、有人性、有人文思想的高士其。它揭示了一個在生活和心路歷程中的真實高士其。而真實的高士其離我們更近,也更加感人。因此,我們能夠深切地理解到:高士其為什么能夠成為高士其。這樣,高士其就成為一個人人都可以仿效的榜樣。
從高士其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高士其把他所學到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所經歷的一切,包括科學、文化、哲學、文學,乃至于民俗民風和民間藝術都運用于他的科普創作中了。如《菌兒自傳》就是他模擬細菌,以第一人稱寫的,把傳統文化、四書五經的內容融入到文章中去了。
高士其的家族信奉道教,因此,他把《封神演義》中的三大教主,都放入了他的作品之中,如《細菌的祖宗——生物的三元論》,論述了植物界、動物界和菌物界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高士其還把基督教《舊約》中亞當、夏娃的故事作為《細菌的大菜館》一文的開篇,把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中豆花、蜘蛛網、小飛蛾、芥子等扮成的山林仙子,巧妙地引進了他的《散花的仙子》一文中。
不但如此,高士其還把童年生活的斗指游戲“大王、雞、螞蟻”寫成了細菌與人的概論,揭示了細菌、植物、動物之間生物循環鏈的關系,較早地闡述了人與自然、人與萬物和諧的道理。他甚至以福州故鄉的石板路作為文章起始,寫成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即《地球的繁榮與土壤的勞動者》,所談內容從宇宙到地球,從山海到土壤,從菌類到植物,從植物到動物,從動物到人類,再從人類回到土壤中的螞蟻、蚯蚓和細菌。篇幅不長,三千多字,卻豎逾時間而橫跨空間,氣勢十分宏闊,揭示了各種生命誕生之理和誕生前后的順序變化。
總之,高士其的作品縱橫時空,涵蓋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從中世紀大規模的瘟疫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熱”都一一展現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甚至預見到日本帝國主義會發起細菌戰,并告訴人民預防的知識與方法。
高士其除了具有科學家固有的科學預見精神之外,還對社會發展規律有深刻的洞悉,這在高士其的作品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天的進行曲》就預言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敗,《生命進行曲》預言了“四人幫”反動路線的滅亡,而《讓科學技術為祖國貢獻才華》一詩則吹響了全民向科學進軍的號角。
高士其以他的創作實踐告訴人們,科普創作不是一項孤立的工作,而是要與科學、哲學、思維科學、心理學、教育學、文學、詩歌、神話、童話乃至民俗民風相結合,讓它們都為科普創作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搞好科普創作,也只有這樣才能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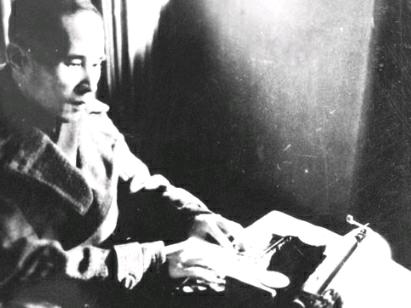
高士其的人民性
熱愛人類、熱愛人民、熱愛兒童,這一特點在高士其的身上體現得格外突出。同時,他也是愛憎分明的,對一切邪惡從不姑息,從不與之同流合污。
在1937年離開上海的前夜,高士其在與表弟高士坦的談話中多次表示,要到前線去和日本鬼子拼命。在廣州三聯書店遭到國民黨特務砸毀時,他憤怒地掙扎著從三樓沖了下來,要和特務們進行斗爭,他的行為感動和鼓舞了在場的許多同志。實際上,他的身體條件并不允許他拿槍上前線,但是他并未放棄一個戰士的使命,他拿起筆來做武器,猛烈地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腐朽統治。
建國以后,高士其生活在人民之中,他對一切人都是友愛的、平等的。甚至到了老年他都不厭倦人,每天接待四面八方的來訪者。
1958年,周恩來總理批準在建國門古觀象臺旁,為高士其建造一座符合他身體狀況和生活需要的特殊住宅,并圈以很大的院落。但高士其認為與機關的同志們離得太遠了,隔絕了與群眾的聯系,他更愿意在機關大樓旁安家。于是就在中國科協所在地建了一幢普通的二層小樓,這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高士其小樓”。小樓落成以后,每逢節假日都賓客盈門、絡繹不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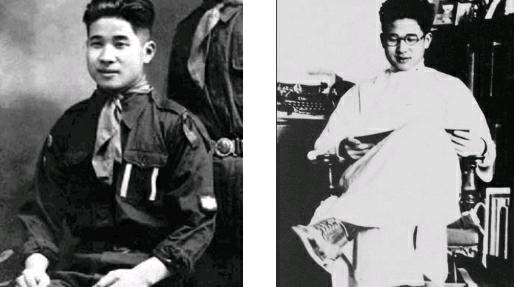
在父親身邊的幾十年間,我從不記得他恨過什么人,對什么人耿耿于懷過。因為沒有什么事情可以讓他難以釋懷,因為他是一個大寫的人,他是屬于人民的人,他把自己和人民融為一體,并為了他所愛的人民,孜孜不倦地從事創作,從他的創作中,他仿佛看到了祖國的美好未來和人類的整體升華。正如高士其在他晚年的一段哲理警句中說道:“不能設想,人類社會如果沒有知識能夠發展到今天,或許,人類早已消亡,或許,人類還在黑暗的深淵中踽踽行走。的確,沒有知識,人類就不可能把自己塑造成具有高度理性思維的崇高形象。”這不僅是一種思想和精神,也正是高士其的人民性之所在。
歷史發展到今天,新的時代,新的世紀,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高士其、走近高士其、理解高士其,與高士其的精神融為一體。
80多年前,高士其把帶“人”字旁、“金”字旁的名字改掉了(原名高仕錤),他毅然宣布“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錢”,這振聾發聵的聲音,標志著高士其從小我、個我、私我走向了大我、忘我乃至無我的境界。
今天我們讀高士其的書、走高士其的路、成為高士其一樣的人,成為高士其那樣的科學家、高士其那樣的作家、高士其那樣的教育家,成為具有高士其精神的在各種工作崗位與領域的人才和棟梁,依然是時代的呼喚、社會的呼喚和人民的呼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