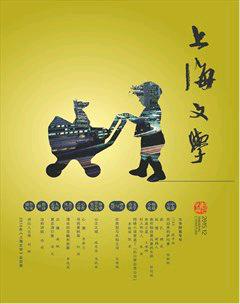夏志清印象
◎陳九
夏志清印象
◎陳九
說“夏志清印象”的確只談印象。見過面,吃過飯,聊過天,肯定有印象。這個印象是對他本人的,不是他的觀點,不是學術評論。這么說并非我矯情,我很慵懶,如果談夏先生學術貢獻就要翻很多書,查很多資料,還得裝得像個學者,選詞用句小心翼翼,那就沒意思了。我喜歡隨心所欲,只談感受,寧可膚淺也不為難自己。學術評論又不是我強項,人家自有一套,我不摻和這事,我與夏先生私下聊天每次都很愉快。
每次就不止一次。紐約是個大碼頭,誰都要來紐約走走,尤其是文化人。胡適來過吧,他與杜威(John Dewey)、孟祿(Paul Monroe)等人在此創建了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這是美國最早,以溝通中美文化為宗旨的非盈利組織,就坐落在曼哈頓東65街,中文匾額即為胡適所書,字如其人,清秀柔弱。徐志摩也來過吧,這位中國近代詩歌奠基人,曾在成立不久的華美協進社朗誦自己的詩篇。順便一提,1982年我在上海畢業實習,只身跑到徐志摩海寧的老家憑吊。當時那棟老宅還不是展館,門戶深鎖四下無人,我站在門外很久,不說話。還有作家老舍也曾在紐約逗留,住西83街,并在那里寫下很多作品,包括我中意的那篇《正紅旗下》,他在這里曾與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交往,賽女士喚他“舒先生”,說他是個不喜歡美國食物,很靦腆的男人。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保不齊在哪兒都能撞到。除文人外,前清遺老、退役封疆、世家子弟、演藝名流,很多都在紐約留下過足跡。不久前我去一家叫“白珠”的餐館吃飯,都說那里風沙雞做得好,發現隔壁有位老太太舉止不凡,上前一聊,竟是馮玉祥家人。還有一次我也在華美協進社朗誦詩歌,下面有位年長女士風采奪目,經介紹方知是郁達夫的兒媳。還有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的遺孀、愛新覺羅氏的金王爺、青海馬步芳的后人、筧橋航校的少將教官、“兩航起義”的上校駕駛員、前中央金庫駐紐約襄理。看過《北平無戰事》嗎?你會情不自禁覺得里面的后人都在紐約。中國近代史離不開紐約,像抒情散文離不開刪節號、啊……,中國是“啊”,后面的歸紐約。
我就在這個“刪節號”里遇到夏志清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在當地華文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詩歌,惹人矚目。有個叫海鷗的大姐找到我,一是索要我的詩歌,二是介紹我加入“海外華文作家筆會”。該筆會于1960年代由夏志清、唐德剛、李金發等人創建,是海外唯一加入“國際筆會”的華文文學團體(中國作協也是“國際筆會”成員)。那是個春日晌午,我按通知趕往曼哈頓中城一家中餐館,海鷗大姐已在門外等候。她帶我進去,逐一介紹給在座的作家。我一看不得了,都是大牌,夏志清、唐德剛、董鼎山、鄭愁予、王渝、叢蘇、趙淑俠、殷志鵬,我說不全,眼花繚亂。其中董鼎山先生我了解較多,上大學時就讀他發表在《讀書》雜志上的隨筆短章,非常喜歡。不過最終落座,我有幸被安排在夏志清先生身旁。與這位譽滿天下的學者并肩而坐,我一時不知該說什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本架構深受夏先生那本《中國現代小說》的影響。尤其在中國擺脫意識形態束縛的新時代,是夏先生這本書填補了理論“空白”,比如對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的評價,中國文學界至今仍較多采取“夏說”。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幾人曉得張愛玲喲,聽過這個名字就不錯了,到哪去找她的作品啊?正是夏志清這本書把張愛玲等人引入現代文壇,演變成今天的新常態。
沒想到夏先生的提問打破了“僵局”。“你叫陳九,家里行九嗎?不是說大陸不許生那么多孩子?”夏先生江浙口音,語速較快,且不拘辭令,讓人感到他是個思路敏捷坦誠灑脫的性情中人。我解釋道,陳九陳酒諧音,而陳酒太過直白,故以陳九托之,我出生時并無人口限制,即便如此也很少有生九個的呀。夏先生微笑著,他面色紅潤,兩個顴骨微微隆起,紅潤正從那里漫出身外。他的衣領很白很亮,漿挺著,反倒讓膚色略顯沉著,眼睛上戴著無框眼鏡,鏡片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明亮得像個童子,閃耀著他充沛的精力和鮮明個性。他說我的口音是純正京片子,當年他在北京住過,一聽就聽出來了。還叫唐德剛趕快聽聽,“喂,你那個安徽腔改得掉吧,誰聽得懂,所以你最好不要講話,不要講話。”他邊說邊做鄙薄狀,搞得對面的唐先生滿臉尷尬,全場笑成一團。
文壇一提夏志清必言所謂“唐夏筆戰”,指的是當年發生在夏志清、唐德剛之間,關于如何評價中國近代小說文學地位的爭論。夏先生認為西方小說在創作技巧上優于中國同類。而唐先生堅稱中國文學歷史悠遠自成體系,毫不遜人。兩人筆戰甚喧,只殺得呼啦啦天昏地暗,成就了文壇一樁趣聞。如果只看文字,好像唐夏二人仇敵一般,我過去就有這種誤解,文人相輕嘛,一旦撕破臉很難收場。而此刻見到唐夏本尊,才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好著呢,交杯換盞吃嘛嘛香,相互調侃心照不宣,畢竟是同代人,又相聚于紐約這個大碼頭小天地,僅憑對華文文學的執著就足以抵擋任何不同觀點,仿佛現在的北極熊,聽說數量急劇下降,如果彼此偶遇,再怎樣也得多看幾眼吧,那是你的同類,錯過可就見不到了耶。原本覺得唐夏之爭是兩個神仙論劍,蒼茫遠古與史識靈性鑄就了彼此的長劍,壯士出山劍氣如虹,笑傲江湖的日子舍我其誰也?而此刻在這間熾熱的店堂,看著兩位不再年輕的大師依舊像年輕人一樣“好勇斗狠”,不禁感慨得春暖花開,他們才不是什么神仙,而是兩位充滿熱情的人類在分享生活,有熱情有靈性的人類比神仙幸福多了。還需一提的是,早在1986年10月《中國時報》就有報道說:“喧囂海內外的唐夏之爭,數天前已告結束。據聞,10日晚上在紐約文藝協會的一次宴會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盡棄前嫌。”誰能告訴我這個“文藝協會”指什么?我做過核實,就是上面提到的海外華文作家筆會,當時情景必與此刻我跟夏先生的相遇差不太多。耶!
我趕上的海外華文作家筆會或許不勝當年火爆,當年像夏志清、唐德剛等文壇才子正值風華并茂,又無名氣負擔,自由揮灑。名氣不單是正能量,更像達摩克利斯劍懸于頭頂,好壞全憑天意。到我加入的時候,筆會依舊十分熱鬧。夏先生一代已功成名就,但仍充滿活力。接下來還有王渝、叢蘇、趙淑俠、陳楚年等中興代作家,他們在海外文壇的影響亦不可低估。那時我們每月一聚,地點多在曼哈頓中城,因夏志清、董鼎山等前輩都住在曼哈頓,方便他們出行。副會長顧月華充當召集人,她是上海人,又是名副其實的美食家,與中城諸多菜館頗為熟悉,她選的菜式好吃又好看,還不貴,每人均攤不超過二十美元。店家每每為我們辟一方安靜所在,有時還奉送兩支紅酒,一片殷勤。我們常去的館子有杏花樓、萬壽宮、憶香園,以本幫菜為主,估計這與夏志清、董鼎山等均為江浙人不無關系。煙雨江南云蒸霞蔚,是才子輩出之地,這種特征也蔓延到海外文壇,筆會中不少作家來自那里,像陳楚年、殷志鵬、李亦飛等。我愛用方言與他們打趣,雖然我是典型北京爺們兒,二鍋頭炸醬面,但喜歡模仿外地口音,“得哩得哩吵瞎磨,額去勸勸得,得哩刮達額,額心里想想啊難各”,這是我學的一段常州俚語,我們經常這樣開玩笑,夏先生也難免卷入其中。他說我講的南方話是“洋涇浜”,還說北方人舌頭硬,拐不過彎兒,但腔調嘛還可以。與夏先生的相遇漸漸演變成賞心悅目的空氣,流行話叫氛圍,氛圍其實就是感覺,很難說清,也很難忘掉。
夏先生并不是每次都參加筆會活動。但只要他在,氣氛便不一樣,大家會高興很多熱烈很多。我們往往圍繞某個主題開聊,比如朗誦自己的新詩,介紹新書,或談論當下熱門話題。記得七八年前一個冬日,我們在萬壽宮聚會,夏先生由夫人王洞陪同參加。我依稀記得他進門脫大衣的情景,衣服尚未脫下聲音已傳了過來。
那次是討論李安剛剛完成的新片《色戒》。該片由張愛玲的小說改編而成,既然張愛玲就不能不夏志清,夏志清是張愛玲作品的權威已是公認的事實,我們當然希望聽到他的看法。關于這次聚會我無意間做過日記,是這樣記載的:“夏先生看上去很健康。席間談論李安的《色戒》,夏先生說李安曾找過他,希望給予支持。但他未做過什么,也沒說過什么。他認為這部戲色情成分過重,并無必要,他不覺得這是李安的成功作品。叢蘇對李安的《色戒》持否定態度,認為其色情部分是一大敗筆。她認為電影的社會影響較大,必須考慮到這一因素。王渝則對《色戒》持肯定態度,她認為李安作品第一在乎觀眾,第二人性化,是他作品的突出特點,對色情不必大驚小怪。董鼎山先生對《色戒》的色情部分也不以為然,他認為過多的色情渲染會把英雄人物庸俗化,并不合適。談到張藝謀,夏先生認為他后期作品不可看,太空洞,前期還湊合。談到作家哈金,夏先生說他的語言太過簡單,內容比較平淡,最近《紐約時報》的書評正在變差。后來上菜時,夏先生表明他不吃米飯,想要意大利面條。可惜店家沒有,遂以上海炒面代之……”
日記內容不光這些。但你不覺得那種自由氣氛和身臨其境的感覺更重要嗎?紐約是個海納百川的“世家城市”,它的歷史雖然無法與萬里長城相比,但它從不折騰自虐,而是珍惜每一滴歷史榮耀,并帶著榮耀一路前行。沒有自尊便不懂珍惜,沒有珍惜就沒有積淀,沒有積淀何談文明的分量?一個文明的地位與歷史長短基本無關,而取決于文化的自信度。紐約正是靠日積月累的榮耀,使它成為巨大的參照系,讓一切所謂成功或偉大在這里只能以最真實本性的狀態呈現,否則便會尷尬。離開真誠,任何成功偉大都虛偽渺小,在與夏先生的接觸中我清晰感到這點。他侃侃而談,喜怒哀樂皆形于色,真實坦然,既不神秘也不遙遠。我相信所有成功者都應是平凡的,只有平凡中的個性才更可信,更具感染力。比如夏先生在上海菜館要意大利面,聽著很奇怪,這或許正是他的率性所致,特立獨行,善為人所不為。甚至對張愛玲的評價都可能有他個性的烙印,是他個性的物化。他本人是學英國文學的,來美后遍覽美國文學作品,審美體系豐富且多元,故而才石破天驚敢為人先,用獨特眼光將張愛玲引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令主流刮目相看。連夏先生自己都調侃說,他“使張愛玲成為偉大作家”是有點“離經叛道”。
我多次見過夏先生,但很少聽到他正兒八經談論張愛玲。最多一次是在他那本《張愛玲給我的書信》出版前后的筆會聚餐上,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他。當時我并不知夏先生正在出這本書,是從他與周邊人的對話中曉得的。我知道這不是件簡單事,因為涉及隱私,出版這種書需要勇氣。文學的確需要勇氣,像所有杰出必須有犧牲一樣,文學的杰出也不會平白無故,首當其沖就要面對自身的“清譽”,你能否將文學追求超越于自身的真實?這對任何作者都是考驗。早就聽說張愛玲與夏先生間有書信往來,坊間甚至有關于夏張關系的流言。可當親耳聆聽夏先生閑談張愛玲后,我相信他們之間就是君子之交。夏先生的神態平淡超然,目光很純粹,毫無閃爍或遲疑,任何有些閱歷和判斷的人都能感到他心中的坦蕩。他說他對張愛玲一直很客氣,語言分寸都有把握。還說張的孤僻已到根深蒂固的程度,連夏先生請她吃飯都不領情。反過來,夏先生卻盡力幫助陷于窘境的張愛玲,協助她在北美發表作品。他在談論張愛玲這個作家時,對她的肯定干凈利落毫不猶豫,始終認為她是優秀作家。但當涉及張愛玲本人時,我記不清他用過多少積極的詞匯,我的日記中也缺乏這樣的記載。我的基本印象是,夏志清是夏志清,張愛玲歸張愛玲。夏志清對張的肯定來源于他的學術判斷。而張愛玲的可悲結局則是她個性和心理狀態的產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
寫到這里一聲輕嘆,方感斯人已逝情景成昨。
不知你有沒有這種感覺,當某個熟悉的人駕鶴西去時,我們才真正開始回味他的價值,音容笑貌,他的生命分量,才開始珍重與他接觸的時光。想起與夏志清的偶遇,我心里確有“揮霍生命”的遺憾。如果那時能與他多聊聊,或許我對中國現代文學會有更逼真的理解。一切都已無法更改,無法更改的事叫緣分,緣分大小皆由天定,強求不來。所以我談的只能是一些淺薄印象,對夏先生的印象,文人稱作一瞥,目光所及,尚未清晰已飄然而去了。我坦誠說出自己的感受,并以此表達對逝者的尊敬,對生命過往的珍惜。這是我虔誠的企圖,只是不知做到沒做到。
愿夏先生安息。
2015年6月8日記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