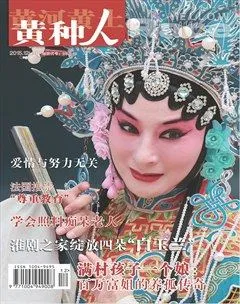懷想家書
張月軍
很長時間沒有給年邁的父母寫一封像樣的家書了,內心的失落和悵惘不言而喻。現代通信設備的高速發展,使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方便和快捷了許多,只要撥一串阿拉伯數字,你就可以聽到遠方親人的聲音;只要你樂意,你就可以和電話那端的親人盡情地煲電話粥。可是,家書卻漸漸淪落了,遠在異鄉的我曾經是那么迷戀溫馨無限的家書。
在18歲以前,我對家書的理解相當膚淺。我行走在故鄉的天空下,同血脈相連的親人住在同一個屋檐下,過著閑適的鄉間生活。直到我考入大學在異地讀書,家書的旅程才伸展開來。不過那時,我給父母寫信無非是希望家里寄些錢來。我亦時常收到父親天書般的來信,盡管錯字連篇,我還是讀懂了蘊含其間的親情。也正是從那時起,家書的魅力感染和征服了我。
我真正理解家書的含義,是走上工作崗位以后。也許因為我身在西北邊城,難得回一趟老家同親人團聚,也許因為生活中的諸多困擾,我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鋪開潔白的信紙,傾訴對親人和故園的無盡思念。當我把一封封家書塞進綠色郵筒時,我感到潮水般的思鄉之情,正順著漫漫的詩意般的郵路,一路歡鳴著向故鄉的方向奔涌而去……當然,在異鄉的天空下,讀親人的家書,總會讓我在激動不已中,兩眼盈滿滾燙的淚水。盡管讀父親的信相當吃力,但我還是一字不落地從頭讀到尾,然后將父親的來信整齊地收藏在抽屜里。通過家書,我踏上了一條抵達故園曼妙而幽靜的蹊徑;通過家書,我可以和遠方的親人進行一次次心靈對話與交流;通過家書,我可以化解堆積在靈魂深處的鄉愁。
在漫長的玫瑰般歲月中,家書給我這個浪跡天涯的游子以極大的精神慰藉。
當我調到煙雨蒼茫的南方時,電話和手機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伴隨信息革命的到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變得頻繁密集起來,但因為缺少了期待,也就失去了詩情畫意以及在等待中的那份焦灼和等到后的那種欣喜若狂。不過那時家里還沒有電話,我繼續寫家書,給老家的父母帶去情意綿綿的思念和牽掛,我沐浴著家書溫暖的陽光和皎潔的月光,我感到我生活得如此充實。有家書陪伴的歲月,像一瓶剛剛啟封的陳年老酒,讓我沉醉與玩味;像許多鮮艷的浪漫的春花,芬芳無限地綻放在我心之曠野上。但家書和情書一樣,已經成為一種落伍甚至被逐漸淘汰的表達方式。我是說,當家中裝了電話,父母會隔三岔五地打來電話,家里的大事小情,甚至親人有個頭疼腦熱,我都會了解得一清二楚,對于老家和親人,似乎已經沒有懸念可言,而曾經的牽腸掛肚的思念也似乎淡化了許多。在拿起話筒的那一瞬間,我知道父母就在電話機旁,我知道我可以格外清晰地聽到父母蒼老的關切的聲音,可是,怎么說呢?握著話筒,我似乎進入了一種失語的狀態。我是說,那種情真意切的深層表達,是不可能通過電話來表述的,于是我想到了被我遺忘和冷落了的家書,想到了古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那種扣人心弦的快慰與激動,想到在許多流逝的時光中,家書曾經以春風化雨的無窮魅力,溫暖和滋潤了游子的心。
今夜,傾聽窗外雨打芭蕉的聲音,我是應該給遠方的父母寫一封像樣的家書了,我鋪開潔白的信紙,任情感河水般流淌,我知道,那是我對親人和故園的思念,是對家書的獨一無二的表達方式的捍衛與堅守。我想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多寫幾封發自肺腑的意味深長的家書,以撫慰走向暮年的父母孤獨的心……我還要和家書相伴而行,我知道我的捍衛與堅守,源于親情和無法割舍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