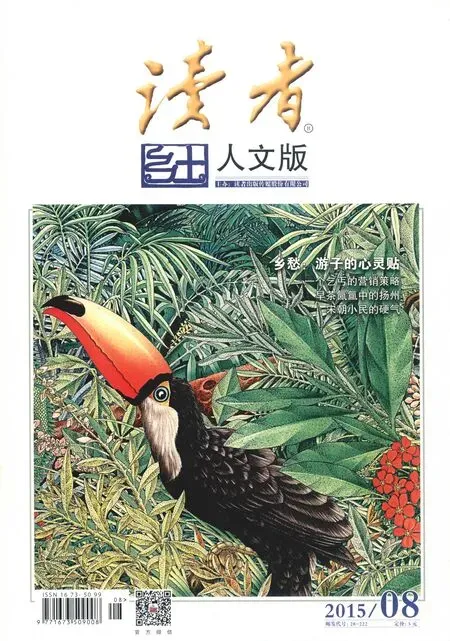舊的城
文/周 沖
舊的城
文/周沖

戲、旗袍、人力車。
寫下這三個詞匯的時候,舊上海洋場的風塵味撲面而來—20世紀30年代的女子,抹著厚厚的胭脂,盤著愛司頭,帶著形銷骨立的命運,由年輕或不再年輕的三輪車夫拉著,趕赴一個秘密約會。上海大劇院的廊柱下立著一個男人,吸著煙,眼睛看著她,遞過來一包微熱的糖炒栗子。
然而在這個夏天,我得知了這三個詞的另外一種解讀方式—武寧。運西瓜的小貨車一輛輛地駛過,花傘在膨脹的陽光和雨水中盛開,水豆腐、裁縫店的老皮尺、渡口的風、竹椅和楊梅果,積銖累寸地設計著葳蕤的小城生活,風情萬種,流光無限。
最早的光明,由一輛人力三輪車載來。
穿著白汗衫的車夫,搖擺在車蹬上,響著長鈴,在大葉女貞的陰影里一閃而過。灰色斗篷里坐著面目模糊的女子,寂靜地看著可看可不看的風景,想著可想可不想的心事。時間輕輕游移,戾氣盡消,“吱吱嘎嘎”的轉輪聲中,一只手從斗篷中探出來,掠過雨后的紫荊花。
黎明被車鈴喚醒,小販張檐支攤,出售微笑與好生活。銀行的男職員帶著兩只熱艾果,在上班途中邊走邊吃,滾燙的甜汁流出來,他撮圓了嘴,倒吸氣,咂咂舌頭。孩子念著“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誰不憶江南”,跑過水門汀的小巷,小書包像雛翅般在身后撲閃……細節活色生香,乘坐著人力車一一經過,就像經過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詩。
成年以后,途經許多城市,它們姓名各異、經緯不同,但都被科技與速度錘煉成孿生子。沒有哪一座城如武寧這般念舊,寬待歷史,寬待記憶。人力車是無聲的證明。它們帶著舊風塵,在小城的街道拐角攬生意。只要三四塊錢,你便可以坐在起伏的背影上,去往想去的地方。
風在下坡處恣意地越過,像老中醫的手安慰著皮膚,人的眼睛舒適得瞇起來。上坡的時候,車夫跳下車,一手持車把,一手拽車后的椅柱,人弓成45度,奮力爬行,如負軛勞作的牛。
到達目的地,人們下了車,離去了。車夫轉道而行,載上新的活計。他們低著順命的眉眼,在風里咬嚼一只白地瓜,車子橫梁上系著的錢罐子叮當作響,斗篷的荷葉流蘇一漾一漾,他們覺得知足。正午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的車斗里打著盹,白煙卷在指間幽幽燃著,積灰一截截斷落,落在車子的踏腳上。
人力車—舊上海與小城在這個詞里達成某種默契,內部風起云涌,算盡機關,表面卻不動聲色。就像悲喜無常的夜里,人力車急速而過,都看到了,看透了,表面卻像什么也不知。
就這樣蹬著蹬著,車轱轆一轉,五月過去了。廣玉蘭俯下身來的時候,旗袍開始在街巷間熙來攘往。白絲緞的底子上繪著小花,邊緣咬著藍絲線,繩絡結扣,風情昭然。低眉順眼的姑娘,披著濃郁的長發,在古艾湖的邊緣走過。

北方是穿不得旗袍的,太粗糙了,太蒼茫了,絲綢單薄的料子一落地,就要被糟蹋。都市也成不了旗袍的背景,燈紅酒綠、明槍暗箭的世界,一切都在進攻,在索取,矜持成為不懂風情的代名詞,旗袍的韻致風干了,像狼狽的絹花。
唯有武寧這樣的小城,像屏風一般,提供古典的底色。安分的、多情的、有故事的、入世又出世的,脾氣相近,像是天作之合。
青磚圍墻的小門打開,穿粉色旗袍的姑娘走出來,發髻微墜,她叫住賣菜人,在板車里翻揀,紅番茄、綠辣椒、黃萱花、白米糕,質地素凈,色彩繚繞。她想到晚餐的清爽饜足,抿嘴一笑。
也有不再年輕的女子,在黃昏的葡萄架下,翻看一只蒼老的紅箱子。隔年的旗袍已經皺了,時光這張大網,沒有因為它的精致而心生惻隱。她捧著它,想著多年前的千回百轉,那輪月,那個人,那些沉默與灼燒。此時的墻外,有人吹起響亮的口哨,騎自行車的男孩,像白鳥一樣飛過。
如同人力車,旗袍在這里也出奇地興盛。曾在古艾河邊坐著,打量過往行人,計算這種服飾的穿著率,發現十有二三。她們回家,約會,穿過長長曲徑去看一折戲,聽傳說如何落到人間。
來歷不明的花鼓戲班,在這個六月,在午后和夜間,咿呀唱響。古艾河邊的青磚白瓦、長藤野蔓,一下子加上了柔光,然后,眠在一片輕盈的宋詞里。
我不知道戲班子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也不知他們將在這里停留多久。我只知道在來到這座城市之后,他們就一直在這里,拈袖拂巾,橫波媚眼,蘭花指在空中游來游去。
旦角穿紅,花滿鬢,云滿裳,珠粒巍巍搖,眉心點朱砂;生角著青,戴著大沿檐,更像水上討生活的漁家。兩個人在臺上互相抬舉,用牛郎織女作譬喻:“我把你,比牛郎……”“我把你,比織女……”充滿暗示的挑逗,在空氣中來來去去。唱著唱著,水到渠成了,互喊夫或妻。“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哇哈羅”,“劉大哥,你是我的夫哇哈呀”,終身已定,以后生死都要相依。傳說里的愛情,總是簡單、不費事,輕松得令人不敢相信,但大家喜歡,喜歡這種花團錦簇,祥光普照。
“你帶路往前行啊,我的妻你隨我來行啊,得兒來得兒來……”臺詞時頓時起,鑼鈸響聲陣陣,填滿唱詞的間隙,三兩個換戲服的戲子站在沒有幕布遮攔的后臺,毫無顧忌地解扣寬衣,赤裸的胸膛露出,隱約在觀眾的視線之內。他們的臉與身體形成鮮明對比,一邊白得刺眼,一邊黑得醒目,像謝必安與范無救。紅色道具箱里擠著算盤、折扇、長髯、須鞭、珠花、胭脂,長鐵桿上吊著戲服,花花綠綠一大堆,取盡了人間最鮮艷的色澤。
螟蛾般的人們,被燈光吸引著,簇擁在四周。小孩鉆來鉆去,姑娘顧盼生姿。老人坐在自家的小板凳上,搖著蒲扇,盯著戲臺,一邊交換對劇情的意見:“哎呀,真可憐哪!”“寧拆一座廟,不拆一門婚,你搗什么亂呢?”“這婆娘也真狠心!”賣玉米、涼粉、咸水花生的帶著小馬燈,在角落里守株待兔。他們的籃子上半掩著白包袱,白包袱上倚著一只長長的木勺子。
我忽然非常感動。這樣的戲,這樣的人,這樣的水波與夜晚,彼此融合著、呼應著,成為小城的外部的光彩,內部的柔情。除了它,還有什么能成為小城的胭脂與花鈿?除了它,還有什么能成為寂寞夜光的羽衣?除了它,還有什么能成為當地最好的柴火與藥引,給予它綻放和療救?
看戲回來的時候,穿過這些日常歡喜,對身邊人說:“生活這么好,我們要相愛。”
(馬 鐘摘自豆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