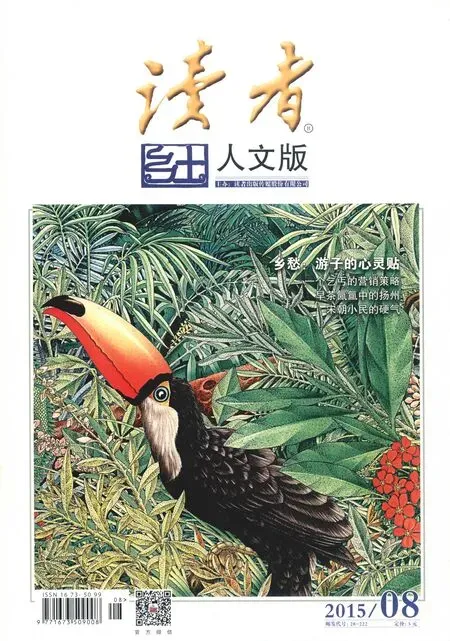母親的風干菜
文/李光彪 圖/夢沙丘
母親的風干菜
文/李光彪圖/夢沙丘

在城市,千絲萬縷的風飄過,幾乎沒有多少人在意。
在鄉村,風有時很溫柔,有時也發點脾氣,扯斷莊稼,折斷樹枝。就像一匹馬,乖巧聽話時任人騎耍,討人喜歡;烈性發作時,則令人束手無策。
而我的母親卻像馴養豬雞牛馬一樣,善于駕馭鄉村的風,借風風干很多菜,以保證缺菜季節全家人桌上有菜吃。
秋季,是鄉村大豐收的季節,也是母親“大風干”的黃金時節。
母親做的風干菜很多,首先是從風干茄子開始的。那些紫色的茄子,幾場雨水過后就會掛滿枝頭,吃不完就會很快老去,母親便會選個晴天,把那些鮮嫩的茄子一籮籮摘回家,切成片,一篩篩晾在柴堆上。幾天后水分曬干,將干茄片收拾歸家,便可日后煮著吃了。
轉眼,那些間種在苞谷地里、菜園地埂邊的豇豆,仿佛一枝枝婀娜多姿的柳條,一串串鼓著青黃的肚子,簇擁著問候秋天,捎來收獲。放學回家,我常背一只小竹籃跟在母親后面,有時去掰苞谷,有時去摘豇豆。搬回家的苞谷堆滿院子,晚上全家人分工合作,一邊撕剝,一邊像辮頭發一樣辮起來,掛在屋檐下。有時苞谷太多,只好在院子里塔個架子,把苞谷一串串掛在上面,任風吹雨淋太陽曬,要吃或要喂豬喂雞時,再下辮脫粒、碾磨。摘回家的豇豆被我們一一掐斷,去筋后就被母親盛入簸箕、篩子,放在屋外邊晾曬,曬干后收進家,缺菜時,與臘肉骨頭煮著吃,十分可口。
辣椒是家中一年四季天天吃飯都少不了的調料。那些火紅的辣椒被母親摘回家,用稻草一串串編成項鏈形狀的辣椒辮子,掛在屋檐下。此時等待風干的辣椒辮子,和苞谷辮子成了家里一道特有的風景,呈現五谷豐登、糧食滿倉的景象。尤其是那些后來補種的苞谷,收獲時總是不成熟,只能吃青,吃不掉的母親便用水煮,然后讓我們一粒粒脫下,晾曬成“陰風苞谷”。“陰風苞谷”吃時像花生、蠶豆一樣用油一炒,又香又脆。那些騰地時摘回家的嫩辣椒也不例外,被母親風干后,用油一炒就成了下飯的“陰風辣”,既可口,又開胃。
秋天的鄉村,是蔬菜最豐盛的季節,一時吃不完的全被母親風干,做成了干菜。就連那些我們摘回家的蘑菇,全被母親揀洗干凈,晾曬成干蘑菇,啥時想吃,再用水浸泡,即可炒著吃,也可煮著吃。
轉眼入冬,母親又開始風干另一種“干板菜”。她把那些辛辛苦苦種成的青菜、苦菜一籃籃弄回家,青菜做成腌菜;苦菜則洗干凈,放在燙水里一焯,趁熱掛在晾衣服的鐵線上,或掛在屋檐下的竹竿上,一批一批風干,收藏。
除了這些,母親風干的菜還有臭菜、蕨菜、蛤蟆葉、白刺花、棠梨花、大白花、烏鴉花、香椿芽等。只要是能吃的菜,幾乎都被母親逐一風干,調理成全家一年到頭的美味。每年夏收季節,一方面少雨干旱,一方面蠶豆小麥要收,水稻、苞谷、烤煙要栽要種,顧不了菜園,所以是最缺新鮮蔬菜的時節。這時,那些母親早已備好的風干菜就派上了用場。

母親風干的菜,也曾撐起過我們家不少面子。有客登門,新鮮蔬菜不足,母親就會用風干菜來彌補,招待客人。家里哥姐娶嫁,殺年豬辦喜事,總是有幾道風干菜做配角、湊碗頭,擺得桌子滿滿的,辦得有臉有面。按照鄉村的風俗,不論是誰家辦紅白喜事,既要互相幫忙籌備,又要互相送菜,把一家人的事當作大家的事辦。母親有時送新鮮蔬菜,有時送風干菜,總會盡力幫助人家圓滿完事,有口皆碑。
正是母親傾心做的那些風干菜,讓我度過了那段缺吃少穿的歲月。如今,離開鄉村棲居城市已二十多年,我時不時總是能吃上母親從老家帶來的風干菜,雖不新鮮,卻讓我品嘗到一縷來自鄉村的風的味道,享受到一縷來自鄉村的風向我的問候。
(三月風摘自云南民族出版社《母親的氣味》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