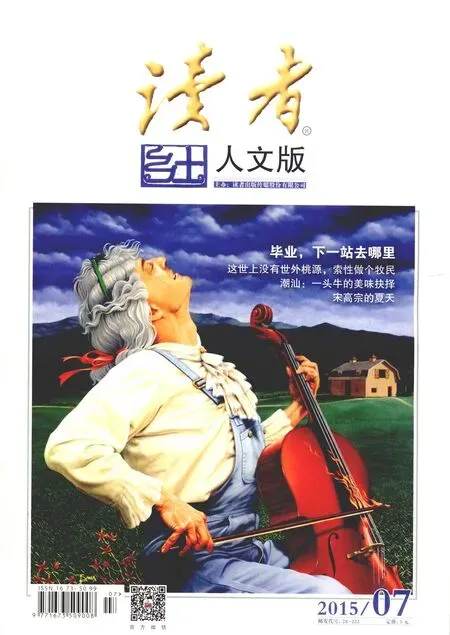圍攏在父母身邊的日子
文/兔子老愚 圖/郭德鑫
圍攏在父母身邊的日子
文/兔子老愚圖/郭德鑫

在我生長的年代,家是父母用盡全力從土里拱出來的棲身之所。土墻瓦房,磚頭和木頭是叫人稀罕的玩意兒,甚至連牙膏皮、包裝紙都讓人眼前一亮。在這樣一個用黃土筑起來的院子里,有土炕和土鍋灶,日子便能過下去了。與土的間隔僅僅在炕上,用席子把身體與泥土抹平的炕面隔開,若能就著煤油燈讀一本沒書皮的小說,我就很有幸福感了。
全家人最珍視的寶貝是糧食,在上房頂樓上做成糧倉,四周用席子包起來,沿根腳撒上老鼠藥。夏秋兩季,把隊里分下來的麥子、玉米一麻袋一麻袋吊到上頭。吃糧時,再一斗斗提下來。院子里打了地窖,存放紅薯和白蘿卜。歉收年月,連玉米芯、紅薯秧子都要儲存起來。
父親在院子四角各種了一棵泡桐,我負責(zé)每天澆水。
豬是最舒服的,每天在圈里“哼哼”著要吃的,幾只母雞下完蛋“咯咯咯咯”地叫喚著向主人邀功。
老鼠夜里出來,它們躲在廚房的案板下,有的鉆進風(fēng)箱里,弄出“窸窸窣窣”的聲響。我一跺腳,它們便安靜了。
梧桐枝丫伸開,便有鳥駐足,不時掉下氣味熏人的排泄物來。據(jù)說,屎掉到誰頭上,誰就會有霉運,弄得誰也不敢往樹蔭里去。
有一年,來了一對喜鵲,它們來回打量了上房屋檐幾圈,決定筑巢安居。一家人面帶喜色,走路說話都壓低嗓門,生怕驚動了貴人。喜鵲夫妻嘰嘰喳喳,嘴里銜著從地里撿來的細枝,進進出出,仿佛一對心里盛滿喜悅的可人兒。
家里也有神靈。母親在上房東屋侍奉了神仙,香火長年不斷。木刻的神靈,到夜里便讓我害怕。好多次,我感覺他們有了生氣,睜開眼,從墻上走出來,躡手躡腳朝我撲過來,甚至把手放到我的脖子上。
最欣喜的是薄暮時分。一家人坐在院子中央的石桌前,中間往往擺放一碟涼菜,涼拌胡蘿卜或白蘿卜絲,無非是澆一勺醋,放半勺辣椒。母親把稀飯和饃挨個遞到大家手里,等父親夾起一筷頭菜后,我們才敢伸出筷子。很快,就響起“吸溜吸溜”的吞嚼聲。
那時候無人說話,生怕一張嘴,好味道就溜走了。因饑餓而來的幸福感,就在這無聲的響動里。碗一定被舔得干干凈凈,如果誰有未吃飽的表示,母親就從自己的碗里倒一些,或者把手里的饃掰一塊遞過去。她總是最后一個吃,吃得很慢,現(xiàn)在想來,應(yīng)該就是在等孩子們的呼喚。
飯后喂豬,我和大弟弟將豬食抬到豬圈里,還未倒進食槽,豬就撲過來。中午放學(xué)回家,我會習(xí)慣地把手伸進雞窩,一般會摸到一枚蛋,運氣好時會有兩三枚。這些雞蛋大都賣給了城里人,母親只把那些品相欠佳的留下來,在誰過生日時煮熟臥在碗底下。
夜里,村子安靜了。勞累一天的人和牲口都疲乏了。我們幾個就著煤油燈,讀讀課文、寫寫作業(yè),就熄燈睡了。起夜時,月色正好,父母的呼嚕聲有節(jié)奏地呼應(yīng)著,好像眉戶戲里的男女對唱,讓人踏實。
近幾年,想家了便回去,可當(dāng)與父母睡在一個屋子里時,浮上心頭的卻是難言的滋味:日子老了,父母終將會離我們而去,一次次見面不過是人世的一次一次告別罷了。
(元 知摘自兔子老愚的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