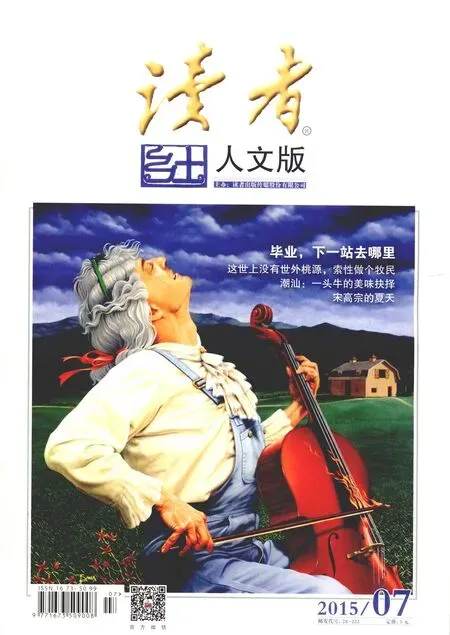你的胃會告訴你哪里是故鄉
文/七堇年 圖/邵曉昱
你的胃會告訴你哪里是故鄉
文/七堇年圖/邵曉昱

一
我曾經是一個在吃東西這件事上讓人頭痛的孩子。
1歲的時候,我家的陽臺正對著長江。據我母親說,為了給我喂飯,她必須用左手抱著我,同時拿著碗,右手舉著勺子,站在能看見江景的地方,哄我:“快看呀,輪船來了!”趁我一高興對著輪船發出“哇……”的叫聲之前,趕緊舀一勺食物塞進我嘴里—不用這種把戲,我根本不肯張開嘴。
4歲的時候,幼兒園里每到吃飯時,老師便拎一個灰色的大鋁桶,裝一桶清水白面,拿一個鐵勺舀出來,“啪”一聲倒進碗里,喂給我們。我想不通為什么別的小朋友可以吃得那么香,而我永遠難以下咽,老是吃到最后。老師急得要死,忍不住親手喂我,眼看快喂完的時候,我實在受不了,“哇”的一口全吐了出來。
步入青春期,大約是因為身體開始發育,我的胃口漸漸變好了,飯量增大了不少。
記得在香港讀書的那一年,學校食堂的菜量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少了。一般我會吃一個三明治、一碗米線,再加一碗叉燒飯才能飽。有一天,一個很斯文的女同學看著我吃完了一個三明治,又捧起了一碗米線準備下口。她驚叫起來:“你吃這么多啊?”我被嚇了一跳,抬起頭來,無辜地望著她,說:“我還沒墊著底呢,一會兒還有一碗叉燒飯……”她那個無比復雜的表情我一輩子忘不了。
后來我開始意識到,“胃口好不是你的錯,出來嚇人就不對了”,于是,我不再去食堂吃飯,轉而去市場買菜,自己做著吃。我買了一個電飯鍋,在宿舍里自己煮東西吃。條件有限,我是將就著電飯鍋的內膽吃飯的,這意味著我的飯量是論鍋算的。
二
2012年,有一批意大利學者來我工作的實驗室進行訪問,他們要待三個星期。在用餐的時候,我每次都親自給他們點清淡的、不辣的、鮮美的中式菜肴,我知道他們不能吃辣。
但吃了兩天中國菜之后,他們就紛紛問我,哪里有肯德基、麥當勞,只要有薯條和漢堡就可以,不奢求其他。那天我簡直太失望了,我想不通,跟那些垃圾食品相比,這么好吃的精致菜肴你們都吃不慣?我簡直有一種“山豬吃不了細糠”的憤慨。
但后來我理解了,世上本沒有最好吃的食物,吃習慣了,也就成了最好吃的食物。那是你從小到大就習慣的味道、你的記憶、你身體的故鄉。
2014年,我不時會去北美住兩三個月。北美風景好、空氣好,人有禮貌,城市整齊有序,但“總有一種味道,以其獨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著我們,認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來處”。
召喚我鄉愁的不是別的,正是我的胃。在北美吃的食物都是有機的、無毒的—新鮮綠色的健康沙拉、全麥面包、放心牛肉,可我想吃燒烤都想瘋了。像哈金《自由生活》里寫的那樣,奶酪對我來說簡直就跟肥皂似的。每次回國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直奔那個“朱師烤全茄”的攤子,點兩串烤茄子,要一盤掌中寶、雞脆骨之類,痛痛快快吃一頓。第二天一拉肚子,整個人就神清氣爽了。
三
回國后,我一般會很快把朝思暮想的燒烤、火鍋、川菜吃完一輪,這樣我也就很快適應了我曾經很適應的種種:在馬路上開車,人們會任意變道加塞;稍微堵一下車就狂按喇叭,好像這樣就能飛起來似的;大人們在馬路邊毫無顧忌地掰著小孩的屁股撒尿甚至屙屎;處處人山人海,高聲喧嘩……
那天,我把洗好的床單拿到樓頂上去晾,順便俯瞰這座一片灰蒙蒙的城市。那霧靄重重,看不見落日也看不見朝霞的天,白了又黑了,如此熟悉。那一刻,我的心情像是凝視一位久別重逢的舊愛,這是我所熟悉的糟糠之妻。我想起不久之前遠在地球另一邊的日子,那一度是我的新歡。是的,新歡很美麗、很年輕,干凈、優雅……可是,生活在這里與在那里有什么區別呢?
一樣需要洗衣機、冰箱、空調;需要去超市買牛奶、雞蛋、衛生紙;需要那幫老朋友和那幾個常去的老館子,菜端上來,該要醋的要醋,該加辣椒的加辣椒。雖然那些你吃慣了的食物有時也會厭倦,但讓你一個月不吃,你又會想念。這種感覺,類似根深蒂固的婚姻,小吵小鬧—離不了。
當我們在談論吃的時候,我們是在談論小時候校門口那家麻辣燙如何香;是在談論第一次能花自己的錢,想吃什么就買什么的時候如何爽;是在談論那個陪你吃燒烤的身邊人如何體貼;是在談論只需為下一頓吃什么而煩惱的學生歲月如何單純;是在談論那一雙忙于搟面、包餃子的手如何操勞;是在談論那個喝得神志不清的夜里,吃完夜宵如何傷感;是在談論加班回來,微波爐里的那碗湯如何孤獨……
你會安慰自己,與其寡淡無味活到一百歲,不如好酒好肉瀟灑五十年。所以,你會視死如歸地愛著也許是地溝油烤出來的燒烤,只因為味道夠銷魂;視死如歸地愛著有著過多添加劑的午餐肉、福爾馬林泡出來的黃喉、農藥噴過的空心菜、飼料可疑的小龍蝦……只因為你的胃不可背叛。
你的胃會告訴你,哪里有你最愛吃的;而你最愛吃的食物會告訴你,哪里是故鄉。
(白 帆摘自《ONE·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