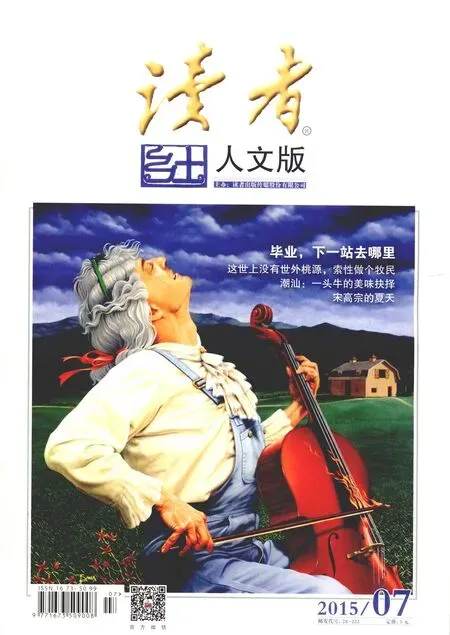大的捉來高吊起,細的捉來下油鍋
文/陶喜寶 圖/邵曉昱
大的捉來高吊起,細的捉來下油鍋
文/陶喜寶圖/邵曉昱

按父親的說法,我的第一次求學經歷,就是被兩泡尿攪黃的。
1988年9月開學前一天,父親趕了個大早,來到奶奶家,把睡眼惺忪的我從那張幾乎要坍塌的木床上拉了起來。我們要去他的高中同學、南天湖鎮中心小學一年級班主任付曉林家中做客。
做客的本意,一是父親想要他高中最好的朋友還錢,再找他借點兒—山上幾十畝烤煙葉子正是需要錢的時候,偏偏資金周轉不靈,父親緊缺這筆錢;二是父親想讓五歲零兩個月的女兒到付老師的班跟班讀書。
“去學校多大點兒事嘛,也不是說非要你正式讀書。我們原本想,在付老師家里暫住,我和你媽放心,哪曉得你從小是個流尿客啊!”多年以后,父親向我講述我的這段入學經歷時,拋開其他,只以“流尿客”收尾。
據父親回憶,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飯,關于我的入學問題,付老師與父親開始了如下對話:
“你嫂子說,陶妹兒昨晚睡覺流了兩次尿,棉絮都濕透了。”付老師話語里多了一層責備。
父親的臉上有些僵,用手摸了摸我稀疏且黃的凌亂短發:“她五歲多了,按理說不該還尿床啊!”
付老師輕哼一聲:“人哪,都該認命!把娃兒扔下,去深山老林里種什么烤煙葉子,折騰來折騰去,賺不到錢不說,娃兒也遭罪!”
付老師完全忘記了,是我的父親“拋家棄子”,在深山老林里種烤煙葉子折騰來的錢借給他,他才得以托關系從村小老師變成了鎮中心小學老師。
付老師的話鋒轉得如此之快,父親一時竟無言以對。讓他還錢,讓女兒暫住他家借讀,兩個念頭被付老師那句“人哪,都該認命”擊得潰不成軍。
“明年過了再說陶妹兒入學的事。”付老師說完這句話,又讓付師母給我塞了幾顆花生糖,就以趕時間去學校上班為借口,禮貌地把父親和我送出了門。父親那天既沒從他高中最好的兄弟那里拿到一分錢,也沒能把我成功送進學堂。
回到奶奶家,父親做了一個決定。很難說是受高中同學的刺激,還是別的什么,父親開始收拾我的衣物。奶奶踮著一雙小腳跟前跟后問:“娃兒不住我屋頭了?娃兒要跟你一路回去?”父親答:“媽,陶妹兒跟我們回山上住。”奶奶不動聲色地告起狀來:“這個娃兒啊,一頓喝兩碗稀飯,還看不住我的羊,也牽不動我的牛。晚上盡是流尿,我天天給她換,天天給她洗,都洗不過來喲!”
父親看一眼床邊那些皺成一團的小小衣裳,不說別的,只說:“媽,這一年給你添麻煩了。”
“你們這個月買來的米、油、面和肉,你弟妹生娃兒,我就全部勻給他們了哈?”奶奶追出門來,希望父親給個肯定的回答。
“好,你說了算。”父親沒有回頭看。年輕的父親只是一邊抽煙,一邊摩挲著我發黃的小臉,說:“幺女,爸爸帶你回家,再也不留你一個人。”
父親不知道的是,奶奶每個月都要把他買的米、油、面、肉送給幺爸。
父親不知道的還有,我在奶奶家喝了近一年的稀飯,因為營養跟不上,才成了流尿客。
回程是長長的、仿佛永遠也看不到盡頭的山路。一陣風過去,成片的松林發出怪響。我躲在父親身后,怯怯地牽著他的衣角。父親一把將我舉在肩頭:“幺女不怕,爸爸教你念咒招。”
“大的捉來高吊起,細的捉來下油鍋。”
一句鬼城人都懂的話。
“幺女,如果你以后怕,大聲念這個咒招,就什么都不怕了。”父親說。
五歲零兩個月的我,就這樣跟著父親在山路上念:
“大的捉來高吊起,細的捉來下油鍋。”
這兩句咒招,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學習到的故鄉俚語。
后來,父親和母親照例折騰,種烤煙失敗,又去鎮上養豬賣,又去了新疆。可是無論去哪里,父親再也沒有把我和哥哥放在任何一家親戚或朋友家寄養過。他們去哪里,我和哥哥就去哪里。
多年以后,提起我的第一次求學失敗的經歷,父親別的不再提,只是拿“流尿客”取笑我。可是,于我而言,不去學堂又如何?我還有你!
(張小艷摘自新浪網陶喜寶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