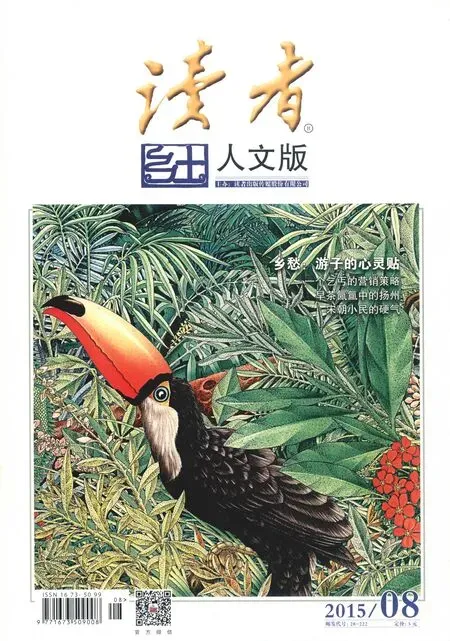鄉愁中的“新上山下鄉”
文/蔣 嬌 張良娟 嚴 芳
鄉愁中的“新上山下鄉”
文/蔣嬌張良娟嚴芳
只需開車10分鐘,廣告策劃人周中罡就能把生活從“城市頻道”切換到“鄉村頻道”。
周中罡的“鄉村頻道”,位于距離德陽市區10公里之外的壽豐鎮東湖鄉高槐村。3年前,他和妻子在這里租下一幢民房,種菜澆花,讀書畫畫,過起愜意的田園生活。
鄉愁在發酵,田園在召喚,家鄉在崛起……各種各樣的動因,讓越來越多的人從城市走向鄉村。有人享受田園生活,有人給鄉村帶去城市文明,有人撥動生意的算盤……其間,融合與抗拒,享受與焦慮,勾勒出當今時代“新上山下鄉”不一樣的表情。
“城歸”下鄉帶來“慢”經濟
讓周中罡“切換頻道”的原始動力,是鄉愁。從鄉村走出來的他,對田園有著天然的親近感。中心城市工具化、臉譜化的生活,則讓他萌生了回到鄉村的念頭。
“晨起沐浴,灑掃庭院,池邊觀魚,屈指數花……”周中罡微信上的照片和文字記錄了高槐村的愜意生活。2012年,他在綿竹、什邡、德陽等地搜尋一大圈之后,選中了偶遇的高槐村。他租下主人的房子,擺起書架,買來農具,起名“等閑居”。
離開中心城市,到周邊鄉村享受田園慢生活的,不止周中罡。在距離成都市半個小時車程的三圣鄉,就有櫻園等文藝和田園氣息交織的空間。它們的主人,有的是專欄作家,有的曾是國企領導。櫻園的女主人熊英說:“我的田園夢源于幼年,因為農村生活一直都很純樸,鄉親們散了工之后,聚在院壩里擺龍門陣,一起吃飯,這就是生命本身應有的活力和熱情。”
鄉愁發酵,田園生活如同一個磁場,吸引著眾多城市人的腳步,也讓鄉村醞釀出“慢”經濟。
2014年年底,在朋友們的強烈建議下,周中罡將“等閑居”改造成一家鄉村咖啡館,并取名“不遠”。“離城市不遠,離鄉村不遠,離理想的生活不遠。”周中罡解釋。
沿著鄉間公路走近“不遠”,淡黃色的招牌上,一只爬行的蝸牛悠然自得。陽光下的小院里,書架、藤椅、插花自成風景。打著鄉村慢生活的招牌,“不遠”還提供很多田園生活體驗。“可以體驗農耕生活,也可以去周邊挖野菜,還可觀鳥。店里特意準備有望遠鏡、鳥類識別圖冊。”周中罡的妻子胡蓉熱情推介。
每逢周末,“不遠”門前都停滿了車。有時候,也有當地的村民出于好奇,到“不遠”點一杯咖啡嘗鮮。不過,“不遠”的客人主要還是城里人。
如今,高槐村已經開起兩家鄉村咖啡館,從事油畫、陶藝、木雕等創作的藝術家也相繼進駐高槐村。不少因為打工離鄉而緊鎖的村民家門口,也掛上了“房屋出租”的標志。“這里不久也許會成為德陽鄉村慢生活的示范點。”高槐村黨支部副書記張赟告訴記者,“高槐村已經把發展文化旅游作為一項產業規劃,期待著鄉村休閑游能為當地百姓帶來紅利。”
中央黨校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授郭強,把像周中罡這樣的人稱之為“城歸”。他說:“農村孩子到大城市里,積累了資本、能力和人脈關系,然后再回到農村去改造農村,這是一個必然的改造過程。”
鄉村“試驗田”引發農業生態轉變
從“地主”到園主,返鄉的“新農人”們不僅改變了祖輩們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也正引發鄉村和農業生態的轉變。
皮膚黝黑的楊慧,是資陽市綠能生態農業觀光產業園董事長,但看起來像個地道的農婦。
5年前,從資陽農村走出去的楊慧,和來自臺灣的老公在廣東經營著自己的企業。她說:“我們有很多朋友做農業,在他們的影響下,我也漸漸對現代農業產生了興趣。”2010年,楊慧回到老家建立了生態農業觀光產業園。
同樣,“80后”唐文萍也瞞著父母,辭掉了成都的工作,回到老家安岳養雞、種湘蓮,創辦了“閑云農園”。
從城市回到鄉村,楊慧和唐文萍不再像父輩那樣單純種地,而是轉身當起園主。
唐文萍的閑云農園采用“半農半X”的發展模式:一方面,用湘蓮種植構筑立體生態農業,充分開發荷塘及其周邊所涉農作物與養殖物的效益;另一方面,為農業副產品融入設計元素。盡管才兩年多時間,但她的農莊已能固定為當地提供100人左右的用工需求,農忙時更是需要200~300人的勞動力。而楊慧的產業園則集中流轉了1500畝土地,流轉出土地的農民在收取土地租金的同時,也可以在產業園打工,在家門口掙工資。
“資本、技術、人才等城市生產要素下鄉,能改變農村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四川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克俊說,“除了給農民帶來經濟效益和就業崗位,城市生產要素下鄉也拉動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帶去了先進的技術和生產、管理方式,拉動了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夢想變現,一路進守拉鋸
對于周中罡和楊慧們而言,田園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對于祖祖輩輩生活在鄉村的人們而言,田園卻是生存。在田園夢變現實的路上,進與守、保留與提升一路拉鋸。
已經5歲的櫻園,今年再次遇到難題。“這里正面臨被肢解,雖然我們的租約沒有到期,也主動漲價保全,卻難以滿足地主的胃口。”熊英在自己的微博上寫道,“從前年開始,已經失去兩塊地了,死掉幾株大樹。我想留下菜地為客人們種菜,想留下成片的薔薇花、金桂……但他們有自己的審美,鏟掉花木、蔬菜,把田地鋪水泥通車,安裝不銹鋼欄桿,搭塑鋼房子……”幾經拉鋸,在損失了一塊菜地并增加了租金之后,熊英的櫻園才得以保全。
“最初許多老鄉不愿把土地流轉出來,他們并不相信我。”楊慧說,“在創建產業園之初,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實地考察、溝通協商,和村民們同吃同睡同勞動,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讓大家漸漸相信我并不是來圈地的。”
農民的擔心并非毫無緣由。“農業建設投入周期長,經濟收效緩慢,很多人一開始熱情很高,結果卻搞不下去。”張克俊說,“近幾年,生產要素開始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雙向流動,從城市流向鄉村的資本、技術、人才和產業正逐漸增多。然而很多工商資本在下鄉過程中,往往以農業的名義大規模圈地,最終卻改變土地用途,開展商業開發,使得農民遭受排擠。”張克俊還向記者列舉了自己在調查中曾遇到過的反面案例:“圈地擠占農民生存空間;不適當的生產方式污染土壤、水資源,破壞鄉村的生態;鄉村觀光體驗游帶來游客的同時,也留下生活和工業垃圾。”
未來,鄉村是綜合生態服務系統
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為,現在出現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將建立一種新的城鄉關系,如何引導這種關系良性發展,是人們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提出“新上山下鄉”的觀點。他認為,城市病在中國爆發,交通擁堵、食物安全等問題,激發了人們回鄉的愿望。“農村將為城里人提供一個綜合生態服務系統。它提供干凈的空氣、干凈的水以及文化、精神和休閑等等,農村將變成一個消費的場所,而不再是一個生產的場所。”俞孔堅說,“以前城市是消費者,農村是生產者,而‘新上山下鄉’將導致一種新的城鄉關系的建立。”
最早在中國提倡“樂活”生活方式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沈立,也多次提出“新上山下鄉”的概念:“保留與提升廣大農村,倡導與發展生態而時尚的鄉村生活方式,在城鄉各地構建這種生態文明村,引導與激勵大批知識青年、小資白領與富裕階層再次‘上山下鄉’,不僅是符合中國文化傳統、國際流行時尚與未來發展趨勢的好事,還能順利解決在大型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諸多難題—空巢問題、大學生就業、新農村建設等。”
“城市的資本、人力上山下鄉,是需要一定基本條件的。”張克俊說,“在未來,農村的景觀價值、生態價值會越來越突出,休閑、觀光農業將會是未來鄉村發展的一個主導方向。在這種大背景下,需要進行提前介入、統一規劃。只有對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生產標準和服務標準進行統一規劃,良性引導,才能更加長遠地發展。”
(袁友仁摘自《四川日報》2015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