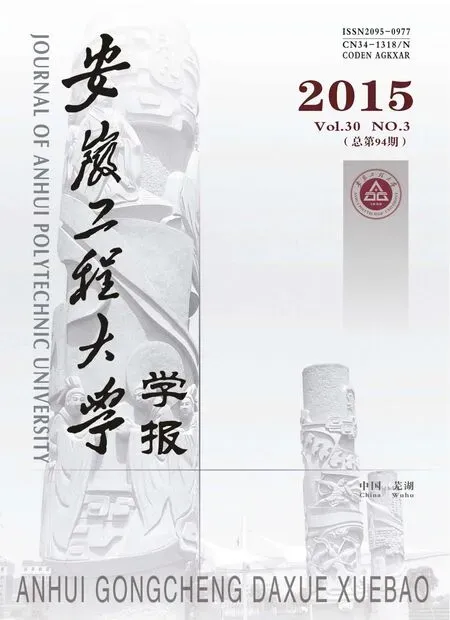翻譯加工中的“垂直翻譯”與“水平翻譯”
崔 燕
(安徽工程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20世紀70年代,一門新興的綜合性交叉學科——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誕生成為人類認識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認知科學涉及哲學、神經科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6個學科,由此形成心智哲學(Philosophy of Mind)、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等6個分支學科.這些學科相互交叉,又產生了認知科學的許多新興研究領域,如: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心理哲學(Philosophy of Psychology)、語言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等等[1].認知科學是研究人類心智的科學,它以人為本,著力描述“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的過程[2],結合各學科優勢以探索人類大腦的“黑匣子”.
長期以來,翻譯研究一直停留在基于文本研究的領域和水平上.然而,翻譯活動畢竟是由有意識、有認知能力的人所進行的涉及復雜心理、思維和認知的活動.因此,翻譯過程可被視為涉及兩種語言轉換的認知心理活動.對翻譯的研究,不能忽略人的因素,更不能忽略人的認知和心理活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將翻譯與認知科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結合起來的實證研究在開始西方興起.一些學者[3-8]借助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成果和方法,利用有聲思維法(Think Aloud Protocols,TAPs)、Translog軟件、眼動追蹤技術(Eye-tracking technology)等,對譯者的動態心理過程進行實證性描述研究,翻譯研究的注意力漸漸轉向針對譯者大腦活動的認知研究,為揭開翻譯過程的本質做出了推動性的貢獻.
進入新世紀,國內一些學者不約而同地意識到建立翻譯(認知)心理學的必要性[9-11],也有學者將基于認知科學的、結合認知心理學和認知語言學理論的翻譯過程研究稱為認知翻譯學(Cognitive Translatology)[12].他們對西方認知科學視角下的翻譯研究做了不少引介工作[13-24].然而,目前我國的翻譯認知研究還存在著實證不足、研究方法滯后等問題[17],我國的認知翻譯學/翻譯(認知)心理學還處于基本起步階段.
1 翻譯加工模式之爭
翻譯過程被看作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語碼轉換過程.基于認知科學的翻譯研究主要探討翻譯過程中的信息加工模式、加工策略、加工單位等問題,對翻譯過程和譯者的思維和心理活動進行描述性研究[12].就信息加工模式而言,目前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De Groot[5]稱之為“垂直/縱向翻譯(vertical translation)”和“水平/橫向翻譯(horizontal translation)”.
“垂直翻譯”倡導者Seleskovitch[25-26]認為,翻譯尤其是口譯,不是從源語到譯語的直接語碼轉換,而是涉及對源語的理解和譯語的再創造過程.對源語文本的理解意味著脫離具體的語言形式,從而生成意義,譯者在理解原文意義或思想之后,再用譯語傳遞所要表達的信息,即“脫離源語語言外殼(deverbalization)”的翻譯加工模式.而持“水平翻譯”觀點的Gerver[27]認為,翻譯就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語言的直接語碼轉換,即從源語詞匯表征到譯語詞匯表征的轉換.換言之,“垂直/縱向加工模式”認為翻譯過程首先是理解過程——對輸入的源語進行加工并獲取其話語表征;理解結束后,譯者開始翻譯——對所獲取的信息進行重新編碼.這種模式下,理解在先、翻譯在后.而“水平/橫向加工模式”認為,譯者在閱讀源語的同時進行語碼轉換和重組,即邊理解邊翻譯[10].
事實上,翻譯認知過程與語言的特點、譯者水平、翻譯難度等各種因素相互關聯.本研究將重點探討非專業譯員在句子層面的翻譯過程中如何進行信息加工.研究的結果可與專業譯員的認知過程進行對比,為今后對非專業譯員翻譯認知過程的干預研究、提高其翻譯水平的可能性進行前期探索.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心理學的有聲思維法(TAPs),即受試者在完成某項任務的過程中,隨時隨地講出頭腦里的各種信息,它是目前研究和描述思維及心理活動最有效、最直接、最簡便的方法[12].
2.2 被試
從某工科院校非英語專業的大一學生中選取15人作為研究對象,參加有聲思維實驗.挑選平時比較善于表達的學生作為被試,且這些學生都表示愿意積極配合.
2.3 實驗過程
(1)實驗前:有聲思維培訓.實驗選擇在教室進行.為使被試明白何為有聲思維、如何進行有聲思維,研究者先告知其中一名被試將一個漢語句子譯為英語,在翻譯過程中要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心理活動全部口述出來,隨后進行評論和指導;再給出第二個句子,請第二個人進行嘗試;以此類推,直到所有被試都明白如何進行有聲思維.
(2)實驗中:句子翻譯.研究者給出3個漢語句子,要求被試各自進行翻譯,并且對有聲思維進行錄音,最后將最終的譯文寫在紙上并上交,整個過程沒有時間限制,但不允許查字典或工具書,這樣做是為了讓被試充分調動已有的知識儲備,更好地觀察其思維活動,避免因查資料而頻繁停滯.
(3)實驗后:數據收集、TAPs數據轉謄、譯文評分.實驗收到11份有效錄音,將這些有聲思維錄音材料中所能聽到的一字一句轉謄為文本材料,以便后續分析研究.實驗同時還收集了被試的最終譯文,將11份有效錄音對應譯文,按照統一標準進行打分(3個句子,每句5分,共計15分),最后,按照譯文質量的高低,將11名被試分為高分組a組、中分組b組、低分組c組,并對其進行編號,如:a1、a2、b1、b2等.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分組編號
根據譯文得分,有4名被試被編入高分組(a組≥11分),編號為:a1、a2、a3、a4;有5名被試被編入中分組(9分≤b組﹤11分),編號為:b1、b2、b3、b4、b5;其余2名為低分組(c組﹤9分),編號為:c1、c2.
3.2 3組被試譯文得分、翻譯時長和思維話語量對比分析
不同水平被試譯文得分、翻譯時長和思維話語量對比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a、b、c 3組完成3個句子翻譯后的平均得分分別為11.88分、9.3分、7分,平均時長分別為5′08″、2′53″、5′46″,翻譯耗時從多到少的排序為c組、a組、b組.由表1可以看出,c組用時最長而得分最低,a組用時略少于c組而得分最高,b組用時最短、接近c組所用時間的1/2,成績居中.這說明b組譯員的效率最高,用時極短,成績也不差;a組譯員用時雖然較長,但譯文質量最高;c組譯員效率最低,用時最長,而譯文質量最低.
研究者統計了每位被試整個翻譯過程中有聲思維文本的字數(不包括字符數),并稱之為“思維話語量(Amount of Thinking Talk)”.統計結果發現,平均思維話語量從多到少的順序為c組(392字)、a組(343字)、b組(250.2字),這與他們的翻譯時長排序正好對應.
通過研究各組被試的具體思維話語可以發現,a組被試詞匯量相對豐富,翻譯某一漢語詞組時可能會聯想到1~2個對應的英語單詞或詞組,因此會有詞匯選擇的耗時,同時造成話語量較多;b組被試的詞匯量相對較小,較少出現詞匯選擇困難,因此耗時最短、思維話語量最少;c組譯員詞匯匱乏,翻譯時往往無從下手,心理活動比較混亂,這表現在不斷重復某詞或詞組,過多使用“錯了,這個不行”、“該怎么說呢”等質疑性表達.此外,該組被試往往不會分析句子成分,拎不出句子主干,有時逐字硬譯、死譯,譯文質量不高,這也證明了“翻譯初學者難以把握較大的翻譯單位”這一說法.

表1 不同水平被試譯文得分、翻譯時長和思維話語量對比
3.3 翻譯加工模式分析
研究者將具有以下特征的翻譯思維模式歸為垂直加工模式:從分析漢語句子主干入手、將翻譯最初的注意力集中于句子結構或關鍵詞組上,即先理解再翻譯;而水平加工模式表現為:邊讀邊譯、沒有首先關注句子主干或聯想典型句型結構,而是逐字硬譯.
依據以上定義,通過分析TAPs文本數據,發現11名被試中,有10位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垂直加工模式,而其中5位不僅采用了垂直加工模式,還參雜了水平加工模式.這5位混合加工模式者,有的在同一句子翻譯過程中,前半句顯現出水平加工模式、后半句顯現出垂直加工模式,而有的在翻譯某一句時,完全采用垂直加工模式,但在翻譯另一句時又完全呈現為水平加工模式.這說明,翻譯過程中的垂直與水平加工模式不具排他性,某一被試可能既會采用垂直加工模式,又會采用水平加工模式.
各被試的翻譯加工模式分析結果為垂直加工模式a1、a3、b4、b5、c2;水平加工模式c1;混合加工模式a2、a4、b1、b2、b3.
可以看出,翻譯過程中,各組被試的加工模式各有不同.以譯文高分組a組為例,有人屬于垂直加工模式、有人屬于混合加工模式.11人中只有c1完全采用水平加工模式.從收集的數據看,c1的譯文總分7.5分,翻譯時長6′07″,思維總話語量490字,耗時長、話語量大,而譯文質量低.因此可以大致推斷,一般情況下采用單一的水平加工模式進行翻譯活動的人比較少,且采用了這一模式的翻譯效率和譯文質量都較低,因此不值得提倡.
那么,垂直加工模式和混合加工模式相比,哪種模式產出的譯文質量更高呢?垂直加工組數據分析如表2所示.混合加工組數據分析如表3所示.對比表2、表3可知,前者的翻譯加工過程用時較短(3′20″﹤4′43″)、思維活動話語量較少(263.6字﹤319.8字),信息加工的結果,即譯文的質量,也相對比后者要低一些(9.8分﹤10.3分).用時少、思維活動相對簡單,可能是由于采用垂直加工模式時,思路相對清晰,工作記憶載荷相對較輕.而參雜了水平加工的混合模式,用時明顯較長、思維活動更為復雜,印證了文獻[10]中提出的“橫向翻譯必然會加重工作記憶的載荷,導致整個加工過程將會顯得難些、慢些”這一說法.

表2 垂直加工組數據分析

表3 混合加工組數據分析
通過分析被試的有聲思維文本,研究者還發現水平加工模式的翻譯過程呈現重復性.例如,a4在翻譯“他為演講時出了錯而感到難為情”這一句子時,采用的是單一的水平加工模式,他按照順序邊讀邊譯,而涉及“演講”這個詞的翻譯就至少重復工作了3次,延長了翻譯時間;而b2翻譯此句時采用垂直加工模式,在讀題時,并沒有急著翻譯,而是先領悟了題目“他為演講時出了錯而感到難為情”的意思,將其理解為“他為演講出錯而感到羞愧”,并進一步簡化為“感到羞愧”,這樣該句的翻譯就變得清晰明了,減少了重復性工作,節省了時間.
然而水平加工模式也并非一無是處.水平加工,即邊閱讀邊翻譯,可視為“刺激—反應”的過程.被試有時之所以會優先采用水平加工模式,是因為他們看到某個詞,就會馬上找到對應的翻譯,由于這種情況下的信息轉碼非常熟練,水平加工就成為了不可避免的條件反射,這樣的信息加工往往正確率高、把握更大.上文還提到,水平加工會導致重復性工作,然而重復工作也正好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斷檢驗其譯文的正確性提供了機會.因此,參雜了水平加工的混合模式效果好于單純的垂直加工模式.
4 結語
翻譯過程中的垂直加工模式與水平加工模式不具排他性,某一譯者可能始終采用某種信息加工模式,也可能交替使用兩種加工模式.當譯者對某一英語單詞、詞組或句型非常熟悉時,在翻譯時就會迅速進行英漢匹配,這時就會呈現水平信息加工.水平加工模式有利有弊,弊處在于它會導致一定程度的重復性翻譯工作,且不易把握句子翻譯重點;利處在于若是基于熟練的信息匹配,翻譯質量比較有保證.本研究結果顯示,融合兩種加工模式的混合加工模式產出的譯文質量最高.
從譯文高分組被試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教學啟示.詞匯量是非專業譯員進行翻譯的基礎,熟練的英漢匹配是進行翻譯的必要條件,而對句子的結構分析是保證高質量輸出的關鍵.
[1]蔡曙山.語言、邏輯與認知:語言邏輯和語言哲學論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2]王寅.什么是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3]W L?rscher.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towards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erformance[C]//In House J.& Blum-Kulka S.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Tübingen:Narr,1986.
[4]W L?rscher.The translation process:methods and problems of its investigation[J].Meta,2005(2):597-608.
[5]De Groot A.M.B.The cogni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three approaches[C]//In Dank J.H.,Shreve G.M.,Fountain S.B.,etal.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25-56.
[6]A L Jakobsen.Effects of think 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C]//In Alves F.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3:69-95.
[7]M Shuttleworth,M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8]S G?pferich,A L Jakobsen,I M Mees.Behind the Mind:Methods,Models and Result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M].Copenhagen:Samfundslitteratur,2009.
[9]劉紹龍.翻譯心理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10]顏林海.翻譯認知心理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11]李奕,劉源甫.翻譯心理學概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12]盧衛中,王福祥.翻譯研究的新范式——認知翻譯學研究綜述[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3(4):606-616.
[13]顏林海.西方翻譯認知過程研究概述[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116-119.
[14]顏林海.試論翻譯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內容與方法[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96-101.
[15]劉紹龍.論雙語翻譯的認知心理研究——對“翻譯過程模式”的反思和修正[J].中國翻譯,2007(1):11-16.
[16]劉紹龍,仲偉合.口譯的神經心理語言學研究——連續傳譯“過程”模式的構建[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8(4):86-91.
[17]劉紹龍,夏忠燕.中國翻譯認知研究:問題、反思與展望[J].外語研究,2008(4):59-65.
[18]鄧志輝.認知學與翻譯學結合的新起點——《翻譯與認知》評介[J].中國翻譯,2011(3):68-71.
[19]鄧志輝.認知科學視域下西方翻譯過程實證研究發展述評[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12(4):88-94.
[20]侯林平.翻譯認知研究的新進展——《翻譯與認知》評介[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1(2):310-314.
[21]肖開容,文旭.翻譯認知過程研究的新進展[J].中國翻譯,2012(6):5-10.
[22]王寅.認知翻譯研究[J].中國翻譯,2012(4):17-23.
[23]王艷濱.《翻譯的認知探索》評介[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3(3):469-473.
[24]王寅.認知翻譯研究:理論與方法[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4(2):1-8.
[25]D Seleskovitch.Interpretation: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ng[C]//In Brislin R.W.Translation: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New York:Gardner Press,1976:92-116.
[26]D Seleskovitch.Language and cognition[C]//In Gerve,D.& Sinaiko H.W.Language,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New York:Plenum Press,1978:333-342.
[27]D Gerver.Empirical studi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a review and a model[C]//In Brislin R.W.Translation,Application and Research.New York:Gardner Press,1976:16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