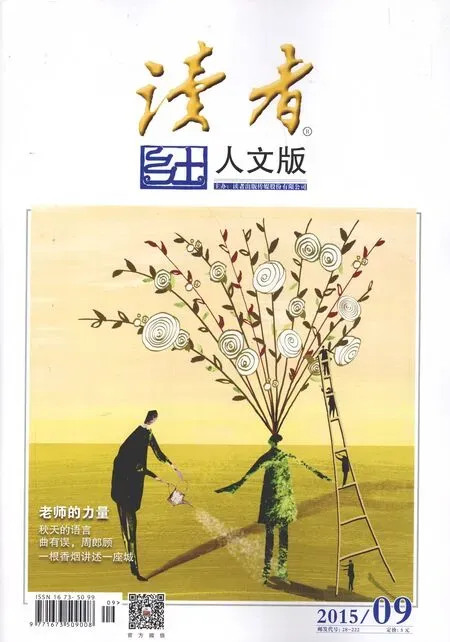愛爾蘭式煩惱VS上海式煩惱
文/崔米娜
愛爾蘭式煩惱VS上海式煩惱
文/崔米娜

一
我現(xiàn)在住在愛爾蘭,每日被綠色環(huán)抱。所有那些關(guān)于愛爾蘭的傳說—翡翠之島、全世界最美的地方,等等—都是真的。只要踏出家門,我看到的就是在山坡上吃草的牛兒、奔跑的馬兒和四處閑逛等待主人一起回家的狗。
這一切真是美妙極了。對于在擁擠喧囂的上海生活了十多年、眼睛極度疲勞的我來說,這些景致實在是太令人放松了。
不過,美麗的愛爾蘭也正面臨著奇特的困境:這個只有450萬人口的國家,沒法留住年輕人。年輕的愛爾蘭人成群結(jié)隊地離開故土,因為在這里找不到工作。
我曾和這里一些孩子剛剛大學(xué)畢業(yè)的父母們聊天,發(fā)現(xiàn)只有少數(shù)家庭有孩子在首都都柏林工作,其余的家庭,孩子們都去了倫敦、巴黎、紐約、悉尼等城市找工作。
城市如此,農(nóng)村更是如此。在愛爾蘭,有些農(nóng)村整個村鎮(zhèn)都見不到年輕人—他們在澳大利亞經(jīng)營個奶牛場,或者在美國當(dāng)個木匠,掙的錢都比在家鄉(xiāng)要多。
與中國不同,經(jīng)營農(nóng)場在愛爾蘭一直是個令人驕傲的職業(yè)。在莫納根,要當(dāng)真正的農(nóng)夫,至少需要擁有60畝土地。擁有土地,尤其是超過60畝地,仍然是一件非常驕傲的事。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現(xiàn)在要從這些地里掙出足以維持生計的收入,非常困難。
一位經(jīng)營農(nóng)場的鄰居,同時養(yǎng)著幾十頭牛。他告訴我,每年從每頭牛身上只能賺不到100歐元。他自己呢,為了確保地都耕好、牛都喂飽,每天清晨5點即起,常常半夜才歇。但是,所有的這些辛苦卻換不來利潤。每天白天,他還要“兼職”當(dāng)卡車司機,賺一點外快。
他向我坦陳,如果哪天歐盟的小農(nóng)場補貼沒有了,他一定不會再做農(nóng)場主了。
這些煩惱在有些一頓飯就能吃掉100歐元的上海人聽來,多半覺得有些不真實吧!至少不像是歐洲人的生活。但事實就是,“第一世界”的很多人生活并不富裕,希臘的情況可能還要更糟糕一些。
二
鄰居是農(nóng)場主,辛苦一年,養(yǎng)二三十頭牛,每頭牛卻常常賺不到100歐元。我常常在想,那為什么還要做呢?
后來慢慢地,我理解了—對他來說,這就是生活的意義。他從小在農(nóng)場做農(nóng)活長大,耕好自己的土地,就是他人生尊嚴的來源,哪怕利潤微薄到只能通過歐盟農(nóng)業(yè)補貼的渠道實現(xiàn)。
我也常常聽他抱怨,為什么牛的收購價格這么低—這當(dāng)然是因為在他的區(qū)域和能力范圍內(nèi),事實上只能找到一個買家。而在一個像愛爾蘭這么小的國家,即便再換一兩個買家,賺到的也不過是微利和薄利的區(qū)別。
我注意到的另一個現(xiàn)象是,這些愛爾蘭的小農(nóng)場主們,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做農(nóng)場主了。原因很簡單:做這一行完全賺不到錢。他們辛苦工作,送孩子上大學(xué),希望他們將來成為銀行家、工程師或教師—任何一種足以讓他們賺錢、養(yǎng)家、買房的職業(yè)性工作。
在舊日的愛爾蘭,有一種說法是,60畝地能讓一個人擁有“陽光下自己的位置”—帶給一個人尊嚴、尊重和獨立生活的能力。但顯然,時代已經(jīng)變了。
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xué)不斷演進的今天,要維系生活,60畝地顯然已經(jīng)不夠,我身邊的小農(nóng)場主們因此生活得越發(fā)吃力。但是,如果農(nóng)場變大、變得現(xiàn)代化,可以養(yǎng)兩三萬頭牛羊,會不會又把我們身邊這片美麗的綠色鄉(xiāng)村景色破壞掉?
這真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或許,最后的最后,我的鄰居們會干脆決定說:“真是受夠了!不想再干了!不如在這60畝地上蓋些別墅,賣給那些向往鄉(xiāng)村生活的城里人算了。”
很有可能,那些向往鄉(xiāng)村生活的城里人當(dāng)中,就有我們當(dāng)年在上海的朋友。誰都知道,中國人現(xiàn)在是“抄底歐洲”的主力軍之一。
我一邊想,一邊嘆息。“陽光下的60畝地”—這些土地,現(xiàn)在還能做什么用?我的孩子們,將來又怎樣才能找到他們在陽光下的位置呢?
(馬一成摘自《瞭望東方周刊》2015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