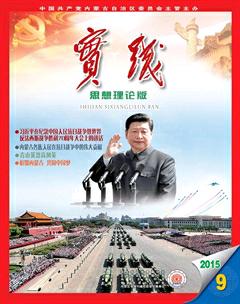辯證把握經濟新常態與“四個全面”的關系
蔡常青
核心觀點:經濟新常態與“四個全面”是既有區別又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所謂區別,主要是各自回答和解決的主題有所不同。經濟新常態是對我國基本國情發生階段性重大變化的新定位,集中回答了如何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推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實現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跨越的基礎性問題。“四個全面”則主要回答了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如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升治國理政水平,統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布局的根本性問題。所謂內在聯系,既體現在兩者統一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局上,統一于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事業上,也體現在兩者互為基礎、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
經濟新常態與“四個全面”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大戰略思想。正確認識和把握兩者的內涵及其辯證關系,是主動適應引領新常態,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基礎和必然要求。
一、經濟新常態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客觀依據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習近平總書記辯證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作出的科學判斷,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階段性變化的認識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1993年,鄧小平同志就已經預見到:“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進入新世紀,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尤其是發展不平衡已經成為全局性的突出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入分析了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2008年以后,隨著世界經濟大穩定周期的結束和我國步入經濟大國行列,國內外發展環境進一步發生了明顯變化。為此,習近平同志明確主張將“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寫入了黨的十八大報告,并強調這是有深意的。這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世情、國情、黨情發生重大變化的整體認識和判斷。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則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后經過近兩年的實踐探索和深入思考,對我國現階段“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內涵作出的更為具體深入的明確回答。習近平總書記自2014年5月首次提出“新常態”后,在多種場合就經濟新常態進行了全面論述,深刻地闡明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的必然性,闡明了經濟新常態的三個主要特征和九個具體趨勢變化,闡明了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必須遵循的大邏輯,從而進一步指明了我國改革發展的新方位、新內涵和新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的論述主要是從經濟層面表述的,但我們對新常態的理解不能僅限于經濟層面。經濟基礎變化對整個社會生活的變化必然產生基礎性、全局性、決定性影響。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的判斷,實質上也是對我國基本國情階段性變化的整體判斷。這一判斷的本質含義是,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雖然沒有變,但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有階段性內涵的重要遞進與轉換。如果說,改革開放后的前三十年,我國經濟總體上是處于以規模速度型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那么,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我國已經進入一個質量效益型的高速發展階段,正向著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新階段演進。
基本國情階段性變化的新判斷呼喚著治國理政的新方略。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決定了小康社會必須更加凸顯全面建成,為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首先邁出關鍵一步;決定了改革必須更加凸顯全面深化,從制度體制上續發新的強大動力;決定了法治必須更加全面公正,充分彰顯保障改革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法治功能;決定了管黨治黨必須更加全面從嚴,擔負起新的歷史任務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同時,也決定了各項目標舉措必須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正是適應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四個全面”更加清晰地確立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和主攻方向,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有機整體和頂層設計,成為指引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
二、“四個全面”是主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科學綱領
“四個全面”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逐步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首次把“四個全面”作為一個整體提出。他強調:“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從這一表述可以看出,“四個全面”作為一個總體戰略布局,是以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為前提的,是與引領經濟新常態直接關聯的。
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首先要立足新常態、辯證地把握新常態。新常態既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客觀依據,也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科學支撐。歷史經驗證明,對基本國情的認識程度不僅直接影響著科學決策的正確性,而且直接影響著科學決策的執行力。比如,科學發展觀,是基于我國改革發展中出現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階段性變化實際提出的,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指導思想。但是,前些年,由于我們對基本國情階段性變化內涵的認識還沒有達到新常態的深度,因此執行時就有一些不堅決、不到位的問題。這正是我們多年強調轉方式、調結構而實際成效并不彰顯的重要原因。在當今,由于我們有了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我們黨始終保持著戰略上的平常心,強調只要經濟不跌出合理區間,一般不采取強刺激手段,要更多地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驅動、擴大內需、拓展空間布局來應對,著力在提質增效升級上下功夫,這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調結構、轉方式的步伐。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新常態并不是穩定態,而是一個有著確定遠景并隨著實踐不斷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正如有的專家所言,我國目前的狀態還只是新常態的起始點,它將經歷一個新舊多重因素變化的綜合優化過程。這個過程既是一個不斷認識、適應新常態的過程,也是一個以“四個全面”引領新常態的探索過程。這就需要我們辯證地把握新常態的動態性、發展性和規律性,始終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引領新常態的實踐指南,不斷提升駕馭新常態的能力和水平。
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須融入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從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來思考“四個全面”與新常態的內在關系,我們可以看到,“四個全面”不僅立足于這一大邏輯,貫穿于這一大邏輯,也是落實這一大邏輯的治本之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對我國現階段戰略目標和戰略抓手的系統化。從戰略目標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體現了黨的階段性奮斗目標與引領經濟新常態的一致性,如果不能落實經濟新常態提質增效升級的內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難以高質量地實現,將會直接影響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從戰略抓手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是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兩個輪子,也是推動經濟新常態的兩個輪子;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保障,也是正確引領經濟新常態的根本前提。因此,“四個全面”不僅把引領經濟新常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和中國夢的目標有機統一起來,而且與實現既定目標的各項戰略抓手有機統一起來,從而為我們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實踐綱領和具體路徑。
三、經濟新常態與“四個全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
經濟新常態與“四個全面”是既有區別又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所謂區別,主要是各自回答和解決的主題有所不同。經濟新常態是對我國基本國情發生階段性重大變化的新定位,集中回答了如何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推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實現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跨越的基礎性問題。“四個全面”則主要回答了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如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升治國理政水平、統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布局的根本性問題。所謂內在聯系,既體現在兩者統一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局上,統一于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事業上,也體現在兩者互為基礎、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在理論上,兩大戰略思想的提出,進一步完善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內在邏輯體系,即以我國基本國情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科學判斷為基礎,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線,以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為戰略布局,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接力奮斗。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內在邏輯體系日趨完善,標志著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基礎上,圍繞實現現代化和中國夢的目標,進一步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化國家以及如何建成這樣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問題,從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飛躍。在實踐上,兩大戰略思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深化,對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布局的構建,進一步完善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國夢的實踐綱領,標志著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體思路和踐行路線的創新突破和日臻成熟,其價值好比我們黨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指導,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進而推動我國以短短的30年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一樣,必將對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鑄就新的輝煌產生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