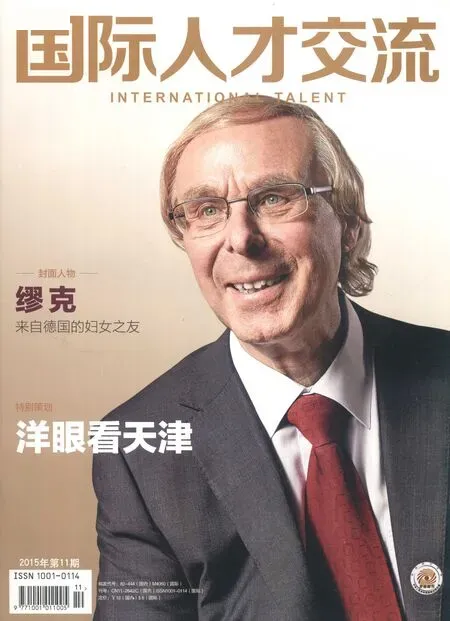屠呦呦:諾獎背后
屠呦呦:諾獎背后

祝賀屠呦呦研究員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座談會在京舉行,圖為座談會后屠呦呦(中)和與會嘉賓交流
1967年,一個由全國60多家科研單位、500多名科研人員組成的科研集體,悄悄開始了一項特殊的使命,代號“523”,研究的指向正是——防治瘧疾新藥,因為上世紀60年代的美越戰場上,瘧原蟲已經對奎寧類藥物產生了抗性,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屠呦呦正是“523”項目中的一員。
經過漫長而又艱苦卓絕的研究,在經歷了190次失敗之后,屠呦呦課題組于1971年在第191次低沸點實驗中發現了抗瘧效果為100%的青蒿提取物。次年,該成果得到重視,研究人員從這一提取物中提煉出抗瘧有效成分青蒿素,后來被廣泛應用,挽救了無數瘧疾病人的生命。
2015年10月5日,諾貝爾委員會授予屠呦呦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表彰她發現青蒿素,顯著降低了瘧疾患者的死亡率,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科研工作者。許多中國人為之歡欣鼓舞,但隨之而來的爭議也不絕于耳。
屠呦呦的科研經歷是“純中國”式的,她的成就是如何登上國際舞臺的?沉甸甸的諾貝爾獎對她來說是否是“不能承受之重”?對此,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試圖揭開這位打著中國特色烙印的國際化人才是如何獲獎的。
他們將屠呦呦推向世界
這位既沒有留學經歷,又沒有博士身份,更沒有兩院院士耀眼光環的中國老太太是怎樣進入諾貝爾獎評委的視野的呢?原來,她身后有兩位來自美國的“伯樂”——一位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路易斯·米勒,另一位則是米勒同一實驗室同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蘇新專。
2007年,米勒與蘇新專赴上海參加一個瘧疾與傳染媒介會議,會上米勒就問在場的人,誰知道青蒿素到底是誰發現的?怎么發現的?在場的人竟都不知道。
這個問題引起了米勒的高度關注,這讓他想到了奎寧的歷史。奎寧是在青蒿素出現之前的一種抗瘧藥物,最早的應用出現于16世紀的秘魯印第安人之中,后來被西班牙人帶回歐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從未被認定為奎寧的發現者。這也導致現在的專家說印第安人不可能有這樣一項發現。米勒認為,在青蒿素的問題上,不能讓歷史重演。同事蘇新專也建議道,應該把這項發現推薦到某個國際獎項。蘇新專當時就提出,可以考慮提一下諾貝爾獎。米勒也一口答應了下來。
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米勒每年都從諾貝爾獎評委會收到推薦表格,而懂中文的華人科學家蘇新專的任務就是幫他找到可以推薦的人選。蘇新專對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李國橋的瘧疾臨床研究工作比較熟悉,正是從李教授那里,蘇新專了解到屠呦呦的工作,從而獲得了當年“523”計劃的一些資料,又到北京見了一些“523”計劃參與者,最終決定將屠呦呦推薦給諾貝爾獎。
2010年,米勒和蘇新專將屠呦呦推薦給了諾貝爾獎后,又推薦到了拉斯克獎評委會,而拉斯克獎素有諾貝爾獎風向標之稱。沒想到,諾貝爾獎沒有消息,但拉斯克獎很快就有回應。2011年屠呦呦獲獎后,曾引起國內轟動。
除了推薦的情誼,米勒和蘇新專為配合拉斯克獎還寫了一篇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藥園的發現》,后發表在著名的《細胞》雜志上。正是拉斯克獎和《細胞》雜志的影響力打開了局面,屠呦呦很快贏得了西方學界的關注。現在,在維基百科有關屠呦呦的介紹里,第一個引用的就是米勒和蘇新專的介紹性文章。
不過,雖然從2010年開始向諾獎評委會推薦,但是,諾獎遲遲沒有消息,米勒便“年年推”,直到5年后的今天,屠呦呦終于登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
除了遠在美國的米勒和蘇新專將屠呦呦和青蒿素擺在了諾獎評委會的案頭,中國大陸也有一位科學家不遺余力地宣傳屠呦呦的研究成果,他就是北大生命科學院前院長饒毅。據媒體公開報道,2011年8月22日,饒毅在其博客首先刊登對屠呦呦和張亭棟從中藥中發現化學分子的成就,其后他與合作者在《中國科學》發表文章,敘述屠呦呦和張亭棟的工作,稱之為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饒毅還曾明確告訴媒體,他希望把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到屠呦呦和張亭棟兩位前輩科學家身上,并希望能夠推動二人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國際科學界對屠呦呦沒多少認識的情況下,饒毅一次次所做的詳細推介,為屠呦呦、為中國科研事業爭取國際榮譽起到了積極作用。
榮譽:集體還是個人?
“這是集體的工作,為什么獎項只給屠呦呦一個人?”連日來,在科學界知名網站科學網上,類似的疑問所激起的討論跟帖絡繹不絕。
一句“屠呦呦能獲得大獎,是一個團隊努力多年、經過190次失敗的結果”的總結回顧,更是被各方廣為引用,這一話題也引起不少大眾媒體的關注。
在《青蒿素:源自中草藥園的發現》文章中,米勒和蘇新專寫道:“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 我們毫無疑問地得出結論: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中藥研究所(中藥所)的屠呦呦教授是發現青蒿素的首要貢獻者。”毫無疑問,這兩位“伯樂”認為,諾獎頒給屠呦呦實至名歸。蘇新專認為,屠呦呦獲獎有五大原因:
第一,“523”計劃始于1967年,當時屠呦呦并沒有參與進來,但從1971年在廣東開會的會議記錄可以看出,研究一直沒有取得太大進展。屠呦呦后來加入進來,并于1972年在南京召開的會議上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效殺瘧原蟲。可以說正是屠呦呦把青蒿素帶到了項目中來。
第二,在1972年的會議上,屠呦呦在報告中提到,當時青蒿提取物效果不穩定,而葛洪著作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這讓她就想到常用煎熬和高溫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壞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便由用沸點78攝氏度的乙醇提取改為用沸點35攝氏度的乙醚提取。所以,提取溫度這個突破點也是屠呦呦第一個解決的。
第三,1972年8月,屠呦呦帶領一個團隊到海南做臨床試驗,包括她和幾個同事首先在自己身上試藥,證明了沒有太大毒性。她們總共做了30例,基本都有效。所以她是第一個做臨床試驗的人。
第四,國內有個爭論,就是中藥所的提取成分沒有其他機構好,確實是這樣,但其他機構的提取方法是根據屠呦呦提供的材料改進的。無可否認,屠呦呦參與了研究青蒿素的化學結構。
第五,屠呦呦是青蒿素衍生物雙氫青蒿素的發明人。青蒿素是脂溶性藥物,水溶性不好。水溶性不好,藥性就不好。而提高水溶性,服用后就比較容易吸收。雙氫青蒿素吸收性能就比較好。
蘇新專的解釋都有嚴實的“523”項目材料作證,并且都是原始資料。
當然,這位“伯樂”也認為不能否認其他人的貢獻。“523”項目參與的人有500多人,有三四十個單位,跨度10多年,確實是一個團隊的貢獻。但是,諾貝爾獎是頒發給個人的,沒有辦法提名一個集體的貢獻。如蘇新專所言,如果有可能推薦集體獎當然最好,但如果只能選一個人做代表,那就是屠呦呦。
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李真真則認為爭議折射出中西文化沖突。“中國的傳統是講集體主義,特別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成績是大家的,功勞是集體的’;至今,國內科技評獎依然主要是獎勵項目,科學家的名字多是以一個集體的形式呈現。而西方的科學傳統恰恰與此相反:大多獎項都是突出個體,科學獎勵源于對科學發現優先權的承認,這是來自于科學追求獨創性的內在邏輯。首先就是獎勵‘優先權’:即關注在重大的科技成果中,誰第一個提出思想或者方法路徑。”
李真真認為,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學科細分,現代重大的科學成就,往往都必須凝聚集體力量和智慧,但西方之所以一直堅持把重大獎項給予個人,就是對一個基本科學理念的回歸,而科學的進步緣起于獨創性的思想。西方科學獎勵關注優先權,堅持將重大獎項頒給個人,有利于啟發創新。
與蘇新專給出的解釋類似,拉斯克獎評獎委員會對屠呦呦獲獎給出了三點評獎依據:一是誰先把青蒿素帶到“523”項目組;二是誰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三是誰做了第一個臨床實驗。
據介紹,諾貝爾獎的獎勵中也同樣出現過不少爭議,這在全球科學界很正常。然而,西方更多爭議的是“優先權”的認定,到底是誰先提出創新的思想路徑。比如日本去年獲得的諾貝爾獎也曾引發學術界討論,其中爭議的正是與德國科學家誰來占有“優先權”。“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發明完全出自一個人,為什么到了中國,類似的重大獎勵就必須攤到每一個參與者身上才算公平?”一位學者撰寫的反思文章激起了不少共鳴,“我們仍然對過時的平均主義、平衡觀念心向往之,仍然沒有樹立起成熟的獲獎心理。”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2015年10月18日3版
《“屠呦呦獲獎爭議”折射中西文化沖突》、新華網2015年10月6日《揭秘屠呦呦美國推薦人》

2011年,屠呦呦獲拉斯克臨床醫學獎,該獎項被看作諾貝爾獎的“風向標”